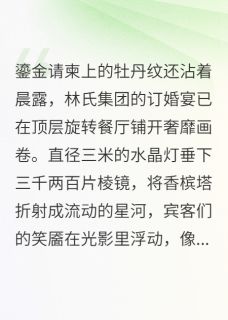
一鎏金请柬上的牡丹纹还沾着晨露,林氏集团的订婚宴已在顶层旋转餐厅铺开奢靡画卷。
直径三米的水晶灯垂下三千两百片棱镜,将香槟塔折射成流动的星河,
宾客们的笑靥在光影里浮动,像一群精致的蜡像。林辰握着锦盒的掌心沁出薄汗。
翡翠项链“碧潭春”是祖父在缅甸开采的老坑料,鸽血红的色根在灯光下流转,
链扣处錾刻的“辰”字被摩挲得发亮。他低头为苏晚晴戴上时,
丝绸礼服的肩带滑到肘弯,
指尖猝不及防触到她颈后肌肤——一枚新鲜的蝴蝶胎记正泛着微红,
翅膀上的磷粉纹路竟与父亲书房那只紫铜密档袋上的火漆印分毫不差。“怎么了?
”苏晚晴侧过脸,睫毛上的碎钻落进他眼底,声音甜得发腻,“是不是觉得我今天特别美?
”林辰喉结滚动,将那句“这胎记什么时候纹的”咽了回去。
他记得父亲总说那密档袋里锁着“能让林家万劫不复的东西”,
此刻却被美人颈间的香气冲散了疑虑。掌声雷动时,他没看见苏晚晴转身敬酒的瞬间,
右手在裙摆下快速按了三下手机。宴会厅的水晶灯突然闪烁两下。
财务总监老陈的尖叫刺破喧嚣:“不好了!核心账户……十亿!十亿凭空消失了!
”笔记本电脑的蓝光映出他惨白的脸,转账记录上的操作IP赫然指向张启明的办公室。
那个跟了父亲三十年的副总正举着酒杯,闻言“哐当”一声摔碎了高脚杯,
红色酒液在地毯上洇开,像一滩迅速蔓延的血。“不可能!”林辰推开人群冲向监控室,
指纹锁验证通过的瞬间,屏幕上突然跳出段视频——张启明正将一叠文件塞进碎纸机,
背景里隐约有苏晚晴的笑声。他攥着鼠标的指节泛白,突然想起今早签字时,
张副总递来的笔似乎比平时沉了些。“林董!林董晕倒了!”混乱中有人撞翻了香槟塔,
碎裂声里,林辰被保镖架着冲向电梯。父亲躺在急救推车上,氧气管里的白雾急促起伏,
胸牌上的照片还是十年前意气风发的模样。ICU的红灯亮起时,
手机在白大褂口袋里震动,来电显示是“晚晴”。“林辰,”她的声音裹着电流的杂音,
像淬了糖的玻璃碴,“你真以为我稀罕当林家少奶奶?张副总可比你大方多了。
”林辰的指甲掐进掌心:“账户是你动的手脚?”“不然呢?”轻笑突然变成冷笑,
“你以为那串破翡翠真是定情信物?有人等着用它换条命呢。”电话那头传来金属碰撞声,
一个苍老的男声透过电流滚过来,带着烟草和铁锈的味道:“项链拿到了?告诉张启明,
按老规矩,货在仰光港三号仓。”忙音突兀地炸响。林辰盯着手机屏幕上跳跃的信号格,
突然想起苏晚晴刚才敬酒时,颈间的翡翠正对着宴会厅的监控探头——那角度,
刚好能拍清链扣内侧的纹路。急救室的门缓缓合上,将父亲最后一声微弱的**关在里面,
也彻底关死了他人生里所有的光。二ICU的探视时间刚过,
林辰就踹开了张启明办公室的门。百叶窗把阳光切成碎片,
落在办公桌那枚黄铜印章上——边缘新添的月牙形缺口刺得他眼睛生疼。
上周签字时还光滑如新的印面,此刻正沾着未干的红泥,
盖在土地**协议上的字迹比原版胖了半分。“张叔,”他抓起协议的手指在颤抖,
“这枚章是假的。”张启明转动着无名指上的玉扳指,慢悠悠地往紫砂壶里添茶叶:“小辰,
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林董还在里面躺着,你总得拿出点继承人的样子。
”蒸汽模糊了他的脸,
林辰却看清他袖口露出的表——那是父亲送他的五十岁生日礼物,
表背刻着的“忠”字被刻意磨平了。财务部的铁皮柜像被野兽啃过,
装着公司印章的紫檀木盒裂成两半。林辰扑到总裁办公室的保险柜前,
指纹锁发出刺耳的报错声。当保镖用电锯切开柜门时,
他瘫坐在地毯上——本该存放海外账户清单的防水袋空空如也,
只有半张撕碎的登机牌卡在夹层里,金色的“仰光”字样被咖啡渍晕染开,
航班日期正是订婚宴的前一天。“林先生,这是您的传票。”穿制服的法警站在碎玻璃渣里,
送达回证上的案由写着“涉嫌非法挪用资金”。附带的证据袋里,
几张模糊的监控截图显示“林辰”深夜进入财务室,签字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
最致命的是份邮件打印件,发件人是他的私人邮箱,内容赫然是“张副总,
按计划转移资金”。“这不是我发的!”林辰攥皱了纸页,指缝渗出血,
“邮箱密码只有晚晴知道!”律师在电话那头叹气:“对方还提交了苏**的证词,
说你早就计划掏空公司……林辰,证据链太完整了。”雨点狠狠砸在落地窗上,
像无数只手在拍门。林辰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公寓,电梯间的监控闪着红光。他摸出钥匙时,
后颈突然贴上块冰凉的手帕,乙醚的甜腥味瞬间灌满鼻腔。挣扎中,
他看见三个蒙面人手腕上都缠着黑布,
布面上绣着极小的蝴蝶图案——和苏晚晴颈后的胎记一模一样。再次睁眼时,
铁锈味灌满喉咙。手脚被粗铁链锁在舱壁上,磨破的皮肤黏在金属上,一动就**辣地疼。
货轮的引擎在腹腔里共振,腥咸的海风从舷窗灌进来,带着远处岛屿的瘴气。
个**着上身的壮汉蹲在面前,胸毛里夹着枚蛇形银戒,
用沾着烟油的手指戳他脸颊:“金三角老板,喜欢嫩肉。”他咧嘴笑时露出颗金牙,
“那位戴翡翠项链的女士,说要活的——慢慢玩。”林辰的指甲抠进舱板的缝隙,
木屑嵌进肉里。他想起苏晚晴最喜欢的那支香水,前调是玫瑰,
后调却藏着若有似无的苦杏仁味——和此刻手帕残留的气味完美重合。
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里,他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响,不是因为冷,是因为那蚀骨的恨。
“苏晚晴……”他对着漆黑的舷窗无声地念,铁链在挣扎中发出绝望的碰撞声,
“我就是化作厉鬼,也绝不会放过你。”三黑暗中,有人往他嘴里塞了块破布。
透过舷窗的微光,他看见货轮正在靠近片被浓雾笼罩的陆地,岸边隐约有红灯闪烁,
像无数双在黑暗中窥视的眼睛。腐叶的腥气混着罂粟花甜腻的香气,像条湿冷的蛇,
钻进林辰每一个汗毛孔。他被铁链拴在木柱上,手腕处的皮肤早已溃烂,
暗红的血痂与铁锈粘在一起,稍一动弹就牵扯着筋肉撕裂般疼。热带的太阳像块烧红的铁板,
烤得他**的脊背冒出油光,背上纵横交错的鞭痕里还嵌着没清理干净的砂砾,
是昨夜电击鞭留下的纪念。“醒了?”粗嘎的嗓音带着浓重的泰语口音,
个**上身的看守晃着手里的电击鞭走过来。那人左脸有道从眉骨划到下巴的刀疤,
嚼着槟榔的嘴角淌下猩红汁液,胸肌上纹着只展开翅膀的蝴蝶,翅尖正好盖住**。
林辰死死盯着那蝴蝶纹身,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
这已经是他被扔进这片丛林的第三十七天,每天清晨都会被这畜生用冷水泼醒,
然后开始长达十个小时的劳作——给罂粟花除草、割浆、晾晒,
稍有迟缓就会迎来劈头盖脸的抽打。电击鞭带着滋滋的电流声甩过来,抽在他腿弯处。
剧烈的麻痹感瞬间窜遍全身,林辰膝盖一软跪倒在地,铁链猛地绷紧,
勒得脖颈像是要被扯断。他看见自己映在泥水里的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出血,
曾经精心打理的头发如今像团枯草,哪里还有半分林氏集团继承人的模样。“看什么看?
”刀疤脸一脚踩在他背上,军靴底的防滑纹碾过未愈的鞭伤,“苏**的男人说了,
要慢慢玩死你。”他从腰间掏出张塑封照片,用脚尖踢到林辰面前。
照片上的苏晚晴穿着露背长裙,依偎在个中年男人怀里笑得花枝乱颤,
男人无名指上戴着枚蛇形银戒,
的阳光正好在照片角落形成个光斑——那位置与张启明指节上那道半月形旧疤完美重合。
林辰的指甲深深抠进泥地里,指甲缝里塞满黑褐色的腐土。他想起三年前在慈善晚宴上,
张启明端着酒杯说“林辰啊,以后这林氏集团,迟早是你的天下”,
那时这男人无名指上还没有疤。他又想起订婚宴前夜,苏晚晴撒娇说“我最喜欢蛇了,
觉得它们特别性感”,当时只当是小姑娘的怪癖,此刻却像毒蛇的信子舔过心脏。
“她还说了,”刀疤脸蹲下来,用电击鞭的金属头挑起林辰的下巴,
“你胸口这块皮肤最嫩,烧起来一定很好看。”旁边两个看守发出淫邪的哄笑,
其中个瘸腿的男人搬来个炭火盆,里面的烙铁正烧得通红,
顶端的蛇头花纹在火光中扭曲蠕动。林辰挣扎着想要后退,铁链却将他牢牢固定在木柱上,
他闻到自己身上的汗味、血腥味,还有远处罂粟加工棚飘来的**甜香,
这些气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绝望气息。
“不……不要……”他嘶哑地哀求,泪水混着汗水淌进嘴角,又咸又涩。
这是他第一次放下所有尊严求饶,却只换来更放肆的嘲笑。刀疤脸戴上厚厚的石棉手套,
捏起那枚烧红的烙铁。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远处丛林里不知名鸟类的怪叫,
还有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他死死闭上眼睛,却挡不住那扑面而来的热浪,
能清晰地感觉到胸口的汗毛正在卷曲、烧焦。“滋啦——”皮肉被烫熟的焦糊味瞬间炸开,
比罂粟花的香气更刺鼻,比腐叶的腥气更难闻。林辰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
浑身剧烈地抽搐起来,眼前阵阵发黑。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被这股剧痛从身体里撕扯出来,
飘在半空中,冷漠地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林家大少,此刻像条蛆虫一样在泥地里扭动。
烙铁被拿开时,胸口留下个清晰的蛇形疤痕,边缘的皮肉外翻着,像朵丑陋的花。
刀疤脸用没戴手套的手抹了把他脸上的冷汗,塞进自己嘴里吮了吮:“味道不错,
比那些缅甸娘们的汗还甜。”林辰疼得几乎昏厥,意识却异常清醒。
他看着那枚还在冒烟的烙铁,突然疯狂地笑了起来,笑声嘶哑破碎,
吓得旁边的瘸腿看守后退了半步。他想起父亲教他的那句话“真正的强者,不是不会痛,
而是痛到极致还能睁着眼睛”,此刻他终于明白,原来极致的痛苦真的能让人笑出来,
那是一种比哭更绝望的表情。夜幕降临时,热带暴雨毫无征兆地砸下来。
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伤口像是被撒了把盐,疼得他牙关打颤。看守们将他拖进简陋的木棚,
扔在冰冷的泥地上。这里挤满了和他一样被贩卖来的“货物”,有男人有女人,
眼神都空洞得像口枯井。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挪到他身边,
用蹩脚的中文说:“别硬撑……他们最喜欢看我们反抗……”老者的左臂空荡荡的,
伤口处缠着块肮脏的破布,“上个月有个不服输的,被扔进鳄鱼池了……”鳄鱼池。
这三个字像冰锥刺进林辰的心脏。他想起小时候在动物园看过的鳄鱼,
那些趴在岸边一动不动的冷血动物,张开嘴时能看到锋利的牙齿和喉咙深处的黑暗。
他下意识地摸了**口的伤疤,那里还在隐隐作痛,提醒着他自己还活着,还能感觉到疼。
暴雨越下越大,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淹没。木棚的屋顶漏着雨,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
却冲不掉那股皮肉烧焦的气味。林辰蜷缩在角落里,听着外面看守们的嬉笑声,
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鳄鱼低沉的嘶吼。他开始想家,想父亲做的红烧肉,
想母亲在世时给他织的毛衣,想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温暖时光。突然,木棚的门被踹开了。
刀疤脸举着油灯站在门口,雨水顺着他的刀疤流淌,看起来像脸上又多了条血痕。
“那个林家的,出来。”他狞笑着说,“老板有新玩法了。”林辰被两个看守架起来,
踉踉跄跄地走出木棚。暴雨模糊了视线,只能看到远处岸边有几点鬼火般的绿光。
他被推搡着走上一座狭窄的木桥,桥下面是浑浊的池水,能听到巨大的水花溅起的声音。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刀疤脸的声音在暴雨中显得格外清晰,
“这是苏**特意为你选的‘归宿’。”林辰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终于明白,
苏晚晴根本没打算让他活着,她要看着他一点点被折磨,最后以最屈辱的方式死去。
“为什么……”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问道,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刀疤脸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哈哈大笑起来:“你到死都不明白?苏**从来没爱过你……她接近你,
就是为了林家的那块翡翠……还有你父亲藏起来的那些秘密……”翡翠?秘密?
林辰的脑海里闪过无数片段:父亲书房里那个神秘的紫铜密档袋,
苏晚晴颈后那个诡异的蝴蝶胎记,
还有订婚宴上她脖子上那条闪闪发光的翡翠项链……这些碎片在他脑海里旋转、碰撞,
突然拼凑出一个可怕的真相。但已经来不及了。刀疤脸猛地一脚踹在他的后背。
林辰感觉自己像片落叶一样坠入黑暗的池水中,冰冷的液体瞬间灌满了他的口鼻。
他挣扎着想要浮出水面,却感觉腿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住了。剧烈的疼痛从腿上传来,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正在被撕裂,鲜血在水中弥漫开来。是鳄鱼!
死亡的恐惧像潮水般将他淹没,但他的眼睛却死死盯着岸边的方向。暴雨中,
他看到刀疤脸正举着手机拍摄,屏幕的光映出他狰狞的笑脸。更远处,
有个模糊的人影站在树下,手里似乎拿着什么东西在晃动——那轮廓,
像极了苏晚晴最喜欢的那款**版手袋。是她!她竟然真的来看自己的死状!
一股难以言喻的恨意从心底喷涌而出,盖过了身体被撕裂的剧痛。林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张开嘴想要嘶吼,却只吐出一串气泡。他看着岸边那模糊的人影,
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诅咒:“苏晚晴!张启明!还有所有害过我的人!若有来生,
我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定要让你们尝遍我所受的所有痛苦!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
”意识渐渐模糊,黑暗像巨大的漩涡将他吞噬。就在他以为一切都将结束时,
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岸边的树影里,有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影一闪而过。
那人手里提着个银色的箱子,在暴雨中显得格外突兀。那是谁?这个疑问在他脑海里闪过,
随后便彻底陷入了无边的黑暗。池水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鳄鱼的嘶吼声在雨夜里回荡,
像是在为这场残酷的死亡奏响哀乐。而那枚烧红的烙铁留下的蛇形疤痕,
在林辰逐渐冰冷的胸口上,仿佛还在散发着灼热的温度,烙印着他永世不灭的恨意。
四喉咙里还卡着鳄鱼池的腥咸泥水,林辰猛地睁开眼,胸腔里炸开撕裂般的疼。
不是被鳄鱼獠牙撕开的剧痛,是种钝重的、带着铁锈味的窒息感,
像有只无形的手攥着肺叶往死里捏。他下意识地抬手去抓脖子,
却摸到片光滑细腻的皮肤——没有铁链磨出的血痂,没有烙铁烫出的疤痕,
只有层薄薄的冷汗。视线里的一切都在旋转。头顶是繁复的金丝楠木浮雕,
缠枝莲纹在水晶灯折射下浮动,像极了父亲书房里那盏价值连城的古董灯。
身下的被褥柔软得不像话,蚕丝被贴着皮肤滑溜溜的,与丛林里发霉的麻袋天差地别。
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发现这具身体虚弱得厉害,稍一用力就头晕目眩,喉咙里涌上股甜腥。
“小少爷!您可醒了!”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头扑到床边,金丝眼镜滑到鼻尖,
露出双惊惶的眼睛。他手里的听诊器冰凉地贴上胸口,林辰瑟缩了下,
那触感让他瞬间想起金三角看守们的电击鞭——金属碰到皮肤时也是这样刺骨的冷。
“水……”他想开口,喉咙却像被砂纸磨过,发出的声音嘶哑古怪,完全不属于自己。
老头连忙倒了杯温水,用银勺喂到他嘴边。水流过喉咙时,林辰盯着对方胸前的校徽,
上面“协和医院”四个字刺得他眼睛发疼。这不是缅甸边境的小诊所,
不是那个能闻到罂粟花香的丛林营地。“镜子……”他又吐出两个字,
指尖不受控制地颤抖。管家匆匆拿来面鎏金铜镜,当那张脸映入眼帘时,
林辰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冻住了。镜中人有着苍白得近乎透明的皮肤,眉骨高挺,
嘴唇是失血过多的淡粉色,一双桃花眼此刻盛满惊恐,瞳孔里映出的全然是陌生。
这张脸俊美得像精心雕琢的玉像,却带着种病态的脆弱,
与自己记忆中棱角分明的模样判若两人。“我是谁……”他喃喃自语,
指尖抚上镜中人的脸颊,镜子冰凉的触感透过皮肤传进心脏。“小少爷,您是顾昀啊!
”老头急得直拍大腿,“京城顾家的独苗,您忘了?三天前您哮喘发作,
一口气没上来……”顾昀?这个名字像枚烧红的针,猝不及防扎进混乱的脑海。
着脸的中年男人摸着他的头说“昀昀要好好活着”……这些画面与林辰的记忆疯狂冲撞,
金三角的烙铁烫痕与这具身体手腕上的输液针孔重叠,
苏晚晴的笑脸和镜中这张陌生的脸在眼前交替闪烁。他抱着头倒回床上,
剧烈的头痛让他几乎呕吐。原来暴雨夜岸边那个白大褂人影不是幻觉,
原来那句“若有来生”真的被听见了。他真的死了,死在鳄鱼池的黑暗里,
却又在千里之外的京城,钻进了另一个少年的躯壳。“京城首富顾鸿的独子,
顾昀……”林辰,不,现在该叫顾昀了,他反复咀嚼着这个身份,手指抠进锦被,
将昂贵的真丝绞出褶皱,“哮喘猝死?”目光扫过床头柜,个白色药瓶倒在杂志上,
标签被指甲刮得模糊不清,只能辨认出“**沙丁胺醇”几个字。他捏起药瓶晃了晃,
里面的药片发出清脆的碰撞声,瓶底残留着点可疑的白色粉末,绝不是哮喘药该有的样子。
杂志封面突然刺入眼帘。苏晚晴穿着高定礼服,挽着张启明的手臂站在纳斯达克敲钟台上,
翡翠项链在闪光灯下泛着贼光。标题用加粗的黑体字写着:“启明集团海外上市,
创始人张启明携未婚妻苏晚晴共庆辉煌”。出版日期是昨天,距离他被扔进鳄鱼池,
才过去短短四天。四天。他在地狱挣扎的时候,
这对狗男女正在享受用他的血泪换来的荣华富贵。顾昀的手指猛地收紧,
药瓶“哐当”掉在地上,药片滚得满地都是。他想弯腰去捡,却发现这具身体异常虚弱,
稍一低头就呼吸急促,胸口传来熟悉的窒息感——这是原主顾昀的哮喘,
像道无形的枷锁,提醒着他如今的脆弱。“小少爷您别动!”白大褂老头慌忙去扶他,
却被他一把挥开。指尖无意间碰到杂志边缘,张折叠的便签掉了出来。
上面是行清秀的少年字迹,墨水洇了又干,看得出写得很急:“爸爸的朋友,蛇形戒指,
不能碰……”蛇形戒指!顾昀的瞳孔骤然收缩。
张启明无名指的旧疤、金三角看守的银戒、现在这张便签……所有线索像条冰冷的蛇,
突然缠上他的脖颈。他抓起便签贴在胸口,那里本该有个狰狞的烙铁疤痕,
此刻却只有平滑的皮肤,和这具身体原主微弱的心跳。窗外传来汽车引擎声,
管家的声音在门外响起:“老爷回来了。”顾昀猛地抬头看向铜镜,镜中的少年脸色苍白,
眼底却燃起簇与这张脸极不相称的火焰。那是从金三角的炼狱里爬出来的恨,
是鳄鱼池底凝结的怨,是林辰用生命换来的复仇火种。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适应着这具身体的呼吸节奏,将所有迷茫与脆弱压进眼底深处。当房门被推开,
那个被称为“爸爸”的中年男人走进来时,顾昀(林辰)已经垂下眼睑,
掩去了所有惊涛骇浪,只留下恰到好处的、病后的茫然。“感觉怎么样?
”顾鸿的声音低沉,带着不易察觉的疲惫。顾昀张了张嘴,
发出的声音还带着少年人的清嫩,与林辰原本的声线截然不同。
他看着眼前这个名义上的父亲,突然想起便签上的字迹,
心脏在胸腔里重重一跳——这个顾家,恐怕也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而他,
必须在这个陌生的世界站稳脚跟,剥开所有伪装,让那些欠了他血债的人,一个个付出代价。
窗外的阳光透过纱帘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顾昀的目光落在满地的药片上,
其中一片滚到他脚边,上面似乎沾着点极淡的、与药瓶底相同的白色粉末。这具身体的死,
恐怕也不是意外。新生的迷茫还未散去,新的疑云已悄然笼罩。顾昀缓缓抬起眼,
看向窗外那片繁华的京华景象,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不管前方有多少迷雾,
他都要一步步走下去,带着两世的记忆与仇恨,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掀起一场复仇的风暴。
五消毒水的味道还没散尽,顾昀已经在顾家老宅住了三天。这三天,
他活得像个偷穿别人衣服的贼,每分每秒都在和原主的影子较劲。清晨五点半,
生物钟准时拽醒他的瞬间,
喉咙里立刻涌上熟悉的痒意——这是原主顾昀哮喘发作前的预兆。
顾昀不敢像林辰那样猛地坐起,而是蜷着膝盖慢慢撑起上半身,指尖虚虚搭在胸口,
模仿着记忆中原主喘息时的弧度。窗台上的湿度计指向68%,他盯着那根红色指针,
想起福伯说过“小少爷对湿度最敏感,超过70%就要犯喘”,
赶紧按下床头的除湿机开关。梳妆镜前的托盘里,眉笔和哮喘喷剂并排躺着。
顾昀捏起那支薄荷味喷剂,
食指在按压阀上悬了三秒才按下——原主总在晨咳第三声时用药,
这个节奏他对着镜子练了十七遍。镜中少年脖颈左侧有颗淡褐色的痣,
林辰从前总爱用拇指摩挲锁骨,现在他必须改成用指腹轻点那颗痣,
这是昨天翻原主日记时看到的细节。“小少爷,该用早餐了。”福伯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
顾昀迅速把眉笔藏进《资本论》第37页——原主总在这一页夹书签。
推开梨花木门时,他刻意放缓了脚步。林辰习惯大步流星,而原主因哮喘,
步幅永远比常人小半寸,鞋跟蹭过地板的声音是“沙沙”的轻响。
顾鸿正用银叉剖开溏心蛋,顾昀拉开椅子的角度刚好是三十度,
这是他趴在门缝偷看福伯整理书房时记下的,原主坐惯了这把椅子,从不肯换位置。
“身体好些了?”顾鸿头也没抬。“好多了,爸。”顾昀端起牛奶杯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