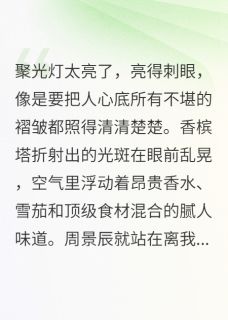
聚光灯太亮了,亮得刺眼,像是要把人心底所有不堪的褶皱都照得清清楚楚。
香槟塔折射出的光斑在眼前乱晃,空气里浮动着昂贵香水、雪茄和顶级食材混合的腻人味道。
周景辰就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臂弯里圈着一个年轻女孩。那女孩穿着一条裙子。
一条我无比熟悉的裙子——Dior去年春夏高定的秀款,全球就三件。当初为了拿到它,
我等了足足四个月,在巴黎蒙田大道旗舰店试穿时,镜子里映出自己发亮的眼睛。
它该安静地躺在我衣帽间最深处防尘袋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被另一个陌生的、怯生生的身体穿着,
出现在这个周氏主办的、汇聚了整个港城上流圈子的慈善晚宴上。女孩很年轻,
皮肤白得晃眼,眉眼间带着一种未经世事的、楚楚可怜的清纯。此刻,她微微低着头,
似乎承受不住这满场的珠光宝气和探究目光,身体不自觉地往周景辰怀里缩了缩。
周景辰的手臂收得更紧了点,
脸上挂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带着保护欲的、甚至有点洋洋得意的笑。我的心跳,
在那一瞬间,沉了下去,沉入一片冰冷刺骨的深潭。不是第一次了。
这种细微的、如同蛛网般缠上来的异样感。第一次,是半年前,他出差回来,
我整理他换下的西装。一件深灰色的Armani,手习惯性地探进口袋检查,
指尖触到一个冰冷坚硬的小东西。掏出来,是一枚小巧精致的钻石耳钉,单只的,设计独特,
绝非我所有。他洗完澡出来,我摊开手掌,那点碎钻在我掌心闪着微光。「哦,这个啊,」
他擦着头发,瞥了一眼,语气轻松得像在谈论天气,「大概是林助理不小心落下的吧,
她最近帮我处理些文件,毛毛躁躁的。」他走过来,自然地拿走耳钉扔在梳妆台上,
「明天让她拿走。」林助理?
那个跟了他五年、做事一丝不苟、永远穿着合身套装、连头发丝都纹丝不乱的女人?
她会「毛毛躁躁」到把耳钉掉进老板西装内袋?那时,我选择了相信。或者说,
选择维持表面的平静。五年的婚姻,两个庞大商业帝国的结合,牵扯太多。
我以为那只是漫长航程中一次无关紧要的气流颠簸。第二次,是在他常去的那家私人会所。
他应酬回来,带着一身烟酒气,醉意朦胧地解开领带。我走过去想帮他脱下外套,
目光落在他雪白衬衫的领口内侧。一点暧昧的、新鲜的草莓色唇印,像一小滴刺目的血,
沾在那里。心脏猛地一抽,指尖几乎要掐进掌心。他似乎毫无所觉,
或者根本不在意被我看到。只是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今晚…闹得有点疯。」
便径直倒进了沙发。我没有追问。那个夜晚,我独自坐在书房里,
落地窗外是沉沉的港城夜色。手指在平板电脑上滑动,订了一张最快飞往巴黎的机票。
我需要离开,需要透口气,需要冰冷的塞纳河风让我清醒。然而,机票订好了,
却迟迟没有按下付款确认。心底深处,似乎还残留着一丝可笑的、名为「希望」的灰烬。
直到现在。聚光灯下,他搂着那个穿着我裙子的女孩,姿态亲昵而张扬。
女孩裙子的腰线收得极好,衬得她腰肢纤细,青春逼人。那裙子,我穿着时是优雅从容,
穿在她身上,却成了某种无言的、宣告**的战利品。整个宴会厅的空气都凝固了。
音乐声不知何时停了,交谈的嗡嗡声也消失了。所有人的目光,
都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们三人之间,带着震惊、了然、幸灾乐祸或是纯粹的看戏心态。
我能感觉到那些目光的灼热,它们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后背上。周景辰也看到了我。
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搂着女孩的手臂似乎下意识地想松开,但随即又收紧了,
像是在宣告什么,又像是在给自己壮胆。他眼神闪烁了一下,
试图扯出一个惯常的、安抚性的笑容朝我走来:「清音,你怎么…」我打断了他。
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泪流满面。我甚至还能感觉到自己唇角微微弯起的弧度。
我踩着那双十公分的ChristianLouboutin,
鞋跟敲击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而稳定的「哒、哒」声。
这声音在死寂的大厅里异常清晰。我径直走到侍者面前,拿起一杯刚倒好的香槟,
澄金色的液体在剔透的水晶杯里微微晃荡。然后,我转身,
走向场地中央那束最亮的聚光灯下。灯光刺得眼睛有些发涩,
但我清晰地看到周景辰瞬间煞白的脸,和那个女孩眼中骤然涌起的惊惶。我站定,
举起手中的香槟杯,对着周景辰的方向,也对着全场所有屏息凝神的人。「周总,」
我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清晰地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平静得像在谈论一笔即将完成的交易,
「离婚协议,明早十点,会准时送到你办公室。」话音落下的瞬间,死寂被打破。
巨大的、难以置信的抽气声如同海啸般席卷了整个宴会厅。闪光灯疯了似的亮起,
咔嚓咔嚓的快门声连成一片,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砸在玻璃上。无数道目光,
惊愕的、狂热的、难以置信的,像带着实质重量的箭矢,瞬间将我钉在了那个光圈的中心。
周景辰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比他那身昂贵的白西装还要惨淡。
他像是被一记无形的重锤狠狠击中,身体晃了一下,搂着那女孩的手终于松开了,
无力地垂在身侧。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喊我的名字,想辩解什么,
但那点微弱的声音被淹没在巨大的嘈杂里,只有口型徒劳地开合着。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那个穿着我Dior高定的年轻女人,此刻脸上楚楚可怜的怯懦荡然无存,
只剩下纯粹的恐惧和茫然。她下意识地伸手想去抓周景辰的胳膊寻求依靠,
却被他不耐烦地、甚至带着一丝迁怒地猛地甩开。女孩踉跄一步,
脸色瞬间变得比周景辰还要难看,精心描绘的妆容也掩不住那份狼狈。我没有再看他们一眼。
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那些曾经对我艳羡、恭维,
此刻却写满复杂情绪的脸孔。周家的长辈,商界的伙伴,甚至还有几个平时与我交好的名媛,
她们的眼神里有震惊,有同情,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毕竟,周太太当众休夫,
这戏码比晚宴本身精彩百倍。高跟鞋的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更加清晰,更加稳定。
我挺直背脊,像一把出鞘的利剑,穿透了凝固的空气和层层叠叠的视线,
一步步朝着宴会厅那扇沉重的、镶嵌着金色纹饰的大门走去。身后,是死寂过后的巨大喧嚣,
是周景辰可能终于爆发的怒吼,是记者疯狂的追问,是闪光灯追逐不休的嘶鸣。但那些声音,
都被我隔绝在身后那道无形的屏障之外。推开那扇雕花大门,外面是相对安静的走廊。
冷气扑面而来,带着酒店特有的消毒水和香氛混合的味道。我深吸一口气,
肺部被冰冷的空气充满,那股一直强压着的恶心感却猛地翻涌上来。
我快步走向最近的女士洗手间,反锁上隔间的门。胃里翻江倒海。我扶着冰冷的陶瓷水箱,
剧烈地干呕起来。眼前阵阵发黑,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的礼服面料。不是因为周景辰,
不是因为那个女孩,不是因为那场当众的羞辱。是因为我包里那张薄薄的纸。颤抖着手,
从晚宴包里摸索出那张折叠起来的报告单。光滑的纸张在冰冷的指尖下显得格外脆弱。
我展开它,视线落在那个清晰的结论上:妊娠阳性(+)约8周。八周。
一个崭新的、脆弱的小生命,在我身体里悄然扎根。而他的父亲,就在几分钟前,
搂着另一个女人,穿着我的衣服,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新欢。
巨大的讽刺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住心脏,勒得我喘不过气。胃里的翻腾更加剧烈,我弯下腰,
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干呕,却什么都吐不出来,只有酸涩的胆汁灼烧着喉咙。
门外隐约传来宴会厅的喧嚣和脚步声,有人进来了,水流声响起,
还有刻意压低却难掩兴奋的议论:「天呐!你看到了吗?许清音!她居然当众提离婚!」
「周景辰带来的那个小妖精是谁啊?那裙子…好像是许清音的?」「啧啧啧,
周家这次脸丢大了…」「活该!早就听说周景辰玩得花,没想到这么不讲究,
这种场合也敢带人……」那些声音像细小的针,扎进耳朵里。**在冰冷的隔间门板上,
闭了闭眼。然后,双手用力,将那张承载着短暂希望又带来无尽讽刺的孕检报告单,
一点点、一点点地,撕成了碎片。细小的纸屑如同雪花般飘落,无声地堆积在光洁的地板上。
最后一片纸屑落下,我深吸一口气,打开水龙头,用冰冷的水用力拍了拍脸颊。
镜子里的女人,脸色苍白,眼神却像淬了火的寒冰。我拿出粉饼,
仔细地补好被冷汗微微晕开的妆容,将一丝凌乱的发丝别回耳后。推开洗手间的门,
外面的议论声戛然而止。那几个正在补妆的名媛看到我,脸上瞬间浮现出尴尬和一丝畏惧,
纷纷避开了我的目光。我没有理会,径直走向电梯。按下下行键,电梯门无声滑开。
里面空无一人。我走进去,冰冷的金属壁映出我毫无表情的脸。电梯直达酒店大堂。
司机早已将我的车开到了门口。拉开车门坐进去,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大**,
回周家还是……」司机老陈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回许宅。」我的声音平静无波,
听不出任何情绪。「是。」老陈立刻应声,发动了车子。
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平稳地滑入港城璀璨迷离的夜色。窗外,霓虹闪烁,
勾勒出这座欲望之都的轮廓。**在柔软的真皮座椅里,目光落在车窗外飞速倒退的光影上。
周景辰惨白的脸,那女孩惊惶的眼神,还有那些碎片般的议论……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
却激不起半点涟漪。手,下意识地轻轻覆上小腹。那里依旧平坦,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撕碎的纸屑仿佛还残留在指尖,带来一种冰冷的触感。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
在一个破碎的婚姻即将彻底坍塌的废墟上。车子驶上半山,周围的景色变得幽静。
熟悉的铁艺大门缓缓打开,车灯照亮了通往主宅的车道。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许家老宅。
厚重的橡木大门在我面前打开,管家忠叔站在门口,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担忧和欲言又止。
「**……」「忠叔,很晚了,去休息吧。」我打断他,声音疲惫却不容置疑。他张了张嘴,
最终只是恭敬地垂下头:「是,**。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我点点头,
径直穿过宽敞却带着点空旷冷清的大厅。父亲许世昌的书房门缝下透出灯光。
我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停留,继续走向二楼的卧室。属于我的房间,一切如旧,纤尘不染。
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沉静的山景和远处港口的点点灯火。我脱下束缚的高跟鞋,
扯掉沉重的耳环,疲惫地倒在柔软的床上。身体的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但大脑却异常清醒。
离婚协议,明天一早就会送到周景辰的办公室。这是第一步。然后呢?手指再次抚上小腹。
这个意外到来的生命,该如何处置?打掉?这个念头刚一升起,心脏就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留下?在一个单亲的环境里?顶着「周景辰的孩子」
这个注定充满非议的身份?混乱的思绪中,一个名字毫无预兆地跳了出来——温时砚。
温氏集团的掌门人,我父亲最欣赏的年轻后辈,也是……我从小就认识的人。
一个在周景辰耀眼的光芒下,似乎总显得过于安静内敛的存在。温家的根基在北方,
近年来才强势进入港城,势头迅猛。温时砚本人,如同他的名字,像一块温润却坚韧的玉石,
话不多,但每一次出手都精准有力。他前天似乎刚从国外回来。一个模糊的念头在心底盘旋,
带着某种孤注一掷的意味。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律师效率很高,九点不到,
那份措辞严谨、条件苛刻的离婚协议书已经摆在了我的书桌上。我签下自己的名字,
笔锋锐利,不带一丝犹豫。看着助理将它密封好,送往周氏集团。几乎是同时,
我的手机疯狂地响了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周景辰」的名字。我面无表情地按掉。他再打,
我再按掉。**锲而不舍地响了七八次,终于消停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发来的、带着气急败坏语气的短信:「许清音!你什么意思?昨晚发什么疯?
!」「立刻给我回电话!」「那份协议?你想都别想!马上给我撤回!」
「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我?许清音,你搞清楚状况!」「接电话!我们谈谈!别逼我!」
我看着屏幕上一条接一条跳出来的信息,像看一场无声的滑稽剧。
心底最后那点残存的、名为「夫妻情分」的东西,彻底烟消云散。
我直接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拖进了黑名单。世界清静了。接下来的一周,是无声的硝烟。
周景辰那边果然没有任何签署协议的动静。周家通过各种渠道试图联系我父亲施压,
甚至派了周景辰的母亲亲自上门。我避而不见。父亲许世昌的态度则异常强硬,
只丢给周家一句话:「我女儿的决定,就是许家的决定。」我的生活似乎回归了平静。
按时吃饭,在家庭医生的调理下,那恼人的孕吐也渐渐平息。
我开始翻阅许氏集团近几年的核心报表和项目资料。这些曾经是我熟悉的东西,
但嫁入周家的五年,为了所谓的「贤内助」身份,我主动疏离了。现在重新拾起,
那些冰冷的数字、复杂的架构、激烈的市场竞争报告,反而带来一种久违的掌控感和安全感。
只是身体的疲惫感比以往更甚,常常看着看着文件,就靠在宽大的扶手椅上沉沉睡去。
这天下午,阳光透过书房的落地窗洒进来,暖洋洋的。我又一次在文件堆里陷入了浅眠。
迷迷糊糊间,似乎听到书房门被轻轻推开的声音,有人走了进来。我以为是佣人,没有睁眼。
脚步声很轻,停在我身边。接着,一件带着体温和淡淡木质冷冽香气的外套,
轻轻地、小心翼翼地盖在了我身上。那香气很特别,像是雪后松林的气息,清冽、沉静,
带着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这味道…不是家里的任何一个人。我猛地睁开眼。
温时砚就站在我的扶手椅旁。他穿着剪裁合体的深灰色羊绒衫,衬得肩线平直挺拔。
他微微弯着腰,一只手还保持着为我披上外套的动作。猝不及防地对上我睁开的眼睛,
他深邃的眼眸里掠过一丝明显的错愕,随即化为一种温和的歉意。「吵醒你了?」
他的声音低沉悦耳,像大提琴的弦音。我坐直身体,
那件明显属于他的、质感极好的黑色羊绒西装外套从肩上滑落。我下意识地抓住它,
指尖还能感受到上面残留的、属于他的体温。「温先生?」我有些意外,撑着扶手坐直身体,
「你怎么来了?」「刚下飞机,和许伯父谈点事。」他站直身体,从容地解释,
目光落在我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他看你睡着了,让我顺路过来看看。」
他顿了顿,视线扫过我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旁边喝了一半的安神茶,
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太累了?脸色不太好。」他的关心很自然,没有刻意的亲近,
也没有过分的疏离,就像认识多年的老友。只是那句「顺路过来看看」
……父亲的书房在另一头,这顺的哪门子路?我忽略掉这个细节,把外套递还给他:「谢谢。
还好,就是看资料看得有点困。」他没有立刻接外套,
反而目光在我略显苍白的脸上停留了几秒,才伸手接过:「许氏这几年摊子铺得大,
千头万绪。你刚回来,不必急于一时,身体要紧。」语气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嗯,我知道。」我点点头,转移话题,「听说温氏在北欧的新能源项目进展神速?」
提到公事,他眼中掠过一丝锐利的光,但语气依旧沉稳:「还算顺利,有些技术壁垒在攻克。
港城这边,」他话锋一转,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带着一种穿透性的洞察力,
「许氏在九龙东的那块地,规划做了快两年,迟迟没有启动。周家在里面使了不少绊子吧?」
他果然敏锐,一针见血。那块临海的地皮位置绝佳,是许氏未来几年战略的重中之重。
周家利用姻亲关系和复杂的人脉,明里暗里设置障碍,拖延审批、抬高周边拆迁成本,
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我回来翻看资料时最头疼的问题之一。「是块硬骨头。」我坦言,
没有掩饰眉宇间的凝重,「周家盘根错节,有些钉子,拔起来伤筋动骨。」温时砚闻言,
嘴角似乎极轻微地向上牵了一下,那不是一个笑容,更像猛兽锁定猎物时的蓄势待发。
他走到落地窗前,望着窗外许家花园精心修剪的草木,背影挺拔如松。「骨头再硬,
总会有下嘴的地方。」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金石般的笃定,
「温氏在港口物流和高端制造方面的资源,或许可以和许氏在九龙东的布局,形成一些互补。
」他转过身,目光沉静地落在我脸上,不再绕弯子:「清音,有没有兴趣,
联手啃下这块硬骨头?」联手?温时砚和许氏?这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提议。
温氏在港城是新贵,但根基深厚,势头正猛,尤其在**关系和打通某些特殊关节方面,
有着许氏暂时欠缺的能量。而许氏,则拥有本土深厚的根基和那块无可替代的地皮。
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合作。这是一个信号。
一个温时砚旗帜鲜明地站在许家、站在我这一边的信号。是对周家,
尤其是对周景辰最有力的回击!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撞击着。
一丝久违的、带着锋利感的兴奋感,沿着脊椎悄然蔓延。我迎上他的目光,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问:「温先生,为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为什么选择我?仅仅是因为商业利益?
还是……他深邃的眼眸如同沉静的寒潭,清晰地映出我的影子。他没有回避我的探究,
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清晰:「因为,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清音。」
「等许家的大**,重新拿回属于她的权杖。」「也等你……真正看清楚,
谁才是那个值得的人。」最后那句话,他说得极轻,却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
在我心底漾开层层叠叠的涟漪。阳光透过玻璃,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投下淡淡的光影。
他站在那里,沉稳如山,眼神却带着一种近乎烫人的专注。书房里很安静,
只有我们两人的呼吸声。空气仿佛凝固了,又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无声地涌动、碰撞。
我看着他,没有立刻回应那个「联手」的提议。指尖无意识地抚过小腹,那里依旧平坦,
但一个决定却在心底清晰无比地成型。这个孩子,我要留下。不是因为周景辰。恰恰相反,
是为了彻底斩断与周景辰之间最后那点可悲的、生理上的联系。这是我的孩子,
只属于我许清音一个人的孩子。他会姓许,在许家的庇护和期待中长大,
继承许氏的一切荣光。周景辰?他不配做父亲,更不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
至于温时砚……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距离很近,
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那股清冽的松木冷香。我抬起头,直视他深邃的眼睛,
清晰地吐出两个字:「成交。」温时砚的眼中,瞬间燃起一簇明亮的光。他没有说话,
只是伸出了手。宽厚、干燥、指节分明的手掌,带着一种沉稳的力量感。我没有犹豫,
将自己的手放入他的掌心。他的手温热而有力,稳稳地包裹住我的。没有暧昧的摩挲,
只有一种郑重的、属于盟友的承诺。他微微收紧了一下,随即松开,动作干脆利落,
不带丝毫拖泥带水。「具体的方案,我会让助理整理好,尽快送来。」
他恢复了一贯的公事公办,但眼底那抹光并未散去。「好。」我点头。他离开后,
书房里似乎还残留着那股清冽的松木气息。我重新坐回宽大的扶手椅,拿起桌上的文件,
心境却已截然不同。那些冰冷的数字和复杂的图表不再是沉重的负担,
而是一块块等待我去征服的疆域。温时砚的行动力惊人。第二天下午,
一份详尽周密的合作方案草案就送到了我的案头。方案的核心是「双核驱动」
:温氏利用其在港口自动化物流和精密制造领域的优势,以及新近打通的高层关系,
垒;而许氏则发挥其在商业地产开发、高端酒店运营和顶级文化艺术资源整合上的深厚经验,
负责核心商业区的规划、招商和品牌打造。这份方案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
不仅精准地切中了项目当前的痛点,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双方的优势,规避了短板。
更关键的是,在股权分配和决策机制上,温氏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
将核心主导权明确地放在了许氏手中。「温先生很有魄力。」父亲许世昌翻看完方案,
摘下老花镜,锐利的目光看向我,「也很有诚意。清音,你怎么看?」「方案很完美。」
我放下手中的笔,「温氏能解决我们最头疼的外部阻力,
让我们集中精力在项目本身的价值提升上。这是一场及时雨。」「嗯。」父亲沉吟片刻,
「时砚这孩子,心思深,但做事有章法,重信诺。他这次出手,不仅仅是商业考量。」
他的目光意有所指地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我垂眸,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避开了父亲探究的眼神:「我知道。所以,我更要把九龙东做成一个标杆。
这不仅关乎许氏的未来,也关乎……我们合作的基石。」父亲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放手去做吧。许家,永远是你的后盾。」
有了温氏这柄锋利的刀,九龙东项目的推进势如破竹。那些曾经如同铜墙铁壁的审批关卡,
在温时砚亲自斡旋下,竟然以一种令人咋舌的速度被逐一攻克。周家设置的重重障碍,
在温氏强大的资源和精准的策略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项目正式启动的那天,
举行了盛大的奠基仪式。镁光灯下,我和温时砚并肩而立,手握缠着红绸的铁锹,
为奠基石培下第一铲土。无数镜头对准我们,快门声如同暴雨。
我穿着剪裁利落的白色高定西装,小腹依旧平坦,但眉宇间是久违的、锐利逼人的神采。
温时砚站在我身侧,深色西装衬得他肩宽腿长,沉稳如山。他微微侧身,
替我挡住了侧面有些刺眼的阳光,姿态自然而体贴。台下,前排的嘉宾席里,
周景辰赫然在座。他是主办方之一(虽然已被边缘化),不得不出席。
他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死死地盯着台上并肩而立的我们,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