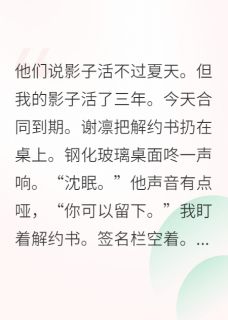
他们说影子活不过夏天。但我的影子活了三年。今天合同到期。谢凛把解约书扔在桌上。
钢化玻璃桌面咚一声响。“沈眠。”他声音有点哑,“你可以留下。”我盯着解约书。
签名栏空着。他名字已经签好。谢凛。钢笔字。力透纸背。“加钱?”我问。他手指顿了下。
“……什么?”“续约得加钱。”我掏出手机看时间,“超时要加收百分之二十。
合同附件三第七条。”谢凛突然笑了。他很少笑。嘴角扯开一点。像刀划了道口子。“行。
”他说,“翻倍。”我摇头。“不续。”空气凝固了。水晶吊灯的光刺得眼睛疼。
这别墅什么都好。就是灯太多。“理由。”他声音冷下去。“钱够了。”我实话实说,
“当初说好三百万。你多给了五十万。够花。”谢凛盯着我。像看个怪物。他眼珠很黑。
看人时像两口深井。温意就说过。她最爱他这双眼。温意。谢凛心尖上的人。
我的买家秀版本。“够花?”他重复一遍,“你知道温意一条裙子多少钱?”“知道。
”我说,“上个月你给她拍的那条古董裙。七百六十万。刷的副卡。我签收的。
”谢凛脸色变了变。“那点钱够你活几天?”他语气带刺。我认真算了算。“按现在的物价,
活到死没问题。”顿了顿,“如果死得不太晚的话。”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过大理石地。
刺啦一声。“沈眠!”他很少连名带姓叫我。一般叫我“过来”。或者“倒酒”。
我坐着没动。等他下文。“你就这么想走?”他胸口起伏。像被气着了。
“这三年我对你不好?”“好。”我说,“吃穿住行。顶级配置。
”“那你——”“合同到期了。”我打断他,“谢先生。买卖不成仁义在。别搞太难看了。
”他死死盯着我。像要把我盯穿。过了足足一分钟。他抓起解约书。唰唰签上名。
摔到我面前。“滚。”他说。我拿起解约书。检查签名。谢凛。没签错。
银行转账通知正好进来。尾款到账。我收起手机。“再见,谢先生。”我说。他没回头。
背对着我。肩膀绷得很紧。像块冷硬的石头。我拎起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只有一个。
二十寸。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走出别墅大门时。天快黑了。晚风吹过来。
有点凉。我缩了缩脖子。叫的车到了。司机帮我把箱子放进后备箱。“姑娘,去哪儿?
”他问。“最近的地铁站。”我说。车开出去时。我回头看了眼。三楼书房亮着灯。
窗帘缝里。有个黑影站着。我转回头。摇上车窗。再见了。谢凛。再见了。替身生涯。
我在城中村租了个单间。三十平。带个小阳台。月租一千二。房东阿姨人不错。
“小姑娘看着面善。”她收钱时说,“押一付三。给你便宜两百。”我道了谢。接过钥匙。
铁钥匙。磨得发亮。房间很干净。白墙。水泥地。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没了。
我把箱子打开。衣服挂进衣柜。化妆品扔进抽屉。最后拿出一个铁盒。打开。
里面是张银行卡。还有解约书。折得整整齐齐。余额通知短信还在。三百五十万零八千。
零头是这三年攒的“小费”。谢凛给钱大方。指甲缝里漏点就够我活。我把卡收好。
扑到床上。床板硬邦邦。我满足地叹了口气。终于。可以当咸鱼了。计划早就定好了。
第一步。睡三天。第二步。吃三天垃圾食品。第三步。躺着看三天狗血剧。完美。我闭上眼。
几乎立刻睡着。三年没睡过踏实觉。谢凛夜猫子。他睡我就得“醒着”。温意睡眠浅。
替身也得“浅”。现在。我的眼皮沉得像灌了铅。这一觉昏天黑地。醒来时。阳光刺眼。
摸过手机看。下午两点。睡了快二十个钟头。肚子咕咕叫。我爬起来。套了件宽大T恤。
头发随便一抓。趿拉着拖鞋下楼。城中村像个巨大的蜂巢。巷子窄。电线乱拉。
小餐馆挤在一起。油烟味混着方言吆喝声。鲜活。热闹。我找了家牛肉面馆。十五块一大碗。
汤浓肉厚。辣子油汪汪。正吸溜面条。手机震了。陌生号码。本地。我犹豫了下。接起来。
“沈**?”是个女声。温温柔柔的。我筷子停了。这声音太熟。熟得我后背发毛。温意。
“哪位?”我装傻。电话那头轻轻笑了。“我是温意。谢凛的……”“前女友。
”我替她说完。嗦了口面。声音有点含糊。“有事?”温意顿了顿。似乎没料到我这么直接。
“听说你和阿凛解约了?”消息真灵通。才一天。“嗯。”我专心挑碗里的葱花。
“钱货两讫。”“我想和你见一面。”她语气放软,“有些事……电话里说不方便。
”“不方便就别说了。”我又喝了口汤。满足地哈气。“我挺忙的。”“忙?
”她尾音扬起一点。带着恰到好处的疑惑。像羽毛搔过耳膜。谢凛就吃这套。“忙着吃面。
”我说,“老板!再加个卤蛋!”电话那头沉默了。估计温大**没被人这么晾过。
“沈**。”她声音淡了点,“地址给我。我过去找你。很快。”“城中村。七弯巷口。
王记牛肉面。”我报得干脆,“给你二十分钟。面坨了不好吃。”挂断电话。卤蛋正好送来。
我戳开。溏心的。流黄。十五分钟后。一辆锃亮的黑色宾利。卡在了巷子口。太宽了。
进不来。司机小跑着开门。温意下车。米白色羊绒大衣。珍珠耳钉。头发一丝不乱。
像幅精修过的画。跟油腻腻的巷子格格不入。她踩着细高跟。小心避开地上的水渍。
眉头微蹙。我在油腻腻的塑料凳上。抬了抬下巴。“坐。”她看着那张泛着油光的凳子。
没动。“站着说也行。”我咬了口卤蛋。黄流到手上。我舔了舔。温意眼角抽了下。
“你变了。”她突然说。“钱赚够了。”我含糊道,“原形毕露。”她盯着我。
目光像小刷子。在我脸上扫来扫去。以前她就这样“验货”。看我和她像不像。
够不够格当替身。“阿凛很难过。”她终于开口。“哦。”我吸溜面条。“替我道个歉?
”“他需要你。”她声音很轻。带着蛊惑。“回来吧。条件随你开。”我放下碗。擦了擦嘴。
“温**。你搞错了。”她微微歪头。露出一点恰到好处的困惑。这个角度。
侧脸轮廓和我有七分像。“他需要的不是我。”我看着她的眼睛,“是你。你回来了。
我这个替身该退场了。”温意嘴角弯了弯。没多少笑意。“他习惯你了。”“习惯能改。
”我摸出手机扫码付钱。“老板!钱转过去了啊!”“沈眠!”温意声音拔高一点。
又迅速压下去。维持着体面。“就当帮我一个忙。他最近……状态很不好。”“找心理医生。
”我站起来。凳子腿刮地。“比找我管用。”“五百万。”她突然说。我脚步没停。
“一千万!”她声音有点急。我走到巷子口。宾利还堵着。后面堵了好几辆小电驴。
滴滴按喇叭。“让让。”我对司机说。温意追上来。高跟鞋敲着水泥地。“沈眠!
你想要什么?你说!”我停下。回头看她。阳光有点烈。她眯着眼。精心描画的脸上。
终于露出一丝裂痕。“我想要……”我拖长声音。她屏住呼吸。“当条咸鱼。”我说完。
侧身从车缝里挤出去。“沈眠!”她在我身后喊。我没回头。拐进旁边小超市。
买了根最贵的雪糕。三块五。巧克力脆皮的。撕开包装。咬一口。甜得齁嗓子。自由的味道。
**好。咸鱼的日子。像泡在温水里。每天睡到自然醒。楼下买两个包子。一杯豆浆。
三块五。中午外卖。二十块以内。晚上煮个面。加个蛋。五块。剩下的时间。躺着。刷剧。
看小说。阳台有把旧藤椅。天气好就窝在里面晒太阳。像只懒猫。手机?静音。
谢凛打过几个电话。陌生号码。我一概不接。温意发过几条短信。语气从恳求到质问。
最后一条是:“你会后悔的。”我删了。没回。后悔?我摸着卡。硬硬的还在。
三百多万在银行里躺着。利息够我活。后悔个屁。直到那天下午。门被砸响。不是敲。是砸。
哐哐哐!震得门框掉灰。我从狗血剧里抬头。皱眉。趿拉着拖鞋去开门。“谁啊?
拆——”门拉开。后半句卡在喉咙里。谢凛站在门口。黑西装。没打领带。
衬衫扣子扯开两颗。头发有点乱。眼下发青。下巴冒出一层胡茬。身上一股浓重的酒气。
他死死盯着我。眼睛里有红血丝。像熬了几宿的狼。“你怎么找到这的?”我下意识想关门。
他一只脚卡进来。手抵住门板。力气大得惊人。“跟我回去。”他声音沙哑得厉害。
像砂纸磨过。“回个屁。”我用力推门。纹丝不动。“谢凛!松手!”他不但不松。
整个人往里挤。酒气混着他身上惯用的雪松香水味。劈头盖脸罩下来。
“**——”我火了。抬腿想踹他膝盖。他猛地抓住我手腕。攥得死紧。骨头生疼。
“沈眠!”他低吼。眼睛红得吓人。“你玩够没有?!”我被他拽得一个趔趄。
后背撞到墙上。咚一声闷响。疼得我倒抽冷气。“操!放手!”我抬脚狠狠踹过去。
他闷哼一声。小腹挨了一下。手劲松了点。我趁机抽出手腕。皮肤上已经一圈红印。
“滚出去!”我指着门外。气得手抖。“不然我报警!”谢凛靠着门框喘气。额角有汗。
刚才那下踹得不轻。他缓了几秒。抬头看我。眼神又沉又暗。“报警?”他扯了下嘴角。
“报什么?前金主骚扰前替身?”“非法闯入!”我摸出手机。手指发抖地按号码。
“私闯民宅!”他看着我。突然笑了。笑得有点瘆人。“沈眠。你这屋子。月租多少?
”“关你屁事!”“一千二。”他准确报出来。目光扫过狭窄的房间。“这床。
睡两个人挤不挤?”我按号码的手指顿住了。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你调查我?
”他不答。自顾自说下去。“房东姓李。本地人。有个儿子在上初中。你押一付三。
给了四千八。”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我刚吃完没收的泡面桶上。“伙食费一天三十。
楼下王记面馆。你最爱加卤蛋。溏心的。”我后背发凉。汗毛都竖起来了。“谢凛!
你到底想干什么?!”他往前一步。逼得很近。酒气喷在我脸上。“跟我回去。
”他又重复一遍。声音低哑。“你要什么。我都给。”“我要你滚!”我吼回去。
他眼神一暗。伸手又要抓我。我猛地举起手机。屏幕亮着。“110”三个数字已经按好。
大拇指悬在拨号键上。“你再碰我一下。”我盯着他。“我立刻按下去。”他动作僵住了。
手停在半空。死死盯着我的手指。胸膛剧烈起伏。像头困兽。僵持。空气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楼道里传来脚步声。隔壁大叔下班回来了。哼着不成调的歌。谢凛眼神闪了闪。
那股骇人的戾气。慢慢收回去一点。他放下手。退后一步。“沈眠。”他声音疲惫不堪。
“别逼我。”“是你别逼我。”我手指稳稳按在拨号键边缘。“滚。”他深深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复杂得我读不懂。有愤怒。有不甘。好像……还有别的什么。我看不清。也不想看清。
他转身走了。背影有点晃。脚步虚浮。消失在楼梯拐角。我砰地关上门。反锁。加防盗链。
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心脏还在狂跳。手心里全是冷汗。疯子。谢凛就是个疯子!
我以为他消停了。至少安静了几天。直到那天早上。我下楼买豆浆。
看见巷子口停着那辆眼熟的宾利。车窗贴着深色膜。看不清里面。但我有种强烈的预感。
果然。豆浆买回来。车还在。油条啃完。车还在。中午下楼取外卖。车还在。
像个沉默的黑色怪物。盘踞在狭窄的巷口。我目不斜视地走过去。车窗突然降下一半。
谢凛坐在驾驶位。侧脸线条冷硬。戴了副墨镜。遮住大半张脸。看不出表情。“豆浆好喝吗?
”他突然开口。声音没什么起伏。我没理他。拎着外卖盒往回走。“那家川菜馆的毛血旺。
”他在我身后说。“你点了特辣。”我脚步没停。后背却像被针扎了一下。他知道。
他什么都知道。下午。我去小超市买卫生巾。货架前。手机震了下。陌生号码短信。
“苏菲弹力贴身。夜用超长。你惯用的牌子。第三排左边。”我猛地回头。超市门口空荡荡。
只有老板娘在嗑瓜子看剧。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来。我胡乱抓了一包别的牌子。冲到柜台。
扫码付款。手指都在抖。回到家。反锁门。心还在怦怦跳。我冲到窗边。
撩开窗帘一角往下看。那辆宾利。还停在老位置。像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我拉上窗帘。
在屋里转了两圈。不行。这样下去不行。报警?没证据。他没闯进来。没碰我。
只是“停”在那里。警察来了能说什么?搬家?刚交的房租。押金还在房东那。再说。
他能找到这里。就能找到下一个地方。我盯着那张银行卡。脑子里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
跑路。跑得远远的。手机又震了。还是陌生号码。“别想着跑。沈眠。
”短信内容让我血液都凉了。“你跑不掉。”我冲到窗边。猛地拉开窗帘。楼下。
宾利驾驶座的车窗降下。谢凛正抬头看上来。墨镜反着光。看不清眼神。
但嘴角似乎勾了一下。冰冷。笃定。我狠狠摔上窗帘。谢凛开始变本加厉。先是门口堆东西。
一大早。门口放了个巨大无比的奢侈品纸袋。打开。里面是条裙子。温意同款。
七百六十万那条的复刻版。吊牌还在。价格后面一串零。我直接塞进楼道的旧衣回收箱。
第二天。门口是个丝绒首饰盒。打开。里面躺着条钻石项链。主钻亮得晃眼。
旁边卡片上打印着:“配那条裙子。”我转手挂上二手网站。标价一折。秒没。
钱捐了流浪动物救助站。第三天。门口没东西了。我刚松了口气。中午。有人敲门。不是砸。
很礼貌。开门。是个穿着考究的中年男人。笑容可掬。“沈**您好。我是谢先生的助理。
姓陈。”他递上一份文件。“谢先生吩咐。把这套房子的过户文件给您送来。您签个字就行。
”我低头看。文件抬头是本市一个著名的高档小区。一套两百多平的大平层。
市值……后面一串零看得我眼花。“什么意思?”我皱眉。“谢先生说。”陈助理笑容不变。
“您住在这里。实在委屈了。这套房子环境好。安保完善。您搬过去。对大家都方便。
”我盯着他。“如果我不签呢?”陈助理笑容淡了点。“沈**。谢先生也是为您安全考虑。
这种地方……鱼龙混杂。您一个女孩子。不安全。”威胁。**裸的威胁。我点点头。
接过文件和笔。陈助理脸上刚露出点欣慰。我当着他的面。把文件撕了。撕得粉碎。
扔进他怀里。“回去告诉他。”我说,“再敢骚扰我。我把他送的东西全挂网上。
标题就叫‘谢氏总裁骚扰前替身实录’。”陈助理的脸。瞬间精彩纷呈。
我以为这招能让他收敛点。我错了。第四天早上。我被一阵嗡嗡声吵醒。声音不大。
但持续不断。像苍蝇在耳边飞。我烦躁地睁开眼。循着声音找。声音来自空调挂机旁边。
墙角。天花板和墙壁的夹角处。一个不起眼的黑色小圆点。闪着微弱的红光。针孔摄像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