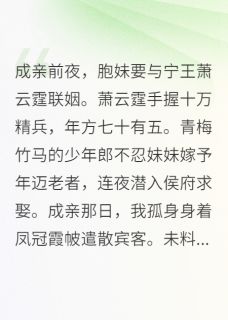
成亲前夜,胞妹要与宁王萧云霆联姻。萧云霆手握十万精兵,年方七十有五。
青梅竹马的少年郎不忍妹妹嫁予年迈老者,连夜潜入侯府求娶。成亲那日,
我孤身身着凤冠霞帔遣散宾客。未料到,一位佝偻着背的老王爷拄着龙头杖缓缓行来,
掷下一枚雕龙玉佩:“姜姑娘,你的情郎夺了本王的王妃,本王要你取而代之。意下如何?
”我轻抬下颌:“即刻行礼?礼乐尚在。”萧云霆听我这么说,
枯槁的手指摩挲着龙头杖笑了:“这不急。”他浑浊的目光扫过满地狼藉的喜堂,
杖尾随意挑开我头上的凤冠,珠翠哗啦啦坠了一地。这凤冠本就是侯府给妹妹的赝品,
我戴着不过充数,上头的珊瑚珠早被虫蛀得千疮百孔。我早该知道,陆明远从未真心待我。
萧云霆忽然冷笑一声:“姜姑娘,本王的聘礼从不寒酸,岂会让你在这破败祠堂成亲?
”他抬手示意,身后暗卫立刻呈上一方金丝檀木匣。“三日后,本王的王府张灯结彩,
亲事书已盖好玉玺,嫁衣也由云锦坊连夜赶制,如何?
”我垂眸望着匣中流光溢彩的赤金步摇:“王爷说什么便是什么。”萧云霆刚离开,
陆明远就闯了进来。我将雕龙玉佩攥得生疼,抬眼睨他:“陆公子,这亲事,结不成了。
”陆明远喉结滚动,轻声唤我:“阿晚,你别胡闹。”“阿柔才十六岁,萧云霆年逾古稀,
她嫁过去就是入虎口。”“我们自幼一起长大,我看着她长大,
实在无法眼睁睁看她跳进火坑。”“所以你就把我推进火坑?”我讥讽地笑出声,
“你可想过,我该如何面对满朝文武?
”陆明远眉头紧蹙:“我以为你会懂我的……”他向前一步,声音放软:“这么多年的情分,
你真忍心见死不救?”“阿柔身子弱,禁不起半点**,
她要是……”我打断他的话:“所以,你的未婚妻能被当众抛弃,姜柔却金贵得碰不得?
”陆明远脸色骤变:“阿晚,你别不讲理!”“你知道阿柔多依赖我,她若出了事,
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他伸手想抓我的手腕:“你是我的人,这不会变。等安顿好阿柔,
我一定……”我突然大笑起来,笑得眼眶发酸。然后,我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陆明远踉跄后退,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你的意思是,成亲当日丢下我,
转头去娶姜柔,我还得巴巴等着你的施舍?”我逼近他,“等你腻了,再赏我个侍妾的名分?
”陆明远恼羞成怒,眼底泛起狠意:“姜晚,别给脸不要脸!
”“整个京城都知道你是我的人,被退亲事的残花败柳。没了我,你以为谁还会要你?
”“我肯给你留条活路,是你不识好歹!”他甩袖欲走,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才惊觉指甲已深深掐进掌心。曾经,陆明远不是这样的。我们青梅竹马,私定终身。
他会在我生辰时踏雪寻梅,会在我受委屈时将我护在身后。
但一切都在姜柔被接入侯府后变了。姜柔说害怕黑夜,要陆明远彻夜相伴。
他开始日日守在她的小院,陪她抚琴作画。她做噩梦,他便衣不解带地守着。有一次,
我感染风寒咳血,派人去请他。他却语气不耐:“阿柔正在发热,你别添乱!自己找大夫去!
”我蜷在床榻上,听着窗外的雨声,突然就明白了。原来在他心里,
我早就是个无关紧要的人了。隔日,萧云霆的聘礼便入了侯府。
整条朱雀大街被玄铁甲车堵得水泄不通。车厢门一掀,
赤金香炉、白玉屏风、西域进贡的夜光珠,皆是内库里珍藏的贡品。我娘捧着一对羊脂玉镯,
指尖抖得几乎握不住:“这可是前朝皇后的陪嫁!是宫里的东西啊!
”我爹摩挲着鎏金镶宝石的太师椅,笑得合不拢嘴:“瞧瞧宁王这排场,阿晚嫁过去,
妥妥的王府主母!”“嫁得好!嫁得好啊!”我立在廊下,看着满地珠光宝气,
眼神凉得像冰。他们欢喜得如同中了状元,而我不过是用来换前程的筹码。
我爹拍着我的肩:“阿晚,入了王府要守规矩,伺候好王爷。”“等王爷百年之后,
王府的家业分你一份,咱们姜家就能光耀门楣了!”我静静听着,喉间泛起苦涩。
这真的是我的父母?当初妹妹要嫁萧云霆时,他们哭天抢地,
说宁王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老怪物。轮到我,倒成了天大的造化?这时,
几个婆子躲在角门后窃窃私语:“听说老王爷油尽灯枯了。”“可不是,上个月咳血,
连着请了七个太医都没治好。”“指不定哪天就咽气了。”“新妇就要守寡,
这晦气事儿……”“守寡算什么?王府规矩森严,搞不好还要殉葬呢!”“哎哟,
前两任王妃下葬时,听说活埋了十八个丫鬟……”“那这姜家**……”我攥紧袖口,
面上仍是平静如水。殉葬?倒也解脱。反正这侯府里,我早就是个多余的人。
自从姜柔被接进府,她成了爹娘的心肝肉,我却成了府里的下人。她睡金丝楠木床,
用和田玉枕,院里四季都有新鲜的时花。我住的西厢房漏风漏雨,墙角爬满青苔,
冬天连炭火都分不到半盆。她想吃荔枝,爹娘派人快马加鞭从岭南运送。我想添件冬衣,
却被骂不知节俭。姜柔生辰,爹娘送她能照见人影的青铜大镜。而我,
连面巴掌大的铜镜都不配拥有。但此刻不同了。宁王送来的聘礼堆满三间库房,
那些我曾可望不可即的珍宝,如今触手可及。我随手拿起一支金凤钗,在鬓边比划。
我娘见状,脸色骤变:“放下!这是能乱动的吗?”我冷笑一声:“王爷送我的,
戴戴都不行?”她咬着牙忍下怒意:“戴归戴,仔细些别磕着碰着。”真是讽刺。
我又取出一顶九凤衔珠冠,端端正正戴在头上,对着铜镜扯出一抹冷笑。侯府容不下我,
王府未必是好去处。可至少现在,这些荣华富贵都是我的。要死,也得做个风风光光的鬼。
我满身珠翠踏出侯府,刚转过街角,便迎面撞见一辆熟悉的枣红马车。车帘挑起,
姜柔踩着金线绣鞋,环着陆明远的手臂款款而下。她瞥见我头上的九凤冠,先是一怔,
随即捂着嘴嗤笑出声:“姐姐这是唱哪出?莫不是把戏班子的行头偷出来了?
”她上下打量我周身珠翠,眼尾含着轻蔑:“这翡翠镯子绿得发灰,
怕不是街边摊子上的假货?妹妹这有对新得的镯子,
姐姐若是不嫌弃……”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对铜环,作势要往我手上塞。我冷眼看着她,
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她却歪着头,眼波流转:“姐姐莫要怨我,明远哥哥心疼我身子弱,
我也是没办法。”“往后咱们姐妹还能常常见面,只是……”她顿了顿,声音越发软糯,
“明远哥哥说先娶我入门,姐姐可要委屈些了……”我嫌恶地甩开她的手,铜环哐当落地。
姜柔惊呼一声跌坐在地,眼眶瞬间泛红:“姐姐为何推我?我知道你怨我,
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夜夜噩梦缠身,明哥哥不过是想多陪陪我……”陆明远几步冲过来,
狠狠将我搡开:“姜晚,你疯了?”“你明知阿柔受不得**,还要下狠手?
”他居高临下地睨着我,字字如刀,“等到时候进了陆家,你最好安分些。
”“后院柴房归你住,粗茶淡饭管饱。”“若是敢伤阿柔分毫,立刻给我滚!
”说罢他俯身抱起姜柔,语气陡然温柔:“别怕,咱们回家。”我立在原地,
看着姜柔伏在他肩头,回头冲我露出得意的笑。侯府嫡女的身份,早就是个笑话。
姜柔的娇弱,向来只在人前发作。当着爹娘和陆明远的面,她连说话都带着哭腔,
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背着人时,却会扯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姐姐怎么还不死?
留着占地方。”我向爹娘诉苦,却换来一顿责骂:“阿柔可怜,你就不能让着她?”如此,
我的胭脂水粉、首饰衣裳,一件一件都成了她的。在嫁入宁王府前,我路过绸缎庄,
想买匹月白软缎做件新衣。刚踏进门,便见陆明远陪着姜柔,各色绸缎在她面前堆成小山。
我刚走近,陆明远已将姜柔揽入怀中,冷冷开口:“这些都是阿柔的。”姜柔倚在他胸前,
眼含笑意:“姐姐也想要绸缎?”她拿起一匹猩红锦缎,掩唇轻笑:“只是这颜色,
姐姐怕是撑不起来。”“都说施施效颦,姐姐这般……”她突然从角落里翻出块粗麻布,
“倒不如这块合适,你看,又灰又糙,和姐姐多配啊!”我盯着她扭曲的笑脸,
心底一片冰凉。不再多言,转身离去。回府时,管家捧来个檀木匣:“**,
宁王送来了贺礼。”只见半人高的朱漆匣中,躺着一支通体莹润的玉簪。
羊脂白玉雕成的并蒂莲栩栩如生,最显眼处,刻着小小的“萧”字。
我的指尖抚过温润的玉面,胸腔里沉寂多年的某处,突然泛起一丝暖意。原来这世上,
真有人会把我的喜好,放在心上。那个老态龙钟的萧云霆,竟也有这般细腻的心思?三日后,
便是我与萧云霆大亲事的日子。这场亲事约,怕是正如府中传言,
不过是老王爷寻个活人殉葬。无所谓了。我这条命本就如风中残烛,陪葬也好,赴死也罢,
我照单全收。迎亲的仪仗来了。百匹披红戴花的骏马在前开道,八抬金丝楠木大轿紧随其后,
队伍蜿蜒数里,将整条朱雀大街堵得水泄不通。轿帘掀开,两个嬷嬷福了福身:“姜姑娘,
请上轿。”我身着云锦嫁衣,莲步轻移跨过门槛,正要踏入花轿,
忽听得街角传来一声暴喝:“姜晚!你这是要干什么?!”循声望去,陆明远身着玄色喜服,
胸前缀着的红绸花鲜艳刺目。他死死盯着我身上的嫁衣,眼底泛起血丝:“穿成这样来搅局,
你安的什么心?!”我冷眼看着他,未发一言。他越发癫狂,
额角青筋暴起:“是不是想让阿柔难堪?想用这种下作手段逼我回头?
”他突然转身面向围观百姓,高声嗤笑:“诸位瞧瞧,这就是侯府嫡女!
”“被退亲事后还不知廉耻,竟穿着嫁衣来抢亲!”“今日我要迎娶阿柔,
她却跑来丢人现眼!”话音未落,他猛然抓住我的手腕:“既然想你这么想引起我的注意,
我便遂了你的愿!”一声令下,身后家丁蜂拥而上,
伸手就要撕扯我的嫁衣:“扒了这**的衣裳!让她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我反手甩开家丁的脏手,语调冰冷如霜:“陆明远,我要嫁的人不是你。”四下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愣住了,连陆明远都瞪大了眼睛。他阴恻恻地开口:“你在说什么胡话?
”“还不赶紧帮姜**把身上的嫁衣脱了!”那些家丁再次围了上来。
一双双粗糙的手在我身上胡乱摸着,就在一双手伸到我胸前即将撕烂我的嫁衣时,
我惊恐大叫:“滚开!滚开!我是宁王妃!”众人吃惊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破空而来:“哪个狗胆包天的混账,敢动本王的王妃?”众人齐刷刷回头,
只见一位银发老者拄着龙头杖,缓步走来。他身着玄色蟒纹吉服,腰间玉佩泛着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