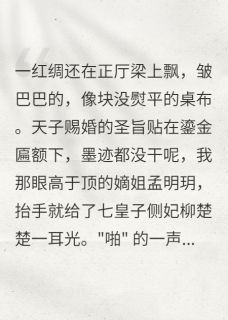
一红绸还在正厅梁上飘,皱巴巴的,像块没熨平的桌布。天子赐婚的圣旨贴在鎏金匾额下,
墨迹都没干呢,我那眼高于顶的嫡姐孟明玥,抬手就给了七皇子侧妃柳楚楚一耳光。
"啪"的一声脆响,落进满院桃花瓣里。七皇子赵珩踩着碎花瓣走过来,
玄色蟒袍扫过青石板,带起的风都透着冰碴子。他没看孟明玥煞白的脸,
径直走到我爹孟德昌面前,侍卫的刀"噌"地架上了尚书大人的脖子。"孟大人,
"他声音不高,却像冰锥往人骨头缝里钻,"令嫒伤了本王的人,本王卸她一条胳膊,
不过分吧?"我缩在假山后,指甲掐进掌心。看嫡母周氏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鬓角那朵珠花晃得人眼晕;看孟德昌气得浑身打颤,山羊胡翘得老高,
却只敢骂"荒唐";看孟明玥咬着嘴唇,嘴角哆嗦得像筛糠——这场景,
跟三年前我娘被打死那天太像了。只是这一次,我心里没怕,反倒有团野火在烧。
我要嫁给赵珩。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张嬷嬷死死按住。她枯瘦的手指掐着我胳膊,
疼得我倒抽冷气:"阿晚你疯了?那是皇子!捏死咱们跟捏死蚂蚁似的!
"我望着赵珩转身的背影,玄色披风在暮色里划出冷硬的弧度。他腰间玉佩晃了晃,
是块暖玉,雕的并蒂莲,俗气又扎眼——准是柳楚楚送的。是啊,他是皇子。
可只有攀附上这种人,才能把那些高高在上的,拽进泥里。二三日后,
周氏果然来了我那破偏院。她坐在唯一能看的梨花木凳上,金护甲敲着桌面,"嗒嗒"响,
每一声都像催命:"孟晚,把你记到我名下做嫡女,你娘的牌位也能进孟家祖坟。
"我低头绞着衣角,粗布衣裳磨得脖子痒:"母亲,
我娘她......她是犯了错的......""死都死了,哪来那么多讲究?
"周氏不耐烦地挥手,袖口的熏香呛得我鼻子疼,"替明玥嫁过去,皇后那边我打点好了,
保你没事。"我猛地抬头,眼里蓄满泪,
恰到好处露出几分惶恐:"皇后娘娘......她知道?""不然你以为这事儿能成?
"周氏嗤笑,唾沫星子溅到我手背上,"明玥是嫡女又怎样?惹恼了七皇子,谁保得住她?
你不一样,你命贱,耐摔打。"我咬着嘴唇,
半晌才磕了个头:"女儿......听母亲的。"她满意地走了,留下满室脂粉香,
和我嘴角压不住的冷笑。门槛外那丛野菊被她的裙摆扫了,蔫头耷脑的,像我那早死的娘。
原来皇后也默许了。看来那位柳侧妃,是真把中宫惹急了。接下来的日子,
我成了尚书府"二**"。周氏请了京都最好的教养嬷嬷,教我琴棋书画,
教我走路要像风拂杨柳,说话要像莺啼燕啭。嬷嬷总说我学得快,就是眼神太硬,
"像揣着刀子似的"。我只笑不语。这些,哪有在偏院看人脸色过日子难?
就像此刻窗台上那只麻雀,蹦蹦跳跳啄着米,看着自由,其实每一步都得瞅着人的脸色。
三大婚那日,红盖头遮了视线,却挡不住满院的喜庆气。唢呐吹得震天响,吵得人脑仁疼。
可这喜庆,跟我没关系。赵珩坐在喜案那头,连盖头都懒得掀。我透过红布缝隙瞅他,
他正把玩着那枚并蒂莲玉佩,指腹摩挲着花瓣,一下,又一下。"庶女替嫁,很得意?
"他的声音透过盖头传来,带着冰碴子。我自己掀开盖头,直视着他。烛光落在他脸上,
勾出高挺的鼻梁和紧抿的唇,确实是副好皮囊,可惜眼神太凉,像腊月里的井水。"是,
挺得意的。"我扯了扯嘴角,红嫁衣勒得胸口发闷。他明显愣了下,
许是没见过这么直白的新娘子。眉毛挑了挑,像受惊的鸟。我指尖划过喜服上的金线绣纹,
慢悠悠地说:"在偏院时,我常饿肚子。听说七皇子府的米缸,从来都是满的。
"赵珩的眉峰拧得更紧,像在看个贪慕虚荣的蠢货。他端起酒杯,酒液晃了晃,
映出他眼底的不屑。"但我知道殿下不想娶我。"我话锋一转,目光扫过他腰间那块玉佩,
"皇后赐婚难违,可若是我'病亡',再迎孟明玥入府,也不是不行。
"他终于正眼看我,眸色沉沉,像积了雨的云。"只是姐姐性子烈,怕是容不下柳侧妃。
"我端起合卺酒递过去,杯沿沾了点胭脂,"我不一样,我无依无靠,
只能靠着殿下活下去。"赵珩盯着我看了许久,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杯底重重磕在案上:"希望你说到做到。"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丫鬟慌张的通报:"殿下,
侧妃娘娘梦魇了!"赵珩起身就走,玄色披风扫过我的裙角,带起一阵冷风。
我看着他的背影,把杯里的酒慢慢喝完。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烧得人发烫。不急,
好戏才刚开始。院角那棵石榴树开得正艳,红得像血,我娘最喜欢这花。四进府半月,
我见过三次赵珩。一次是大婚,一次是给我分派住处,第三次,是他来问柳楚楚的起居。
"侧妃娘娘身子不适,这几日都没胃口。"我捧着账本,头也没抬。纸页边缘卷了角,
磨得手指疼。赵珩站在窗边,看着院外那棵半死不活的合欢树:"她向来娇气。
"树影落在他脸上,忽明忽暗的。"是啊,"我顺着他的话头,翻了页账本,
"所以府里的事,殿下还是别让她操心了。厨房说侧妃爱吃城南那家的杏仁酥,
我让人去买了些。"赵珩回头看我,眼神里多了点什么,像水里投了颗石子:"你倒懂事。
""能嫁给殿下,是我的福气。"我笑得温顺,心里却在冷笑。
柳楚楚是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掌家权攥得死紧,连我院里的炭火都要克扣,
仿佛我是来抢她东西的贼。她不知道,我要的从来不是这些。就像檐下那只蜘蛛,
结网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等猎物。几日后,我让人传话给柳楚楚:"城外桃花开得正好,
殿下说想陪您去散散心。府里琐事繁杂,怕累着您,不如就交给我打理?"柳楚楚果然炸了。
当天下午,就听说她和赵珩在马车上吵了一架,哭得肝肠寸断,说赵珩有了新人忘旧人。
丫鬟们私下嚼舌根,说侧妃把发簪都摔断了,碎珠溅了殿下一身。我抱着暖炉站在廊下,
听着风里传来的琵琶声——那是柳楚楚在院里弹琴泄愤,调子怨得很,像猫被踩了尾巴。
转身去了凉亭,煮了壶清酒等赵珩。酒壶上的花纹磨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铜色,
像我娘留下的那只镯子。五月色溶溶,赵珩果然来了。他闻到酒香,脚步顿了顿,
像被什么绊了下:"你倒清闲。""看兵书看入了迷。"我举了举杯,酒液晃出点来,
滴在石桌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殿下要不要尝尝?"他走近才看清我手里的书,
瞳孔微缩:"《孙子兵法》?""闲来无事翻翻。"我笑了笑,
书页间夹着片干枯的桃花瓣,是上次宴会上掉的,"殿下要是不嫌弃,不如我们摆一局?
"三盘棋后,赵珩看着满盘皆输的棋局,突然笑出声,
像冰块化了点缝:"你这哪是闲来无事。"我敛了笑容,指尖划过棋盘上的"帅位",
木头有点毛糙:"殿下精通兵法,却只能困在京都,不觉得可惜吗?"赵珩的脸色沉了下去,
像要下雨。他捏着棋子的手紧了紧,指节泛白。我知道戳中了他的痛处。皇帝皇后疼幼子,
从不让他涉险边关,连柳楚楚也总劝他安分守己。上次我听见她跟丫鬟说,"沙场多危险,
哪有府里舒服"。"禁军也是兵。"我给他斟满酒,声音轻得像月光,
"若是能在禁军里做出成绩,陛下未必不会动心。"他猛地抬头,眼里燃起我从未见过的光,
像星火燎原。"王妃,你......""我只是不想看殿下的才华被埋没。
"我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阴影,"毕竟,殿下若是龙游浅水,
我这个依附殿下的人,日子也不会好过。"赵珩一口喝干了酒,喉结滚动,
像有东西卡住:"你说得对。"那晚他留在凉亭很久,我们聊的都是排兵布阵,
直到晨露打湿了衣袍。离开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月光落在他眼里,亮得惊人。
廊下的灯笼晃了晃,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六赵珩果然向陛下请旨掌管禁军。皇帝虽意外,
却也给了他一小队人马操练。他像是变了个人,每日天不亮就去校场,回来便往我院里钻,
带着一身汗味和我讨论操练章程。身上的皂角香混着汗味,意外地不难闻。"这样调整阵型,
是不是更稳妥?"他铺开图纸,手指点在其中一处,纸被戳得有点皱。我凑过去看,
发丝不经意间扫过他的手背。他像被烫到似的缩了缩,耳根悄悄泛红,像染上了胭脂。
"殿下英明。"我指着另一处,那里有个墨点,像是不小心蹭上的,
"这里若是加派弓箭手,攻防会更均衡。"他盯着图纸,
声音却有些不自然:"就依你说的办。"府里的流言渐渐变了风向。下人们见了我,
腰弯得更低了;管事嬷嬷汇报工作时,也不再阴阳怪气。连门口那只总冲我龇牙的大黄狗,
见了我都摇尾巴。柳楚楚摔碎了三套茶具,我让人送去新的,附带一张字条:"天气干燥,
侧妃少动气,伤身子。"她的回信是一支断了的玉簪,用锦盒装着,派专人送来。
簪头的珍珠掉了,像只瞎了的眼。我笑着收进妆匣。匣子里还有我娘留下的半块铜镜,
照人模模糊糊的。很快到了我的生辰,赵珩送了支红宝石玫瑰簪,雕工精致,
一看就价值不菲。宝石红得像血,在阳光下有点晃眼。"殿下费心了。"我插在发间,
对着铜镜笑了笑。镜中的人影,眉眼像我娘,又不像。当晚,赵珩却宿在了柳楚楚院里。
听说柳楚楚心悸复发,哭得肝肠寸断,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丫鬟来报时,我正看着那支簪子,
宝石上沾了点指纹,擦了半天才掉。七第二天,全京都都在传七皇子正妃空有其名,
连生辰都留不住夫君。我去给皇后请安时,一路听着窃窃私语。"听说了吗?
七殿下根本不碰那位替嫁王妃。""毕竟是庶女出身,哪比得上柳侧妃青梅竹马的情分。
"说话的是户部侍郎家的夫人,珠翠满头,声音尖得像针。我目不斜视,走进凤仪宫时,
脸上恰到好处地带着几分憔悴。皇后宫里的熏香太浓,闻得人头晕。皇后放下茶盏,
叹了口气,茶沫沾在她唇上:"委屈你了。""能嫁给殿下,是臣妾的福气。
"我屈膝行礼,裙摆扫过地面,带起点灰尘,"侧妃身子弱,殿下多照看也是应当的。
"皇后看着我,眼神复杂,像看件没琢磨透的玉器:"你倒是懂事。"从宫里回来,
我便病倒了,高烧不退。浑身烫得像火烧,却觉得冷,盖了三床被子还发抖。
赵珩来看过一次,站在床边皱着眉,眉头拧成个疙瘩:"怎么病成这样?"我烧得迷迷糊糊,
着他的衣袖喃喃:"别告诉殿下......我没不高兴......"他的衣料很滑,
抓不住。他僵了一下,吩咐太医好生照看,转身去了书房。脚步声很重,像踩在我心上。
那夜,守夜的丫鬟在门外嚼舌根:"还真当自己是王妃?
连男人都留不住......"声音不大,却像蚊子似的钻耳朵。我听见赵珩的怒喝,
接着是瓷器碎裂的声音,刺耳得很。"拖下去,杖二十。"他的声音冷得像冰,
"以后谁再敢议论王妃,直接杖毙!"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赶紧闭上眼装睡。
眼睫毛上沾着泪,凉飕飕的。他坐在床边,替我掖了掖被角,指尖无意中碰到我的额头,
烫得他猛一缩手。"笨蛋。"他低声骂了一句,声音却软得像棉花。
我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像风拂过湖面。八病好后,赵珩来我院里的次数更勤了。
他不再只谈军务,有时会带些新奇玩意儿——城东铺子的糖糕,
甜得发腻;西域进贡的香料,闻着像庙里的味道;甚至还有一只雪白的波斯猫,
眼睛是蓝色的,像两块冰。"听说你喜欢清静。"他把猫塞进我怀里,耳根微红,
像被太阳晒过,"它不吵。"小猫蹭着我的手心,痒痒的。猫爪子上还沾着点灰,
大概是从哪个角落抓来的。我挠了挠它的下巴,它舒服得打了个呼噜。我抬头看他,
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脸上,柔和了他凌厉的轮廓。他鬓角有根白头发,不太明显。"谢殿下。
"他突然伸手,想碰我的发簪,指尖在半空停了停,又收了回去,
像被什么烫到:"那支玫瑰簪,还戴着呢?""殿下送的,自然要戴。
"我摸着冰凉的宝石,笑得温顺。宝石映出我的脸,有点变形。他低笑一声,
转身去看兵书,耳朵却一直红着。书角卷了边,像是常被人翻看,页脚还有点水渍,
不知是茶还是泪。柳楚楚的弟弟柳文轩开始在外面散播谣言,说我善妒成性,苛待侧妃。
听说他在酒楼里喝醉了,拍着桌子说要替他姐姐出头。赵珩听闻后,只皱了皱眉,
剥橘子的手没停:"小孩子不懂事。"橘子汁溅到他手背上,黏糊糊的。我没说话,
只是让人把柳文轩仗着皇子侧妃的名头,强抢民女的证据,悄悄送到了皇后宫里。
那姑娘家的爹来府里磕头时,额头磕出了血,染红了青石板。三日后,皇后的懿旨送到府里。
柳文轩因"恃宠而骄,败坏皇家名声",被杖责四十,扔进了大牢。听说打板子时,
他哭得像杀猪。九柳楚楚跪在赵珩面前哭,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殿下,文轩知道错了,
求您救救他!"她的发髻散了,钗子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赵珩看着我,眼神躲闪,
像做错事的孩子:"阿晚,这事......""殿下觉得该救吗?"我直视着他,
语气平淡,手里摩挲着那只猫,它正打盹,"强抢民女,按律当斩。母后只判了杖责,
已是开恩。"柳楚楚尖叫起来,声音划破耳膜:"是你!是你害我弟弟!"我没理她,
只看着赵珩:"殿下若是徇私,便是置国法于不顾。"赵珩闭了闭眼,像很累的样子,
终是对侍卫道:"送侧妃回院,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柳楚楚被拖走时,
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死死剜着我。裙摆扫过门槛,带起一片灰尘。赵珩走到我面前,
声音艰涩,像被沙子磨过:"委屈你了。""我不委屈。"我轻轻摇头,猫醒了,
伸了个懒腰,"只是怕殿下为难。"他伸手抱住我,力道很紧,
勒得我有点喘不过气:"以后,我护着你。"**在他怀里,
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皂角香混着橘子味,嘴角弯起一个无人察觉的弧度。窗外的麻雀又飞来了,
落在窗台上,歪着头看我们。这一步,走对了。十柳楚楚被禁足后,安分了许多。
听说她院里的花都蔫了,没人打理,像她的脸色。赵珩在禁军里做得风生水起,
皇帝几次在朝堂上表扬他,连带着看我的眼神也温和了不少。上次宫宴,还赏了我一对玉镯,
水头一般,胜在成对。中秋宴上,皇后特意让我坐在赵珩身边。桌上的月饼甜得发腻,
我没动。柳楚楚也来了,穿着素色衣裙,憔悴了不少,像朵快败的花。她看着我们交握的手,
眼底一片怨毒,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宴席过半,柳楚楚突然起身,裙摆扫过凳脚,
发出"吱呀"一声:"臣妾新学了一支舞,愿为陛下娘娘助兴。"音乐响起,
她在殿中翩翩起舞,身姿轻盈,宛如弱柳扶风。衣袖甩得太急,差点扫翻旁边的酒壶。
众人纷纷叫好,声音像潮水。赵珩也看得有些出神,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一曲舞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