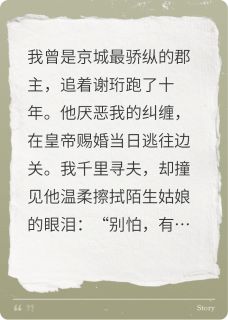
送嫁的队伍沉默地行进着。路途遥远而枯燥,日复一日地在单调的景色中跋涉。窗外,大胤熟悉的青山绿水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开阔的视野,越来越粗粝的风,空气也变得越来越干燥寒冷。初时还能看到零星的村落和田地,后来便只剩下广袤荒凉的戈壁和起伏的沙丘,偶有成群结队的商旅或零星的牧民与他们擦肩而过。
护送我的使节和兵士们,神情也日益紧绷。越靠近边境,空气中弥漫的那种无形的紧张感就越发明显。探马往来穿梭的次数变得频繁,传递着前方未知的消息。队伍的气氛压抑得如同绷紧的弓弦。
我大部分时间都蜷在车厢的软榻上,厚重的车帘隔绝了大部分风沙和景象。心,早已沉入一片无波无澜的深潭。嫁衣的沉重,凤冠的束缚,还有脸上那层厚厚的脂粉,都像一层厚厚的茧,将我包裹其中,麻木地承受着这漫长的放逐。
不知走了多少天,当车轮碾过地面的声音变得沉闷,仿佛踏上了某种特殊的土地,速度也明显放缓时,车厢外传来使节刻意压低却难掩紧张的禀报声:“公主殿下,我们已进入北狄境内。再行半日,便可抵达王都了。”
北狄……终于到了。
我微微动了动有些僵硬的手指,却没有掀起车帘去看一眼外面这片即将成为我囚笼的土地。只是下意识地,又摸了摸袖中那支始终贴身藏着的、冰冷的断翅凤凰步摇。
又颠簸了许久,当车驾终于完全停下,外面传来一阵阵嘹亮的号角声、整齐划一的甲胄碰撞声和一种我听不懂的、低沉而充满力量的呼喊声时,我知道,王都到了。
车门被从外面恭敬地打开。一股凛冽干冷的、带着陌生尘土和皮革气息的风猛地灌了进来,吹得我厚重的嫁衣衣袂翻飞。车帘被侍从高高挑起。
刺目的天光让我微微眯起了眼。适应了片刻,才看清眼前的景象。
没有想象中的巍峨宫殿,眼前是一片极其辽阔、由巨大白色巨石铺就的广场。广场尽头,矗立着一座风格迥异于大胤的宏伟建筑。巨石垒砌,线条粗犷而硬朗,殿顶覆盖着深色的瓦片,在阳光下反射着冷硬的光泽。殿前,矗立着一根根雕刻着狰狞猛兽图腾的巨大石柱,充满了一种原始的、磅礴的力量感。
广场两侧,肃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北狄士兵。他们身形高大魁梧,穿着暗色的皮甲或金属甲胄,手持长矛或弯刀,面容粗犷,眼神锐利如鹰,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审视和野性的气息。此刻,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如同实质的针芒,刺得我**在外的皮肤阵阵发紧。
这就是北狄的王庭。粗犷,冰冷,充满了压迫感。
一个身着北狄高阶官服、须发皆白的老者快步走到车前,躬身行礼,用带着浓重口音但还算清晰的大胤官话说道:“恭迎大胤明懿公主殿下!请殿下移步,觐见吾王!”
我深吸了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得肺腑生疼。扶着侍从伸来的手臂,那侍从的手也带着粗粝的茧子。我缓缓地、竭力维持着仪态地走下车驾。厚重的嫁衣裙摆拖曳在冰冷的白石地面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在两侧士兵如同实质的、刀锋般的目光注视下,我一步一步,朝着那座粗犷宏伟的巨殿走去。每一步都踏在冰冷的石板上,也踏在沉沦的心上。殿门高大幽深,像巨兽张开的口。门内光线略显昏暗,弥漫着一种皮革、金属和某种不知名香料混合的、陌生而沉重的气息。
引路的老者停在殿门外,躬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我定了定神,挺直了脊背,独自一人,踏入了那片象征着未知命运的巨大阴影之中。
殿内的空间比外面看到的更加恢弘空旷。数十根两人合抱粗的巨大石柱支撑着高耸的穹顶。地面铺着打磨光滑的深色石板,光可鉴人。两侧侍立着北狄的文武官员,穿着皮毛或皮质、色彩浓重的官服,同样投射来各种复杂难辨的目光——好奇、审视、轻蔑,甚至还有毫不掩饰的敌意。
光线从高处狭长的窗棂透入,形成一道道斜斜的光柱,切割着殿内略显昏暗的空间。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柱中飞舞。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大殿尽头最高处吸引。
那里是一个数级台阶抬高的宽阔平台。平台中央,摆放着一张巨大的、由整块深色岩石雕琢而成的王座。王座样式古朴粗犷,扶手雕刻成猛兽头颅的形状。
王座之上,坐着一个人。
距离尚远,殿内光线又暗,我看不清他的面容。只看到一身玄黑色的厚重王袍,袍身上用暗金色的丝线绣着繁复而狰狞的图腾。他身形异常高大挺拔,即使坐着,也给人一种渊渟岳峙般的压迫感。一手随意地搭在王座冰冷的扶手上,另一只手似乎支着下颌,姿态看似慵懒,却散发着一种掌控一切的、令人心悸的威仪。
整个大殿死一般寂静,只有我裙裾拖过地面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声,在空旷中显得格外清晰。
我一步步向前走,按照之前学过的、生疏的北狄礼节,在距离王座约十步之遥的地方停下。双手交叠于身前,微微屈膝,垂下眼睑,用尽全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大胤明懿公主萧氏,奉旨入狄和亲,拜见……”我顿了一下,那个陌生的称谓在舌尖滚了滚,“拜见陛下。”
话音落下,大殿里依旧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来自王座方向的那道目光,如同实质般落在我身上,带着一种沉甸甸的、穿透性的力量,仿佛要将我整个人从里到外看个通透。
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息都变得无比漫长。
就在我几乎要被这无形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时,王座之上,终于传来了声音。
那声音不高,低沉,带着一种奇特的沙砾质感,却异常清晰地穿透了大殿的寂静,像冰冷的金属刮过石板:
“把头抬起来。”
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意味。
我的指尖在宽大的袖中猛地蜷缩了一下,指甲掐进掌心。深吸了一口气,我慢慢抬起头,目光迎向王座的方向。
光线依旧昏暗,王座上的人影轮廓分明。他微微前倾了身体,那张脸终于从高处的阴影里清晰地显露出来。
棱角分明的下颌线,紧抿的薄唇透着冷硬的弧度。高挺的鼻梁……再往上……
当我的目光触及他完整面容的刹那,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巨手狠狠攥住,骤然停止了跳动!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张脸……虽然比记忆中成熟了许多,褪去了所有属于草莽的粗粝,被一种深沉冷硬的帝王威仪所取代,眉宇间更是多了一道斜飞入鬓的浅淡疤痕,平添了几分凌厉……
但那五官的轮廓,那双深邃沉静、此刻正牢牢锁定我的眼睛……还有那微微勾起的、带着一丝若有似无、近乎玩味的唇角弧度……
分明是……分明是当年在匪徒刀下救了我,又塞给我染血银子的那个……铁面草寇!
记忆的碎片如同被飓风卷起,疯狂地在脑海中冲撞:隘口里冰冷的刀光,飞溅的鲜血,他沉静如古井的眼,塞到我手里带着血污的银子,还有那句低沉沙哑的“走吧……边关不是你能去的地方……”
是他!竟然是他?!
巨大的震惊和荒谬感如同滔天巨浪,瞬间将我吞没!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思维都停止了运转,只剩下那双深邃锐利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清晰地倒映着我此刻苍白失魂的脸。
王座上的男人,北狄的新君,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许久,似乎在欣赏我瞬间崩塌的表情。然后,他缓缓地、缓缓地站起了身。
玄黑色的王袍垂落,勾勒出他高大挺拔的身形。他一步一步,沉稳而缓慢地走下那几级石阶,朝着僵立在殿中的我走来。
沉重的皮靴踏在光滑的石板上,发出清晰而规律的“嗒、嗒”声,每一步都像踩在我骤然失序的心跳上。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距离很近,近到我几乎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着冷冽皮革和淡淡龙涎香的、极具压迫感的气息。高大的身影投下的阴影,将我完全笼罩其中。
他微微俯身,那张曾隐于铁面之后、如今却掌控着整个北狄命运的脸,靠近了我。深邃的眼眸里,清晰地映着我惊魂未定、妆容也掩饰不住苍白的脸。嘴角那一抹玩味的弧度加深了些许,低沉沙哑的嗓音,带着一种久别重逢般的熟稔,清晰地钻入我的耳膜:
“郡主,”他刻意停顿了一下,声音里似乎含着一丝极淡的笑意,“别来无恙?”
“郡主……别来无恙?”
低沉沙哑的嗓音,带着一种久别重逢般的熟稔,却又裹挟着属于帝王的沉沉威压,如同淬了冰的细针,狠狠扎进我的耳膜,也扎穿了我勉力维持的最后一点平静。
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失序地擂动,震得耳膜嗡嗡作响。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四肢百骸一片僵冷。我死死地盯着眼前这张脸——这张褪去了铁面遮掩,被岁月和权力打磨得更加深刻冷硬,却又无比清晰地烙印着隘口血腥记忆的脸!
是他!那个在绝望中递给我一线生机,又用冰冷话语将我推回深渊的铁面人!那个塞给我染血银子、告诫我边关凶险的草寇!
他……竟然是北狄的新君?!
巨大的荒谬感和一种被命运戏弄的眩晕感如同巨浪,瞬间将我吞没。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语言、所有的反应都凝固了。我只能僵硬地站着,像一尊被钉死在原地的石像,任由他带着审视和玩味的目光,如同冰冷的探针,在我脸上来回逡巡。
他俯身的姿态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玄黑的王袍袖口处,用暗金丝线绣着的狰狞兽纹近在咫尺,仿佛随时会扑噬而来。那股混合着冷冽皮革与淡淡龙涎香的陌生气息,霸道地侵占了周围的空气,让我几乎窒息。
时间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扭曲。大殿里死一般的寂静,两侧北狄臣子们投来的目光如同芒刺在背,充满了探究、惊疑和毫不掩饰的敌意。
“怎么?”他的声音再次响起,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尾音微微上扬,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嘲弄,“朔风城一别,不过数载,郡主竟认不出故人了?还是说……”他刻意停顿,目光扫过我身上繁复沉重的大胤嫁衣,“这身凤冠霞帔,重得让郡主连旧识都忘了?”
朔风城!
这三个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心尖!瞬间将我拉回那个冰冷刺骨的黄昏,断墙残垣后,谢珩温柔地为阿宁拭去眼泪的画面!那份锥心刺骨的羞辱和绝望,如同跗骨之蛆,在这一刻被眼前这个男人的话语,**裸地撕开!
一股难以言喻的屈辱和冰冷的怒意猛地从心底窜起,瞬间冲散了最初的震惊和僵硬。血液重新开始流动,带着一种近乎毁灭的灼热。
我猛地抬起头,迎上他深邃锐利、带着审视的目光。脸上厚厚的脂粉也掩盖不住瞬间褪尽的最后一丝血色,但眼神却如同淬了火的寒冰,冰冷而锐利地回视着他。
“陛下说笑了。”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稳,甚至带着一丝刻意的清冷疏离,每一个字都像冰珠砸落地面,“明锦此来,只为两国邦交之礼,奉旨和亲。过往萍水之缘,于国事无益,不敢劳陛下挂怀。”
我将“奉旨和亲”、“两国邦交”咬得极重,是在提醒他,也是在提醒自己此刻的身份——我是大胤送来的和亲公主,而他,是北狄的君王。过往的一切,无论是救命之恩还是草寇身份,在这冰冷的政治联姻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甚至……不合时宜。
他似乎没料到我会如此回应,眼中那丝玩味的光芒闪了闪,随即被一种更深沉、更莫测的情绪取代。他直起身,高大的身影带来的压迫感稍稍退去,但那股属于帝王的威仪却更加迫人。
“好一个‘只为邦交之礼’。”他低低地重复了一句,嘴角那抹弧度似笑非笑,“郡主……哦不,如今该称公主了。”他微微颔首,目光却依旧牢牢锁着我,“一路风尘,公主想必乏了。来人!”
他扬声,用的是北狄语,语调威严。
立刻有两名穿着北狄宫廷侍女服饰的女子快步上前,恭敬地垂首待命。
“送公主去昭华殿歇息。”他吩咐道,目光却依旧停留在我脸上,仿佛在欣赏一件刚刚入手的、充满意外的战利品,“好生伺候。待公主休整完毕,再行册封大典。”
“是!”侍女应声,对我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姿态恭敬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
册封大典……这四个字像冰冷的枷锁,再次套回我的脖颈。
我没有再看他,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屈膝,行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北狄宫廷礼节,动作流畅得仿佛演练过千百遍,只有我自己知道,指尖在袖中是如何的冰凉颤抖。
“谢陛下。”
吐出这两个字,我挺直脊背,在两名侍女的引导下,转身,一步一步,朝着大殿侧面的通道走去。厚重的嫁衣裙摆拖曳在冰冷光滑的石地上,发出单调而沉重的沙沙声。
身后,那道锐利如鹰隼的目光,一直如影随形,直到我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通道的阴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