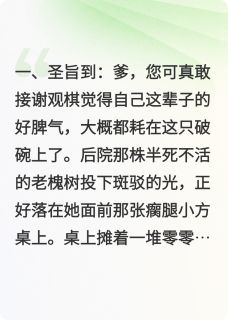
宁王府的日子,如同沉在古井里的水,波澜不惊,却也沉闷得令人窒息。
谢观棋被安置在一个名为“疏影轩”的偏僻小院。院子不大,几间厢房,倒也清静。院如其名,疏疏落落地种着几竿翠竹,在风中摇曳,沙沙作响,更添几分冷清。王府的下人们对这位新进门的世子妃,态度恭敬而疏离,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畏惧和避之不及。送饭、打扫,皆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绝不多话,更不敢与她对视。
谢观棋乐得清闲。
她带来的嫁妆不多,但件件是她精挑细选。此刻,疏影轩光线最好的东厢房,俨然成了她的“工坊”。那张瘸腿的小方桌被她搬了进来,上面摊开的,不再是那只倒霉的缠枝莲青花碗碎片——那东西在离开谢府前,被她面无表情地彻底敲成了齑粉,挫骨扬灰——而是几件同样伤痕累累、被岁月遗忘在谢家库房角落的旧物。
一幅虫蛀鼠咬、绢丝脆化断裂的《秋山行旅图》残卷;一只釉面剥落、缺了半边耳朵的粉彩婴戏图梅瓶;还有一卷书页粘连、墨迹晕染模糊的宋版《梦溪笔谈》残本。
修复这些玩意儿,需要极大的耐心、极稳的手,以及对材料特性、历史风貌的深刻理解。谢观棋沉浸其中,心无旁骛。锉刀、镊子、特制的粘合剂、洗画用的温水盆、补绢用的细丝线……在她手中如同拥有了生命。她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只有指尖细微的动作和偶尔调整角度的侧影,证明时间的流逝。
阳光透过窗棂,在她专注的侧脸上投下柔和的光晕。此时的她,沉静得如同古画中的仕女,与那个曾拎着扫把追鸡骂街的谢二姑娘判若两人。
然而,这份沉静,只属于白天。
每当夜色深沉,万籁俱寂,疏影轩彻底沉入黑暗之后,谢观棋的“消遣”便开始了。
她会在窗边支起一条细细的缝隙,自己则隐在厚重的帘幕阴影里,只露出一双清亮的眼睛,如同潜伏在暗夜里的猫。
目标,是隔壁主院——江见月所居的“听松居”方向。
起初几天,并无异常。听松居安静得像座坟墓。
直到第四天深夜。
月黑风高,王府巡夜梆子刚敲过三更。
一道比夜色更浓的黑影,如同鬼魅般从听松居后墙无声滑落。落地轻盈,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那黑影身姿挺拔,动作迅捷如电,哪里还有半分白日里坐在轮椅上、不良于行的病弱模样?
他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无人,随即足尖一点,身形拔地而起,竟如狸猫般蹿上旁边一株高大的梧桐树,借着枝叶的掩护,几个起落,便消失在王府层层叠叠的屋脊之后,速度快得惊人,方向似乎是王府西北角那片荒废的园子。
窗后的谢观棋,眼睛微微睁大,随即弯成了两道狡黠的月牙。
哦豁!
腿瘸?不良于行?
世子爷,您这夜班加得挺勤快啊?翻墙的姿势,比野猫还利索几分呢。
她无声地咧了咧嘴,轻轻合上了窗缝,心情莫名地愉悦起来。这宁王府死水般的日子,终于开始泛起一丝值得玩味的涟漪了。
自那夜之后,谢观棋的“夜观天象”便成了固定节目。江见月出门的频率不算高,但隔三差五,总会在深夜“活动筋骨”。有时是翻墙而出,有时是从外面翻墙而入。动作永远干净利落,落地无声,警觉性极高。
谢观棋看得津津有味,像欣赏一出编排精巧的默剧。她恪守着协议里的“安守本分,严守秘密”,白天在江见月面前,依旧是那个低眉顺眼、安静得如同背景板的世子妃。她替他推轮椅(虽然他很少需要她推),在他偶尔咳嗽时递上一杯温水(他从不喝),目光永远温顺地垂着,仿佛从未发现他夜里的秘密。
她装瞎,装得炉火纯青。
直到一个下着淅沥小雨的夜晚。
梆子敲过四更,雨声掩盖了大部分声响。谢观棋照例在窗边“守夜”。这一次,江见月回来得比平时晚了许多。
那道熟悉的黑影再次翻墙落入听松居后院时,动作似乎比往常滞涩了一丝。落地时,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才稳住身形。他没有立刻回房,而是隐在一丛茂密的芭蕉叶后,似乎在处理什么。
谢观棋的视力极好,尤其是在专注的时候。借着廊下灯笼昏暗的光线,她清晰地看到,江见月那身惯常的黑色夜行衣下摆,靠近右腿外侧的位置,濡湿了一大片。那深沉的、不正常的色泽,绝不是雨水!
是血。
浓重的血腥味,似乎穿透了雨幕和距离,隐隐钻入她的鼻腔。
江见月迅速撕下一截衣摆内衬,草草按在伤处,动作间带着隐忍的痛楚。他警惕地再次扫视四周,确定安全后,才快速闪身,准备掠回自己的卧房。
就在他身形刚动,即将暴露在廊下光线中的刹那——
“吱呀”一声轻响。
疏影轩的门开了。
谢观棋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白瓷碗,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她似乎没料到院中有人,脸上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惊讶和困倦。她像是被夜风吹得有些冷,缩了缩脖子,目光随意地扫过院子,然后,“恰好”落在了刚从芭蕉丛后走出、还没来得及完全隐去身形的江见月身上。
“世子?”她声音带着刚睡醒的微哑,似乎有些意外他这么晚还在外面,“您……还没歇息?”
江见月身形骤然僵住!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时辰,这个向来安静得如同不存在的世子妃,会突然出现!他几乎是瞬间敛去了所有因伤痛而泄露的情绪,挺直背脊,脸上恢复了一贯的冰冷淡漠,只是眼神深处掠过一丝极快的杀意和惊疑。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变故陡生!
谢观棋似乎被脚下湿滑的青苔一绊,“哎呀!”一声惊呼,整个人向前踉跄扑去。她手里那碗热气腾腾、散发着浓郁辛辣姜味的汤水,不偏不倚,如同长了眼睛一般,朝着江见月刚刚草草包扎过的右腿伤处,兜头泼了过去!
滚烫的、浸透了老姜汁液的液体,瞬间浸透了黑色的衣料,狠狠浇在了那道新鲜的、皮肉翻卷的伤口上!
“嗤——”
仿佛能听到皮肉被灼烫的声音。
“呃啊!”饶是江见月意志如铁,这突如其来的、钻心蚀骨的剧痛也让他瞬间闷哼出声,额头上青筋暴起,冷汗涔涔而下。他猛地后退一步,靠在冰冷的廊柱上,才勉强支撑住身体没有倒下,看向谢观棋的眼神,如同淬了毒的冰刃,充满了暴戾和难以置信的震怒。
“谢、观、棋!”这三个字,几乎是从他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浓重的血腥气。
谢观棋自己也“摔”倒在地,手肘磕在冰冷的石板上,疼得她皱了皱眉。她抬起头,脸上满是惊慌失措和无辜,那双清澈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被眼前的情形吓坏了。她顺着江见月杀人的目光,看向他被热姜汤浇透、正因剧痛而微微颤抖的右腿,以及那无法完全掩盖的、被血浸透又晕开的深色痕迹。
她像是才反应过来,小嘴微张,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即用那种充满了后怕和茫然、又带着点不合时宜好奇的语气,怯生生地、无比真诚地问道:
“哎呀!世子!您……您这腿……怎么受伤了?”她的目光在那狰狞的、被热汤一浇更显狼狈的伤处溜了一圈,又抬眼看向江见月因剧痛和暴怒而扭曲的俊脸,慢悠悠地补了一句,语气天真得像在讨论天气:
“看这伤口……像是被什么野物抓的?这王府里的猫……爪子挺锋利啊?”
江见月只觉得一股腥甜直冲喉头,眼前阵阵发黑。那三道整齐的、深可见骨的刀伤,在她嘴里,就变成了野猫抓的?!
他死死地盯着她那张写满了“无辜”和“关切”的脸,胸口剧烈起伏,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
“是……猫抓的。”他咬着牙,每一个音节都带着血腥味,“一只……不知死活的野猫!”
谢观棋眨了眨眼,从湿冷的地上爬起来,拍了拍沾了泥水的衣裙,脸上依旧带着点惊魂未定的余悸,语气却恢复了那副温顺的模样:“原来如此。那世子可要当心些,野猫性子野,爪子利,下次见了,还是躲远点好。”她顿了顿,看着江见月几乎要喷火的眼睛,又“好心”地补充了一句,“这姜汤驱寒的,可惜撒了。世子受了伤,还是快些回房处理吧?妾身……再去给您煮一碗?”
“不必!”江见月几乎是低吼出来,强忍着剧痛和滔天的怒火,转身,拖着那条被烫得**辣剧痛的伤腿,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艰难,几乎是挪回了自己的卧房,重重地关上了门。
谢观棋站在院中,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空空如也的手和沾了泥的衣袖,脸上那副无辜惊慌的表情瞬间褪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抹狡黠如狐的笑意,在唇角一闪而逝。
她慢悠悠地弯腰,捡起地上那只幸免于难、只是磕掉了一小块瓷的白碗,指尖在碗沿的豁口上轻轻弹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微响。
“啧,又得修了。”她低声自语,语气轻松得像刚看完一场好戏。转身,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回了自己的疏影轩。至于那碗“驱寒”的姜汤?谁爱煮谁煮去。
那夜“姜汤事件”后,疏影轩和听松居之间,陷入了一种更加微妙而紧绷的寂静。江见月看她的眼神,除了惯常的冰冷审视,更多了一层深沉的探究和毫不掩饰的警告。他似乎在评估,这个看似温顺无害的庶女,到底是真傻,还是深藏不露。
谢观棋则贯彻“装瞎到底”的策略,白天依旧安分守己地修复她的破烂,对世子爷的冷脸视若无睹,仿佛那晚真的只是一场意外。只是偶尔在给他递东西时,指尖会“不经意”地擦过他搁在轮椅扶手上的手背,换来他瞬间的僵硬和更冷的眼风。
王府的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沉闷地走着。
直到这天午后,管库的老王头佝偻着背,敲响了疏影轩的门。
“世子妃安。”老王头的声音带着常年咳嗽的沙哑,“王妃……呃,就是以前老王妃留下的库房,西边角落那个,王爷……老王爷在时吩咐封存的,最近雨季返潮,怕里头东西霉坏了。老奴想着,您手巧,能不能……帮着看看,有些字画古籍什么的,若还能救,就拾掇拾掇?若实在不行,也好……也好处理了。”他话说得吞吞吐吐,眼神躲闪,显然对踏足这“不祥”的世子妃院落充满畏惧,但又不得不来。
谢观棋放下手中正在粘合的一片古瓷,眼睛微微一亮。老王妃?宁王生母的库房?还是被封存的?这里面,说不定真能淘到点好东西。修复旧物不仅是她的技艺,更是她了解这座王府、了解江见月秘密的途径。
“好,带路吧。”她起身,语气平淡。
老王头如蒙大赦,连忙引着她穿过重重院落,来到王府最西侧一个偏僻的角落。一座独立的小库房,门锁锈迹斑斑,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吱嘎”声,一股浓重的霉味混合着尘土的气息扑面而来。
库房里光线昏暗,堆满了蒙尘的箱笼家具。老王头指着一个角落:“就……就那些,老王妃生前喜欢收集些字画,后来……后来就堆这儿了。”
谢观棋点点头,让老王头自去忙。她挽起袖子,点燃带来的蜡烛,开始在这片尘封的角落里翻找。大多是些寻常的花鸟仕女图,或是些普通佛经,虫蛀鼠咬,破损严重。
翻找了小半个时辰,就在她以为没什么收获时,一个沉甸甸的、包着褪色锦缎的长条画匣被她从一堆破家具下拖了出来。画匣本身用的就是上好的紫檀,虽蒙尘,却无损其贵重。
她拂去厚厚的灰尘,解开系带,小心地取出里面的画轴。画轴入手沉重,卷得极紧。她缓缓展开——
烛光下,一片磅礴的青绿山水,如同沉睡千年的瑰宝,骤然撞入眼帘!
纵然历经岁月,绢丝泛黄,虫蛀点点,许多地方色彩剥落,甚至有大片大片的留白(那是被虫蛀空的画心),但那恢弘的气势、精妙的笔触、层叠的峰峦、浩渺的烟波……依旧扑面而来,震撼人心。
《千里江山图》!
虽然不是王希孟那幅震古烁今的真迹,但看这绢质、这青绿矿彩的运用、这构图气韵,绝对是前朝大家临摹的精品!其价值,难以估量!
谢观棋的心跳瞬间加速,呼吸都屏住了。不是因为它的价值,而是因为这幅画本身的精妙和它所承载的历史厚重感,深深吸引了她。修复这样一幅巨作,是每一个修复师梦寐以求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