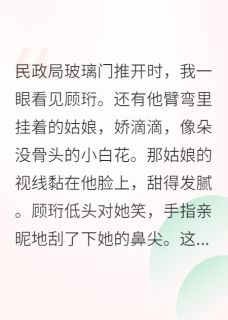
大概是看我态度过于笃定,王老板反而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犹豫了一下,最终哼了一声:“行!就给你三天!我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来!签字!”
签完那份屈辱的协议,打发走王老板那帮瘟神,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老赵叔。他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重重叹了口气:“小沈总,你这是……唉!三天,我们去哪弄几十万啊?”
“赵叔,”我疲惫地捏了捏眉心,“厂里账上还有多少能动用的钱?”
“不到五万块,是留着给大伙儿买劳保和应急材料的……”
杯水车薪。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先把工人的工资核算出来,尽量准备。告诉大家,工资一定会发,让他们安心。”
“那王胖子这边……”
“我有办法。”我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办法?其实心里一片茫然。但在这个四面楚歌的时候,领头的人不能露怯。
老赵叔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担忧,最终还是点点头出去了。
偌大的办公室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看着窗外日渐萧条的厂区,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账单,绝望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越收越紧。
三天。七十二小时。几十万的窟窿。顾承宗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堵死了我所有的路。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个本地的陌生号码,但不是顾承宗那种令人窒息的号段。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你好,沈霁**?”一个清冽悦耳的男声传来,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客气。
“我是。您哪位?”
“萧凛。”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但我一时想不起来。
对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迟疑,补充道:“上周在‘前沿科技创投峰会’上,我们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你关于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即兴发言,很精彩。我是凛冬资本的负责人。”
凛冬资本?!
我猛地想起来了!那次峰会,我是陪一个做软件的同学去凑热闹的。中场休息茶歇时,听到几个西装革履的人在讨论传统制造业转型的困境,一时没忍住,结合我爸厂子的实际情况插了几句嘴。当时有个穿着黑色高定西装、气质异常冷峻的男人,一直没怎么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看我一眼。原来他就是萧凛!
凛冬资本,那可是近几年在风投圈异军突起、眼光极其毒辣的新锐机构!投的几个项目都成了行业独角兽。他们怎么会注意到我?
“萧……萧总?”我有些不敢相信,“您找我有事?”
“确实有事想和你当面聊聊。”萧凛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依旧没什么温度,却奇异地驱散了我心头的些许阴霾,“关于你父亲的‘建晟精密加工厂’,以及你本人在峰会上的观点,我很感兴趣。不知沈**今天下午是否方便?地点你定。”
峰回路转?还是又一个陷阱?
顾承宗的阴影太重,我不得不警惕。“萧总,您怎么会对我家这个小厂感兴趣?”
电话那头似乎传来一声极轻的笑,快得像是错觉。“凛冬资本的投资方向,不看规模大小,只看价值和潜力。沈**在峰会上的见解,以及你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他顿了顿,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韧性和清醒,是价值的一部分。下午三点,方便吗?”
价值?韧性?清醒?这些词从萧凛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奇特的份量。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疑虑和狂跳。管他是机会还是陷阱,眼下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抓住任何一根可能的稻草,是溺水者唯一的本能。
“方便。地点……就在我们厂区的办公室吧,萧总不嫌弃简陋的话。”
“好。三点见。”
挂了电话,我看着老旧办公室斑驳的墙壁和蒙尘的窗户,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撞击着。凛冬资本……萧凛……这会是绝境中的一线生机吗?
下午两点五十,我让老赵叔简单收拾了一下办公室,把最重要的几份资料摆在了桌上。自己则对着洗手间那面模糊的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领。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下带着浓重的青黑,只有一双眼睛,因为未知的可能而亮得惊人。
三点整,一辆线条冷硬流畅的黑色宾利慕尚,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厂区门口。与周围破败的环境格格不入。
车门打开,一条包裹在黑色西裤里的长腿迈出。萧凛下了车。
他比在峰会上看到的更加挺拔。一身剪裁完美的深色西装,衬得肩宽腰窄。面容极其英俊,却带着一种生人勿近的冷冽感,眉骨很高,鼻梁挺直,下颌线如刀削般利落。眼神深邃,像不见底的寒潭,平静无波地扫过厂区破败的大门和坑洼的路面,没有流露出丝毫嫌弃或惊讶。
老赵叔紧张地迎上去。萧凛对他微微颔首,目光随即越过他,落在了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我身上。
他的视线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那目光很锐利,带着审视,仿佛能穿透我强装的镇定,看到我骨子里的疲惫和焦灼。但只是一瞬,便恢复了公事化的平静。
“沈**。”他走到我面前,声音低沉悦耳。
“萧总,里面请。”我侧身让开。
办公室简陋得有些寒酸。萧凛却像是没看见,目光直接落在了我摊开在桌上的资料上——厂子的基本情况、设备清单(尽管老旧)、客户名录(虽然所剩无几)、以及那份要命的债务明细表。
他没有客套,直接坐下,拿起那份债务表,修长的手指划过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数字。
“情况比我想象的更糟。”他放下表格,抬眼看向我,眼神锐利,“顾氏撤资的连锁反应?”
我的心猛地一沉。他果然知道!是巧合,还是……调查过我?顾承宗的阴影再次笼罩下来。
“是。”我没有否认,也否认不了,“顾氏原本承诺的过渡资金没了,原有的合作方也……受到了压力。”我斟酌着用词。
萧凛微微颔首,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仿佛在听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你现在的计划是什么?三天后,拿什么还宏发的债?”他精准地点出了王老板的逼债。
我手心冒汗。在他面前,我像个被完全看透的小学生。“我……抵押了我家的房子。但银行评估需要时间,最快也要五天,赶不上宏发三天的期限。”这是我最后的底牌,也是无奈之下的孤注一掷。
萧凛沉默地看着我,那双深潭般的眼睛似乎能洞悉人心。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尘埃落定的声音。
几秒后,他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叠放在桌上,一个极具掌控感的姿态。
“沈**,凛冬资本可以帮你解决宏发的债务。”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巨大的狂喜还没来得及涌上,就被他下一句话冻结。
“但,不是无偿的。”他的语气冷静得像在陈述一个商业公式,“我需要你厂子51%的股权。以及,你本人,在未来五年内,必须担任这家工厂的总经理,负责其全面的转型和运营。”
51%的股权?意味着厂子易主!我爸一辈子的心血……
“这不可能!”我脱口而出,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厂子是我爸的命!51%绝对不行!”
“命?”萧凛嘴角似乎勾起一个极淡的弧度,带着一丝近乎残酷的理性,“如果厂子破产清算,它连一分钱都不值。你和你父亲,还会背上巨额债务。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心血?”
他的话像冰锥,刺得我鲜血淋漓,却又无法反驳。
“凛冬的注资,是买一个机会。”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目光如炬,“一个让‘建晟’摆脱低端代工,转型为拥有核心技术的小型精密制造企业的机会。我买的是潜力,是未来,不是你父亲过去的‘心血’。51%,是我的底线。同时,也是对你能力的捆绑和考验。五年总经理,做成了,你和沈家不仅能翻身,还能更上一层楼。做砸了……”
他后面的话没说完,但意思不言而喻。
巨大的矛盾撕扯着我。一边是厂子立刻破产、全家坠入深渊;一边是交出控股权,赌一个渺茫却诱人的未来。而萧凛,这个突然出现的冷峻男人,是拯救者,还是另一个……掠夺者?
“为什么是我?”我看着他,艰难地问出心底最深的疑惑,“萧总,凛冬资本有无数选择。我家这个厂子,负债累累,设备老旧,毫无优势。您图什么?”
萧凛身体向后靠去,姿态放松了一些,但眼神依旧锐利。“三个原因。”
“第一,峰会上你的发言,思路清晰,痛点抓得准,有破局的狠劲儿,不像个纸上谈兵的。”
“第二,”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苍白的脸,“顾承宗亲自打压的人,要么蠢到无可救药,要么……就是真碍了他的眼,或者,有他忌惮的东西。我倾向于后者。”
顾承宗忌惮我?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觉得荒谬。但萧凛显然不这么想。
“第三,”他的目光落在我紧握的拳头上,那指甲掐出的月牙印痕清晰可见,“也是最重要的。你拒绝了顾承宗的‘恩赐’。宁肯要饭,也不吃他沾了屎的饭。这种宁折不弯的骨气,在商场上是双刃剑,但用好了,能成事。”
他看着我,一字一句道:“我投的,就是你这股不肯低头的劲儿。赌你能把这把双刃剑,磨成开山刀。”
宁折不弯的骨气……开山刀……
他的话,像重锤,敲在我濒临崩溃的心防上。
办公室里再次陷入沉寂。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在布满灰尘的空气里投下光柱。我看着桌上那份沉重的债务表,又看向萧凛那张轮廓分明的冷峻侧脸。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在油锅里煎熬。
最终,我抬起头,迎上萧凛等待的目光,声音因为紧绷而有些沙哑,却带着孤注一掷的决绝:
“好。51%股权,五年总经理。我签。”
签下那份股权**协议和附加的五年“卖身契”,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轻松,反而像是背上了更沉重的枷锁。
萧凛的动作快得惊人。协议签完的第二天,凛冬资本的法务和财务团队就进驻了厂子。第三天,宏发王老板的账户上,准时收到了那笔要命的尾款。他打电话来时,语气惊疑不定,甚至带着点讨好,再也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工人们的工资,也按时足额地发到了手里。车间里停转的机器,重新发出了轰鸣。
危机暂时解除,但厂子里弥漫的气氛却更加复杂。老工人们看我的眼神,有感激,有担忧,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毕竟,厂子以后不姓沈了。
我爸沈建国从外地赶了回来。当他看到办公室里那些穿着讲究、行事干练的“凛冬人”,看到那份白纸黑字的股权**协议时,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瞬间老了十岁。他把自己关在车间后面的小休息室里,抽了一下午的闷烟,一句话也没跟我说。
我知道,他心里那道坎,比我更难迈过去。
萧凛很少亲自来厂里。凛冬派驻了一位姓陈的副总,负责日常监管和财务。但厂子转型的具体方向和执行,萧凛明确放权给了我。他只给了我一个模糊的目标:半年内,摆脱低端代工,找到核心技术突破口,实现盈亏平衡。
压力,比顾家撤资时更沉重,也更具体。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泡在厂里。研究设备潜力,梳理客户资源,分析市场趋势。萧凛偶尔会打电话过来,言简意赅地问进展,或者丢过来一个行业前沿的资料包。他的话永远不多,但每次都能精准地戳中我思路的瓶颈。
日子在高压下缓慢推进。就在我带着技术骨干,好不容易啃下一小块技术升级的硬骨头,勉强说服了一个老客户试用我们的新工艺样品时,新的麻烦又来了。
这天下午,我正和技术组长讨论样品测试数据,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六神无主:
“霁霁!不好了!你爸……你爸被一群人堵在家里了!那些人凶神恶煞的,说要搬东西抵债……你快回来啊!”
我脑子“嗡”的一声!家里?抵债?银行的抵押贷款还没到期!宏发的钱也还清了!哪里又冒出来的债主?
“妈!你别慌!锁好门别开!我马上回来!”我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
一路疾驰回家。刚拐进我家老小区那条窄路,就看到我家楼下围着不少人。两个穿着黑T恤、一脸横肉的男人,正不耐烦地拍打着我家老旧的单元门,嘴里骂骂咧咧。旁边还停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
“沈建国!开门!别他妈装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不开门,老子砸门了!”其中一个光头壮汉吼道。
我妈在门里带着哭音喊:“你们找错人了!我们家没欠你们钱!”
“放屁!白纸黑字写着呢!沈建国担保的!五十万!连本带利六十万!今天拿不出钱,就拿东西抵!”另一个纹着花臂的男人晃着手里的几张纸。
担保?我爸什么时候给人担保了?!
我停好车,推开车门就冲了过去:“住手!你们干什么的!”
那两个男人闻声回头,看到我,眼神不善地上下打量:“你谁啊?”
“我是沈建国的女儿!你们手里拿的什么东西?”我强压着怒火和惊疑。
“女儿?”光头男嗤笑一声,把手里的纸抖开,几乎戳到我脸上,“看清楚了!你爸沈建国,给‘永利商贸’的刘大富做的担保!刘大富卷钱跑了,这钱,就得你爸还!我们是受债权人委托来收债的!六十万!今天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我一把夺过那几张纸。上面确实是担保合同,借款人是“刘大富”,担保人签字栏里,赫然是我爸沈建国歪歪扭扭的签名!日期……竟然是我和顾珩订婚后的第三天!
刘大富?我有点印象。好像是我爸以前的一个牌友,做点小生意的。我爸怎么会给他担保这么大一笔钱?还瞒着我们所有人?!
“这签名……是真的?”我手指发颤,盯着那个签名,心不断下沉。我爸的字,我认得。
“当然是真的!公证过的!”花臂男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少废话!要么还钱!要么让我们进去搬东西!”
我被推得一个趔趄,怒火瞬间冲上头顶:“你们敢动一下试试!这是非法侵入!我报警!”
“报警?”光头男像听到了笑话,指着我的鼻子,“欠债还钱,天王老子来了也是这个理!你报警啊!看看是警察管用,还是我们兄弟天天来你家门口‘问候’管用!”
周围看热闹的邻居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我妈在门里哭喊着我的名字。屈辱、愤怒、还有巨大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刚解决了一个顾珩,又来了一个萧凛的“枷锁”,现在又莫名其妙多出一笔我爸的糊涂债!
顾承宗那张冰冷的脸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是他吗?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就在这时,一阵低沉有力的汽车引擎声由远及近。一辆熟悉的黑色宾利慕尚,以一种近乎蛮横的姿态,直接开进了狭窄的社区小路,停在了那辆破面包车旁边,堵住了它的去路。
车门打开,萧凛迈步下车。他依旧是那身剪裁完美的深色西装,在破旧混乱的环境里,显得格格不入,却又带着一种镇压全场的强大气场。
他目光冰冷地扫过那两个叫嚣的壮汉,最后落在我身上,眉头几不可查地皱了一下:“怎么回事?”
看到萧凛,那两个壮汉明显愣了一下,气势弱了几分。光头男梗着脖子:“你谁啊?少管闲事!”
萧凛没理他,径直走到我面前,目光落在我手里那份担保合同上:“什么东西?”
我喉咙发紧,把合同递给他,声音干涩:“他们说我爸……给人担保了六十万……”
萧凛快速扫了几眼合同,眼神骤然变得锐利如冰刀。他抬眼看向那两个壮汉,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压迫感:
“债权人是谁?委托书拿出来。”
花臂男被他看得有点发毛,色厉内荏地嚷道:“**谁啊?凭什么给你看!”
萧凛没说话,只是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语气淡漠:“老周,带几个人过来,锦华小区三栋一单元。有两个非法讨债的,涉嫌伪造文书、暴力胁迫,处理一下。”
非法讨债?伪造文书?我愣住了。
那光头男脸色一变:“你……你少血口喷人!合同是真的!有公证!”
“是吗?”萧凛冷笑一声,指着合同上担保人签字栏旁边一个不起眼的日期章,“这个公证处的编号,上个月就因为违规被吊销资格了。你们拿一份用失效公章‘公证’的合同来讨债?”
两个壮汉的脸色瞬间煞白,眼神慌乱地对视一眼。
“还有,”萧凛的声音像淬了冰,“刘大富上个月底就在邻省落网了。他交代的债务关系里,根本没有这笔所谓的担保借款。你们是哪里冒出来的‘债权人’?嗯?”
最后一句话,带着雷霆万钧的质问。两个刚才还凶神恶煞的男人,此刻像被戳破的气球,冷汗“唰”地就下来了。
“我……我们……”光头男结结巴巴,说不出话。
花臂男更是脚底抹油,转身就想溜。
“站住。”萧凛的声音不大,却像钉子一样把两人钉在原地。“伪造文书,暴力讨债,敲诈勒索。哪一条,都够你们进去蹲几年。谁指使你们来的?”
光头男腿一软,差点跪下,哭丧着脸:“大……大哥!我们就是拿钱办事!是……是一个姓张的老板!他给我们钱,让我们来闹……说闹得越大越好……我们真不知道这合同是假的啊!”
姓张的老板?我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毫无头绪。但直觉告诉我,这背后,绝对有顾家的影子!
“名字,电话,转账记录。”萧凛言简意赅。
两个壮汉哪还敢隐瞒,竹筒倒豆子般全说了。萧凛带来的保镖(他电话里叫的老周)很快赶到,控制住了两人,并报了警。
混乱的场面被迅速平息。看热闹的邻居被劝散。我妈哆哆嗦嗦地开了门,抱着我直哭。
萧凛站在旁边,看着惊魂未定的我和我妈,眉头依旧微蹙着:“人交给安保处理了。伪造文书和背后指使的事,他们会查清楚。这几天,我会安排人在这边看着。”
“萧总……谢谢。”我声音有些哽咽,除了谢谢,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刚才那一刻,他像天神降临,驱散了魑魅魍魉。可这种被保护的感觉,又让我觉得无比脆弱。
“你爸呢?”他问。
我这才想起,闹这么大,我爸一直没露面。“可能在休息室……”我看向单元门里面。
萧凛点点头,没再多说,转身走向他的车。走了两步,又停住,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有些凌乱的头发和苍白的脸上,停顿了几秒。
“沈霁,”他第一次叫我的全名,声音低沉,“商场如战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顾承宗的手段,不会只有这些。打起精神来。”
说完,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黑色的宾利缓缓驶离,留下我和我妈,还有一地狼藉的惊魂。
我爸沈建国,终于从小休息室里出来了。他脸色灰败,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爸!”我看着他,又气又急,“那担保到底怎么回事?刘大富是谁?您怎么会签那种东西?”
沈建国颓然地坐在旧沙发上,双手抱着头,声音嘶哑,充满了悔恨:“我……我对不起你们娘俩啊!那个刘大富……他……他以前是顾氏下面一个小分包商,跟我也算认识……去年,就你跟顾珩订婚后没多久,他突然来找我喝酒,说手头紧,想借笔钱周转,利息给得高……还说他跟顾家关系好,马上有个大项目,稳赚……我当时……当时也是昏了头,想着顾家这门亲事定了,厂子有靠山了……他又拍胸脯保证……我……我就……”
“您就给他做了担保?!”我气得浑身发抖,“五十万啊爸!您连合同都不看清楚吗?!”
“他……他说是正规合同,有公证的……我就签了……”沈建国的头埋得更低了,“后来他确实还了几个月利息,我就没多想……谁知道……谁知道他人跑了!那帮人今天突然找上门,我才知道……那公证……那公证是假的啊!霁霁!爸糊涂!爸该死啊!”
看着我爸老泪纵横、悔恨交加的样子,我满腔的怒火像被戳破的气球,只剩下深深的无力感和悲哀。顾家……顾承宗……他们早就算计好了!从我爸这里下手,埋下这颗随时可以引爆的雷!什么亲家?分明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
萧凛说得对。顾承宗的手段,不会只有这些。这只是开始。
我扶住摇摇欲坠的我妈,看着悔恨交加的我爸,一股前所未有的冰冷恨意,从心底最深处蔓延开来,迅速冻结了所有的软弱和犹豫。
顾承宗,顾珩。
你们想玩?
好。
我沈霁,奉陪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