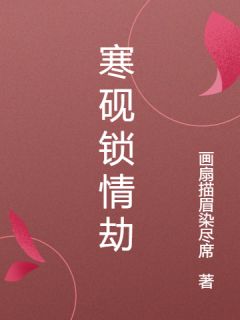
炭炉里的火星噼啪爆开时,苏砚的指尖正压在新制的墨锭上。
浅青釉陶砚台旁堆着几团松烟,晨雾从糊着旧报纸的窗棂渗进来,在她眼尾那道浅疤上凝出细珠——那是十二年前飞溅的血滴结的痂,早没了痛感,却总在她动心思时跟着发烫。
"阿砚!"
门环被拍得哐当响时,苏砚的手顿了顿。
老仆佝偻着背冲进来,额角沾着晨露,粗布衫下摆还沾着泥。
他喉间发出破风箱似的声响,枯树皮般的手攥住苏砚手腕,指甲盖泛着青:"我...我想起来了。"
苏砚瞳孔微缩。
她记得昨夜替老仆擦身时,他后颈的溃烂已经漫到耳后——这把老骨头撑不过这个月的。
可此刻老人浑浊的眼里烧着团火,像极了十二年前那个血夜,他断了两根手指替她撬开狗洞时的模样。
"当年...抄家那晚。"老仆咳得弯下腰,指节深深掐进苏砚腕骨,"我躲在柴房梁上,看见个穿黑衣服的。"他突然抬头,浑浊的眼珠里映着炭炉的光,"他进了老爷书房,没拿金银,抱走了那本《松雪斋墨谱》。"
苏砚的呼吸滞在胸口。
十二年前玉衡斋被冠上"私藏逆书"的罪名,满门抄斩时,官府翻遍了书房都没找到所谓"逆书"。
而《松雪斋墨谱》是她家传三代的制墨手札,父亲总说"墨匠的魂在谱里",连她都只翻过三回。
"我...我怕说出来害你。"老仆的手渐渐松了,指甲在苏砚腕上刮出红痕,"可昨儿夜里,我梦见你阿爹了...他说,该让阿砚知道了。"
苏砚的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案上墨锭。
炭炉的热气裹着松烟香涌进鼻腔,恍惚又看见十二岁那年,老仆背着她从狗洞爬出去时,后颈渗出的血把她的绣鞋都染红了。
她按住老仆手背,声音比砚台里的墨还凉:"您好好歇着,我去煎药。"
可等她端着药碗回来,老仆的手已经冷了。
他保持着伸手的姿势,像是要替她擦掉眼尾的湿意。
苏砚跪坐在草席上,替他合上眼,指腹擦过他后颈溃烂的伤口——那里还沾着半片碎瓷,是前日她熬药时手滑碰翻的。
"对不住。"她对着老人灰白的鬓角轻声说,"您等我。"
埋完老仆时,日头已经爬到东墙。
苏砚拍净手上的土,转身就看见巷口晃着靛青短打。
李三叼着狗尾巴草,腰间铜酒壶撞得叮当响,身后跟着獐头鼠目的小六——这俩泼皮最近总在寒砚斋附近转悠,昨天还掀了她晒墨的竹匾。
"苏娘子这是..."李三眯眼扫过新堆的土包,嘴角扯出阴恻恻的笑,"办白事呢?
正好,某替官府查查你这作坊有没有藏违禁品。"
苏砚眼尾的疤又烫了。
她垂眸笑,温吞得像巷口老井里的水:"李大哥说笑了,我这小本生意,哪敢藏什么违禁品?"
"那便让某看看。"小六搓着手就要往里闯,却被苏砚抬手拦住。
她指尖还沾着新土,在小六腕上轻轻一按:"墨胚刚上胶,碰坏了今日文会可交不了差。"
李三的目光落在案上一排墨锭上。
松烟墨泛着乌金光泽,最上面那块雕着九叠云纹,云头里还嵌着粒米大的珍珠。
他凑过去嗅了嗅,眉峰一挑:"好香的沉水香。"
"这是给城南书坊的订墨。"苏砚指尖拂过墨锭,在云纹最深处一按,墨身突然裂开条细缝,"李大哥瞧,里面嵌的是松针形银叶——文会要比'墨中藏巧',我这算讨个彩头。"
李三眯眼凑近。
细缝里确实躺着片薄如蝉翼的银叶,弯成松针模样,叶尖还刻着"南都文会"四个字,小得要用指甲盖对着光才能看清。
他直起腰,酒壶在腰间撞出闷响:"算你识相。"
小六还想再搜,被李三扯了把袖子。
两人晃出巷口时,苏砚听见小六嘀咕:"那墨香邪性得很...""蠢货,"李三的声音飘进来,"制墨的哪个不用香料?"
月上柳梢时,苏砚关了店门。
她从梁上取下个木匣,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二块松烟墨——每块背面都有微雕,有的是半片枫叶,有的是断了弦的琴,合起来是十二年前玉衡斋被抄时的线索。
她取了块新墨,刀尖在背面游走。
松烟簌簌落下,很快露出一行细字:"黑衣客,松雪谱,十二年前夜。"
"阿福!"她推开后窗,隔壁卖馄饨的少年探出头,"把这个带给梅娘,就说'松针落'。"
阿福挠着后脑勺接过去,转身跑远时,腰间铜铃叮铃作响。
苏砚正要关窗,窗纸忽的一暗。
她反手抄起案上镇纸,却只看见几片碎瓦落在院里——刚才那片阴影,像极了老仆说的,那件黑衣人穿过的玄色。
"比我想得更快。"她盯着掌心的汗,把镇纸轻轻放回原处。
墨香裹着夜雾漫进来,在她眼尾的疤上凝成颗水珠,坠下来时,把案上未干的墨锭晕开道细纹。
次日清晨,苏砚刚推开店门,晨雾里就晃进一片湖蓝。
那人身穿湖蓝锦袍,腰挂鎏金酒葫芦,正弯腰捡起地上半块松烟墨,抬头时眼尾上挑:"姑娘这墨香..."他嗅了嗅,笑出声来,"比胭脂勾人多了。"
晨雾未散时,苏砚推开店门的手顿了顿。
门轴吱呀声里,湖蓝色锦袍先撞进视线。
那人弯腰捡地上半块松烟墨,鎏金酒葫芦在腰间晃出细碎金光,抬头时眼尾上挑,眉峰沾着点雾水:"姑娘这墨香..."他把墨锭凑到鼻尖,喉结随轻笑滚动,"比胭脂勾人多了。"
苏砚后退半步,脊背贴上门板。
她的指尖无意识摩挲着门框,新刷的桐油还带着潮气。
这是她昨夜特意让阿福帮忙刷的——若有人硬闯,门框上未干的油痕会沾在衣襟上。
此刻那抹湖蓝离她三步远,锦袍下摆干干净净,连鞋尖都没沾泥。
"客官早。"她垂眼扫过对方腰间玉佩,定北侯府的玄鸟纹在雾里泛着冷光,"寒砚斋今日新到松烟墨,要挑些送书房?"
裴溯直起身子,墨锭在掌心转了个圈:"书房倒用不上。"他忽然凑近,酒气混着沉水香撞进苏砚鼻端,"听说这南都制墨师里,数寒砚斋的墨能藏巧。"
苏砚的后槽牙咬了咬。
十二年前玉衡斋的墨中藏巧,是天下一绝。
老仆说过,当年抄家的官差在庭院里挖地三尺,就是为了找那些嵌着密纹的墨锭。
此刻裴溯的指尖正抚过她案头未完工的墨胚,指节分明,指甲盖泛着淡粉,像极了读书人的手,偏生按在墨胚上的力道重得反常。
"藏巧是虚的。"她从他掌心抽走墨锭,指尖触到他掌心薄茧——不是握笔的茧,是握剑的。"不过是雕些花鸟讨文人喜欢。"
裴溯突然笑出声,酒葫芦在案上磕出脆响:"玉衡斋的墨,可不止讨文人喜欢。"
案上墨香猛地一滞。
苏砚眼尾的疤微微发烫。
她望着裴溯身后斑驳的砖墙,那里还留着去年暴雨冲掉的半幅招贴,写着"玉衡斋墨,墨香传家"。
十二年前的火把烧了玉衡斋的匾额,却烧不尽市井里的旧话。
可眼前这人,分明是在试探。
"玉衡斋?"她弯腰整理柜台下的墨匣,声线压得温吞,"我听老辈说过,那是二十年前的老字号了。"
"二十年前?"裴溯拖长音调,突然抓起她搁在案上的刻刀。
刀刃映着他眼底暗芒,"我倒听说,玉衡斋灭门那日,有个小丫头躲在晒墨的竹架上,看官兵砍了老制墨师的手。"
刻刀"当啷"坠地。
苏砚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她想起老仆断指时溅在她脸上的血,温热的,像极了今日晨雾里裴溯的目光。
她弯腰捡刀,发尾垂落遮住表情:"客官这故事,比话本还玄。"
"玄不玄的,试试便知。"裴溯拾起她落在地上的半块墨,对着光看了看,"这墨背面的纹路...像半片枫叶?"
苏砚的呼吸陡然一紧。
那半片枫叶是她昨夜刚刻的,藏在墨身最深处。
除非用刀尖挑开表层松烟,否则根本看不见。
她抬眼时,裴溯正把墨锭抛着玩,酒葫芦上的流苏扫过她案头未封匣的密信——那是阿福昨夜送去梅娘处的"松针落"回函。
"客官若喜欢,这墨算您半价。"她扯出个笑,伸手去接,"但小本生意,不赊账。"
裴溯却后退一步,锦袍扫过门边的绿萝:"不急。"他指腹蹭了蹭鼻尖,"改日带个懂墨的来,再挑。"
话音未落,他已晃出店门。
晨雾里只余一句"姑娘眼尾的疤,倒像朵开败的梅",混着酒葫芦的轻响,散在风里。
苏砚关上门,后背抵着门板滑坐下去。
她摸出袖中藏的银簪,簪尖挑开刚才裴溯碰过的墨锭——松烟簌簌落下,半片枫叶下果然多了道划痕,细得像发丝,却分明是"溯"字的起笔。
"啪!"
店门被踹开的巨响惊得她跳起来。
小六叼着根狗尾巴草,身后跟着三个拎着木棍的汉子,门框上的桐油在他衣襟上染了片暗黄。
"苏老板好手段啊。"小六踢翻她的墨匣,松烟墨骨碌碌滚了满地,"李三哥说,昨日没搜着逆书,今日该交个投名状了。"
苏砚蹲下身捡墨,指尖摸到块被踩碎的墨锭。
她望着碎成两半的墨身,里面嵌着的银叶在晨光里泛冷——那是给城南书坊的订墨,文会要用的。
"投名状?"她把碎墨拢进掌心,"李大哥要我做什么?"
"简单。"小六蹲下来,食指戳她额头,"明日文会,你那墨里的银叶,改成'李'字。"他从怀里摸出包药粉撒在地上,"若不肯...寒砚斋的墙脚,可经不住这'溃石散'泡三夜。"
苏砚盯着地上的药粉。
那是用南境红土和生石灰混的,泼在砖墙上能慢慢蚀穿地基。
她抬头时,小六的刀尖正抵着她喉结:"后日卯时,李三哥在码头等答复。"
门"砰"地关上时,苏砚掌心的碎墨扎进肉里。
她望着满地狼藉,忽然笑了——李三急了。
昨日他派小六搜店,是试探她是否藏着玉衡斋的密墨;今**她改银叶,是想把文会的彩头变成他的护身符。
可他不知道,她今早给城南书坊的墨里,除了银叶,还嵌着半粒松脂。
戌时三刻,苏砚裹着玄色斗篷蹲在醉仙楼后巷。
裴溯的湖蓝锦袍在二楼雅间窗纸上投下影子,对面坐着个戴斗笠的男人,袖口露出半截玄色暗纹——和昨夜后窗那片阴影的纹路一模一样。
她听见"玉衡斋"三个字被风卷下来,又听见裴溯轻笑:"当年那把火,烧得可干净?"
斗笠男的声音像砂纸擦过石板:"干净得很。除了个小丫头..."
苏砚的指甲掐进墙缝。
她摸出怀里的竹哨,刚要吹,雅间里突然传来瓷器碎裂声。
裴溯的声音拔高:"老子要的是松雪谱!
你说干净?"
松雪谱。
这三个字像根针,扎得她太阳穴突突跳。
老仆咽气前,最后一句话就是"松雪谱...在..."。
她望着二楼晃动的影子,忽然想起裴溯今早留在墨里的"溯"字——定北侯府的世子,怎会不知道松雪谱?
后巷突然传来脚步声。
苏砚缩进修竹丛里,看着两个提灯笼的伙计走过,这才猫着腰绕到醉仙楼后门。
门没关严,她听见斗笠男压低声音:"那丫头最近在查黑衣客,得..."
"闭嘴。"裴溯的声音冷得像冰,"她要查,便由她查。"
苏砚的心跳漏了一拍。
她退到巷口,望着醉仙楼的灯笼在风里摇晃,影子里的湖蓝锦袍忽然贴近窗户,像是要往下看。
她转身就跑,鞋底碾过片碎瓷,脆响惊得檐角铜铃叮当。
回到寒砚斋时,案头多了个青竹匣。
她摸出藏在房梁的钥匙打开,里面躺着张薄如蝉翼的绢帛,梅娘的字迹在月光下泛着青:"松雪谱在太医院典籍阁,守谱人颈后有朱砂痣。
另,李三与户部陈侍郎有私,上月往南境运了十车盐。"
苏砚把绢帛塞进烛火,看着字迹在火焰里蜷成灰。
她从床底摸出个陶瓮,倒出里面的墨锭——每块都刻着不同的线索。
她挑了块雕着松针的墨,刀尖在背面游走,很快刻出"盐车,南境,陈侍郎"几个小字。
窗外传来更夫打更的声音,梆子响了三下。
她刚把墨锭收进木匣,院外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苏姐姐!"阿福的声音带着哭腔,"快开门!"
苏砚抄起案上的镇纸,指尖却在触到门闩时顿住。
她望着月光下阿福晃动的影子,腰间铜铃还在叮铃作响——和昨夜送密信时一样。
但这一次,铜铃的响声里,混着血的腥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