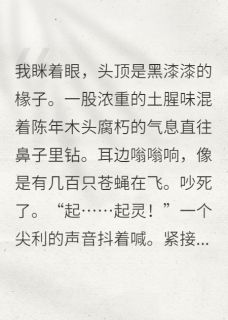
我眯着眼,头顶是黑漆漆的椽子。一股浓重的土腥味混着陈年木头腐朽的气息直往鼻子里钻。
耳边嗡嗡响,像是有几百只苍蝇在飞。吵死了。“起……起灵!”一个尖利的声音抖着喊。
紧接着,是沉闷的“嘎吱”声。我头顶那一片黑乎乎的东西,被一点点挪开了。
刺眼的光猛地扎进来,晃得我眼睛生疼。“啊——!!!”凄厉的尖叫炸开,
比刚才那声“起灵”响亮十倍。“鬼!鬼啊!”“诈尸了!夫人诈尸了!”“娘嘞!
”棺材板被彻底掀开,砸在地上,扬起一阵灰尘。我撑着棺材边沿,慢吞吞地坐了起来。
脖子有点僵,浑身骨头都像生了锈。我环顾四周。挺大的一个灵堂。白幡挂得到处都是。
底下跪着、站着不少人。离棺材最近的一个婆子,穿着素净的绸布衣裳,脸刷白,
眼珠子瞪得溜圆,指着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然后白眼一翻,
直挺挺向后倒去,砸翻了后面一个端盆的小丫鬟。“哐当!”铜盆摔在地上,水泼了一地。
小丫鬟也顾不上盆,跟着尖叫起来,手脚并用地往后爬。整个灵堂乱成一锅粥。哭喊的,
尖叫的,想跑又腿软摔跤的,互相推搡的。几个穿着短打、看着像是护院的壮实男人,
手里拿着哭丧棒,脸色发青,想上前又不敢,只死死盯着我,手里的棒子抖得像风中的叶子。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身簇新的寿衣,料子不错,是上好的锦缎,绣着繁复的缠枝莲纹。
就是颜色太素,白惨惨的。手腕露在外面,皮肤倒还细腻,就是没什么血色。挺好,
开局就是棺材体验卡。我活动了一下手指,还好,能动。混乱的人群里,
一个穿着深青色长衫的男人格外显眼。他大概三十出头,身形挺拔,脸长得挺周正,
就是此刻面沉如水,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他没像其他人那样惊慌失措,只是站在原地,
目光沉沉地落在我身上,带着审视,还有一丝极力压抑的……惊疑?
这应该就是那位“夫君”,沈砚。他旁边还站着一个年轻女子,穿着月白色的衣裙,
头上簪着朵小白花,脸上还挂着泪珠,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只是此刻,
她脸上的惊恐比悲伤更真实,一只手死死抓着沈砚的袖子,指甲都快掐进他肉里了。
沈砚似乎毫无所觉,依旧盯着我。这应该就是那位传说中“温柔可人”的庶妹,林娇。
原主的记忆碎片像潮水一样涌进我的脑子。我是王静婉。沈砚明媒正娶的正妻。出身商户,
嫁妆丰厚。性格……怎么说呢,有点懦弱,有点死心眼,还有点不合时宜的清高。
嫁进沈家三年,无子。前几日“病”了,然后“病逝”了。怎么病的?原主的记忆很模糊。
只记得喝了庶妹林娇亲手端来的“补药”后,就开始昏昏沉沉。然后就躺进了这口棺材。
至于林娇,是原主父亲一个不受宠的妾室生的。原主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后,
对这前头夫人留下的女儿更不上心。林娇从小就会看眼色,在原主面前装得乖巧温顺,
背地里心思不少。她一直倾慕沈砚,原主嫁过来后,她更是以“陪伴姐姐”为由,
三天两头往沈府跑。沈砚对原主,说不上坏,但也说不上好。相敬如“冰”。
他对林娇的温柔体贴倒是很受用。原主的愿望?没有具体的。只有一股强烈的不甘和怨气,
沉甸甸地压在心头。不甘心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不甘心看着自己的一切被林娇夺走。
行吧,明白了。“搞破坏”,从诈尸开始。我扶着棺材边沿,有点笨拙地往外爬。
寿衣有点长,绊了一下脚。我踉跄一步,差点摔倒。“啊!”人群又是一阵骚动,退得更远。
我站稳了,拍了拍寿衣上沾的灰。抬起头,目光直接对上沈砚那深潭似的眼睛。“吵什么?
”我的声音有点哑,带着刚睡醒的迷糊劲儿,还有点不耐烦,“睡个觉都不安生。
”全场死寂。连刚才吓得抽噎的几个小丫头都死死捂住了自己的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法,惊恐地看着我。睡觉?在棺材里睡觉?沈砚的眉头狠狠拧了起来,
眼底的惊疑更深。他旁边的林娇,身体抖得更厉害了,抓着沈砚袖子的手用力到指节发白。
“夫……夫人?”终于,一个看起来像是管事的老仆,壮着胆子,颤巍巍地开口,
“您……您这是……”“我怎么了?”我揉了揉太阳穴,那里一跳一跳地疼,
“不就是睡了一觉吗?瞧把你们吓的。”我看向沈砚,
语气自然得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夫君,我睡了多久?头怎么这么疼?
”沈砚盯着我,眼神锐利得像是要把我剖开。他没回答我的问题,
反而沉声问:“你……感觉如何?”“感觉?”我低头又看看自己,“感觉……有点饿。
”这个回答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范围。灵堂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气声。
“静婉姐姐……”林娇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带着哭腔,怯生生地开口,
“你……你真的……活过来了?太好了!真是菩萨保佑!你不知道,这些天,
我和姐夫有多伤心……”她说着,眼泪又扑簌簌往下掉,试图靠近我。我抬手,
止住她的动作。“停。”我的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离我远点。你身上脂粉味太重,
熏得我头疼。我刚‘睡醒’,闻不得这个。”林娇的脚步僵在原地,
脸上的泪和可怜兮兮的表情也僵住了。她大概从来没想过,
一向对她还算和气的“静婉姐姐”,会用这种嫌弃的口吻跟她说话。
沈砚的目光在我和林娇之间扫了一下,眼神晦暗不明。“既然夫人……无恙,
”沈砚缓缓开口,声音低沉,“来人,扶夫人回房休息。请大夫过来仔细诊脉。”他顿了顿,
目光扫过一片狼藉、人心惶惶的灵堂,“灵堂撤了。今日之事,任何人不得外传,
违者家法处置。”几个胆大的婆子战战兢兢地挪过来,想扶我,又不太敢碰我。“不用扶。
”我摆摆手,“我自己能走。”我抬脚,跨出了那口晦气的棺材。踩在坚实的地面上,
感觉好多了。我径直朝灵堂外走去,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看我的眼神跟看什么怪物一样。
路过沈砚身边时,我停了一下,侧头看他。“对了,”我像是突然想起来,
“我‘睡’着的时候,好像做了个梦。梦见有人给我灌药,灌得特别急,差点呛死我。
”我笑了笑,目光若有似无地瞟过林娇瞬间惨白的脸,“那药的味道……啧,又苦又涩,
还有点怪味儿,跟娇妹妹上次端给我的那碗‘补药’,味道一模一样呢。”说完,
我不再看他们瞬间剧变的脸色,径直走了出去。留下身后一片死寂,和无数惊疑不定的目光。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深吸一口气。破坏第一步:物理惊吓达成。顺便,埋个种子。
回到“我”住的静心苑,院子里的丫鬟婆子看到我,那表情,跟活见了鬼没两样。
胆子小的直接就跪下了,筛糠似的抖。“都起来。”我挥挥手,懒得废话,“该干嘛干嘛去。
打盆热水来,我要洗脸。再弄点吃的,清淡点,饿死了。”一个叫翠竹的大丫鬟,
看起来还算镇定,虽然脸色也白着,但还是麻利地指挥着人打水、准备吃食。
我坐在梳妆台前。铜镜里映出一张脸。眉眼清秀,皮肤白皙,只是没什么精神气,
透着大病初愈的憔悴。这王静婉,底子是不错的,就是被自己那性子耽误了。洗了把脸,
换了身常服。大夫也来了,是府里常用的老大夫,胡子都白了。给我诊脉的时候,
那手指头抖得,差点按不准脉门。“夫人……脉象……嗯……虽然虚弱,
但……但生机……尚存……奇哉,奇哉……”老大夫捋着胡子,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嘴里念念叨叨,“怪事,怪事啊……前几日明明……”“明明什么?”**在软枕上,
懒洋洋地问,“明明该死了?”老大夫一哆嗦,差点把胡子揪下来:“夫人恕罪!老朽失言!
失言!夫人福泽深厚,得上天庇佑,逢凶化吉,必有后福!”他赶紧改口,额头都冒汗了。
“行了。”我摆摆手,“开点安神调理的方子吧。没事了,你下去吧。”老大夫如蒙大赦,
赶紧收拾药箱溜了。翠竹端着熬好的小米粥和几碟清淡小菜进来。我慢条斯理地吃着。
味道还不错。“夫人,”翠竹站在一旁,犹豫了一下,还是低声开口,
“您……您真的没事了?”“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我喝了口粥。
“不像……”翠竹摇摇头,眼神复杂,“只是……太吓人了。您是没看见,
灵堂里当时……”“看见了。”我打断她,“挺热闹。”翠竹噎了一下,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她感觉夫人好像哪里不一样了。以前夫人说话总是温温柔柔,
带着点怯意,现在……好像什么都不在乎,还有点……懒洋洋的痞气?
“府里现在都怎么说我的?”我问。翠竹脸色变了变,支吾着不敢说。“直说。
”“是……是……”翠竹一咬牙,
“下人们都在传……说夫人您……您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体了。还有的说,
您……您是狐仙娘娘显灵……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她声音越来越小。“哦。”我点点头,
继续喝粥,“狐仙娘娘?这说法新鲜。”我笑了笑,“告诉他们,狐仙娘娘喜欢吃烧鸡,
以后多备点。”翠竹:“……”她彻底懵了。一碗粥下肚,胃里舒服多了。我擦了擦嘴。
“林娇呢?我‘死’后,她是不是一直住在府里?”翠竹点头:“是。
二**说……不放心姐夫一个人,留下来帮着料理……料理后事。一直住在西厢的暖香阁。
”“呵,她倒是不避嫌。”我站起身,“走,去看看我这位‘好妹妹’。
”翠竹一惊:“夫人,您现在去?二**她……她可能吓得不轻,
还没缓过来……”“就是因为她吓得不轻,我才要去看看她啊。”我理了理衣袖,
笑得格外“和善”,“姐妹情深嘛。”暖香阁离主院不远。我带着翠竹,慢悠悠地晃过去。
一路上遇到的仆从,无不退避三舍,眼神躲闪,恭敬里透着恐惧。刚到暖香阁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低低的啜泣声,还有丫鬟小声劝慰的声音。“**,您别哭了,
仔细伤了眼睛……”“我……我害怕……她真的……回来了……她是不是知道……”“嘘!
**慎言!隔墙有耳啊!
……她看我的眼神……好可怕……她是不是……是不是来索命的……”我示意翠竹不用通报,
直接推门走了进去。屋里的声音戛然而止。林娇正坐在窗边的软榻上,眼睛红肿,
拿着帕子拭泪。旁边一个贴身丫鬟,叫春杏的,正给她倒茶。看到我进来,
春杏手里的茶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热水溅了一地。林娇更是像被针扎了一样,
猛地从软榻上弹起来,脸色煞白,惊恐地看着我,下意识地往后退,差点被矮几绊倒。
“姐……姐姐……”她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哟,哭着呢?”我走过去,
自顾自地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姿态闲适,“哭什么?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该高兴才对啊。
”林娇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春杏赶紧跪下行礼,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我。“怎么,
看见我活着回来,妹妹不高兴?”我挑眉,看着林娇。“不……不是!”林娇慌忙摆手,
眼泪又涌了出来,“姐姐能回来,我……我高兴!真的高兴!
就是……就是太意外了……太……太惊喜了……”她语无伦次。“惊喜?
”我玩味地看着她惨白的脸,“我看是惊吓吧。瞧瞧这小脸白的。”我伸手,
作势要去摸她的脸。林娇吓得尖叫一声,猛地往后一缩,撞在窗棂上,
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姐姐别碰我!”她失声喊道,带着哭腔。我的手停在半空,
然后慢慢收回,脸上的笑容也淡了下去。“怎么?嫌我身上有棺材味儿?”“不是!
不是的姐姐!”林娇意识到自己反应过激,连忙解释,眼泪流得更凶了,
“我……我只是……姐姐刚醒,我怕……怕冲撞了……”“冲撞?”我嗤笑一声,
“我人都躺棺材里又爬出来了,还怕什么冲撞?”我站起身,踱步到梳妆台前,
随手拿起一个精致的白玉簪子把玩。“妹妹这暖香阁布置得真不错,比我那静心苑还雅致。
看来妹妹在这里住得很舒心啊。”林娇的脸色更白了,
手指紧紧绞着帕子:“姐姐……这都是姐夫……是姐夫怜惜我孤身一人,才……”“哦?
姐夫怜惜你?”我打断她,转过身,眼神直直地看着她,“怜惜到让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
住进姐夫家后院,一住就是好几天?这传出去,好听吗?知道的,说妹妹你情深义重,
不顾名节也要帮姐夫料理姐姐的后事。不知道的……”我拖长了语调,眼神变得锐利,
“还以为我这个正头娘子尸骨未寒,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要鸠占鹊巢呢!”“我没有!
”林娇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尖声反驳,身体抖得更厉害了,“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只是……只是心疼姐夫……我……”“心疼姐夫?”我冷笑一声,
把玩着那根冰凉的白玉簪,“你心疼姐夫的方式,就是在他妻子‘病重’的时候,
天天给他端汤送水,嘘寒问暖?就是在我‘头七’还没过的时候,就穿着素衣小白花,
在他身边哭得梨花带雨,抓着他的袖子不放?”我的目光扫过她头上那朵刺眼的小白花,
再扫过她因为刚才拉扯而有些松散的衣襟。林娇的脸瞬间涨红,又迅速褪去血色,
变得惨白如纸。她像是被剥光了衣服丢在大街上,所有的算计和伪装都被我**裸地撕开。
“姐姐……你误会了……我……”她还想辩解,声音却虚弱无力。“误会?”我走到她面前,
距离很近,能清晰地看到她眼底的恐惧和慌乱。“娇妹妹,”我压低了声音,
带着一种冰冷的、只有她能听清的恶意,“我‘睡着’的时候,梦见的那碗又苦又涩的药,
味道是不是特别难忘?”林娇的瞳孔骤然收缩到极致,呼吸猛地一窒,身体晃了晃,
要不是春杏及时扶住,她恐怕会直接瘫软在地。她死死地盯着我,嘴唇翕动着,
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只有无尽的恐惧从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溢出来。“看来妹妹记性不太好。
”我直起身,恢复了平常的音量,脸上甚至还带着点笑意,“没关系,姐姐我记性好就行。
”我把那根白玉簪随意地丢回梳妆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好好休息吧,妹妹。
‘惊喜’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我意味深长地看了她最后一眼,转身,
带着翠竹离开了暖香阁。身后,传来林娇压抑不住的、崩溃般的哭声。
破坏第二步:心理碾压达成。种子开始发芽。接下来的几天,沈府的气氛诡异到了极点。
表面上,一切如常。灵堂撤了,白幡摘了。下人们该干嘛干嘛,只是走路都踮着脚尖,
说话都压低了声音,眼神交流时充满了心照不宣的恐惧和八卦欲。暗地里,暗流汹涌。
我这位“死而复生”的夫人,成了府里最大的禁忌,也是最热门的话题。
各种离奇的猜测满天飞。狐仙附体、怨灵复仇、阎王不收……版本越来越离谱。我乐得清闲。
每天在静心苑吃吃喝喝,睡睡懒觉,偶尔在府里溜达一圈,所到之处,众人退散,
效果堪比清场。沈砚没来看我。一次都没有。但他肯定在关注我。我能感觉到,
暗处总有视线。府里的护院巡逻也比以前勤快了不少,尤其是静心苑附近。林娇则彻底蔫了。
据翠竹“无意”中听来的消息,暖香阁那位,是真病了。高烧不退,噩梦连连,
整日胡言乱语,喊着“别过来”、“不是我”、“药……药……”。春杏急得团团转,
大夫也请了好几个,汤药灌下去也不见好。活该。亏心事做多了,自己吓自己。这天下午,
我正在院子里晒太阳,眯着眼,琢磨着下一步搞点什么破坏才够劲。翠竹匆匆进来,
脸色有点古怪:“夫人,老爷……老爷让您去书房一趟。”哦?终于憋不住了?
我懒洋洋地起身,伸了个懒腰:“知道了。带路。”沈砚的书房在府邸前院,
布置得倒是清雅。书卷气很浓。他背对着门口,站在一幅山水画前,身姿挺拔,
却透着一股化不开的沉郁。“夫君找我?”我走进去,随手带上门。沈砚转过身。几天不见,
他眼下有淡淡的青黑,看来也没睡好。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探究、警惕、怀疑,
还有一丝极力隐藏的……疲惫。“坐。”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声音听不出情绪。
我依言坐下,姿态放松,甚至有点随意。“身体可大好了?”他开口,是公式化的询问。
“能吃能睡,好得很。”我回道。书房里陷入沉默。空气有些凝滞。沈砚踱了两步,
似乎在斟酌词句。最终,他停在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目光锐利如刀锋,
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静婉,”他开口,声音低沉缓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来了。终于问出口了。我抬起头,迎上他审视的目光,
脸上没什么表情:“夫君这话问得奇怪。我是王静婉,你的妻子。还能是谁?
”“我的妻子王静婉,”沈砚紧紧盯着我的眼睛,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变化,“她温婉守礼,
从不逾矩。她待下宽和,对娇妹更是视若亲妹。她知书达理,
不会……不会像你这般……”他似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我现在的样子。
“不会像我这般死而复生?不会像我这般说话刻薄?不会像我这般吓唬你的‘娇妹’?
”我替他把话说完,语气带着点嘲讽。沈砚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你承认了?
你承认你不是她?”“我承认什么了?”我无辜地摊手,“我不过是‘病’了一场,
差点见了阎王,想通了一些事而已。难道夫君希望我继续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
被人欺负到死,最后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吗?”我的语气冷了下来。
“你……”沈砚被我的话堵了一下,眼神更加锐利,“那碗药!你对娇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梦见了什么?你究竟知道些什么?”他逼近一步,气势迫人。“我知道什么?”我站起身,
毫不示弱地回视他。身高上虽然矮他一截,但气势上不能输。“我知道有人趁我病,要我命!
我知道有人假惺惺地端来毒药,说是‘补药’!我知道有人在我尸骨未寒的时候,
就迫不及待地想爬上姐夫的床!”我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像冰冷的钉子,
狠狠砸进沈砚的耳朵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眼神剧烈地波动着,
震惊、愤怒、还有一丝……被戳穿的狼狈?但他毕竟是沈砚,城府极深。
他很快压下翻腾的情绪,眼神变得更加幽暗危险。“空口无凭!静婉,你死而复生,
本就离奇。如今又说出这等惊世骇俗、污人清白的话来!你有何证据?”他厉声质问,
试图夺回主动权。“证据?”我笑了,笑容里带着一丝怜悯,看着他,“沈砚,
你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只是你不愿意承认罢了。你怀疑我,
不过是因为我打破了你的平衡,戳穿了那层虚伪的窗户纸,
让你不能再心安理得地享受两个女人的‘温柔’!”我向前一步,几乎与他鼻尖相对。
我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冰冷的、洞穿人心的力量:“你看着我‘病重’,
难道就真的一点疑心都没有?林娇为什么那么热切地亲自照料我?为什么我一‘死’,
她就顺理成章地留下来,对着你哭得那么惹人怜爱?沈砚,你不是傻子!你只是选择了装傻!
因为你享受她的温柔体贴,因为她比我这商贾之女更合你清高读书人的心意!因为我死了,
正好给你腾位置!”“你住口!”沈砚猛地低吼出声,额角青筋暴起,眼中怒火翻腾,
还有一丝被彻底撕开伪装的羞恼。他扬起手,似乎想打我。我非但不退,反而仰起脸,
眼神冰冷无畏地看着他:“打啊!沈砚!有本事你就打!
打我这个‘死而复生’、被‘不干净东西附体’的‘妖妇’!看看明天外面会怎么传!
看看你那清贵的名声,还能不能保得住!”我的手,藏在袖子里,
紧紧捏住了一个冰凉坚硬的东西——是刚才在暖香阁,
我顺手从林娇梳妆台上摸走的那根白玉簪的尖端。很锋利。我的声音不高,
却像淬了毒的冰针,直刺他心底最在意的地方——名声,清誉。沈砚扬起的手,
僵在了半空中。他死死地盯着我,胸膛剧烈起伏,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出来将我焚烧殆尽,
但那高高举起的手,却怎么也落不下来。书房里死一般寂静。只有我们两人粗重的呼吸声。
良久,沈砚猛地放下手,背过身去,肩膀微微颤抖。他的声音压抑到了极点,
带着一种挫败和疲惫:“你……你到底想怎么样?”破坏第三步:撕开伪善,直击要害。
平衡彻底打破。我看着他的背影,缓缓松开袖中紧握的簪尖。手心有点湿,是被汗浸的。
“我不想怎么样。”我的语气恢复了平静,甚至带着点事不关己的漠然,
“我只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不想被人当傻子耍。至于以后……”我顿了顿,走到书桌前,
拿起他桌上的一方上好的端砚。沉甸甸的,触手冰凉温润。“这砚台不错。”我掂量着,
“可惜,装错了墨。”我手一松。“啪嗒!”砚台掉在地上,摔成了好几瓣。
漆黑的墨汁溅开,弄脏了干净的地毯和沈砚的衣摆。沈砚猛地回头,
看着地上碎裂的砚台和污渍,脸色铁青。“沈砚,”我看着他难看的脸色,一字一句地说,
“从棺材里爬出来那一刻起,以前那个任人揉捏的王静婉,就真的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