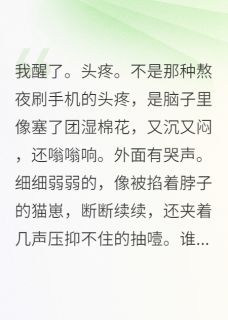
然后,我拉着谢言蹊,在无数道复杂目光的洗礼下,昂首挺胸(一瘸一拐)地走出了祠堂。
外面天色更暗了,豆大的雨点开始砸落。
“下雨了!快跑!”我喊了一声,拉着谢言蹊就往家冲。
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身上,生疼。但我和谢言蹊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跑得飞快。
跑过泥泞的村道,跑过惊飞的鸡鸭,跑过那些依旧站在屋檐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的村民。
冲进自家那破院门,关上吱呀作响的破木门,背靠着门板,我和谢言蹊都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雨水顺着头发、脸颊往下淌。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狼狈的样子。
他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小脸沾了泥水,嘴唇因为刚才咬手指还留着一个浅浅的牙印。我也好不到哪去,像个落汤鸡。
但我们的眼睛都很亮。
“哥……”他喘着气,突然笑了。不是那种怯懦的笑,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带着点小小得意的笑,露出两颗尖尖的小虎牙。
“嗯?”我也忍不住笑,扯动了咬破的手指,疼得龇牙咧嘴。
他伸出手,摊开小小的手掌。掌心里,躺着两颗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藏起来的、快要融化的饴糖。大概是之前村里谁家办喜事发的,被他宝贝似的藏到现在。
“给,”他把一颗稍微大点的糖递给我,自己留下那颗小的,“甜的……止疼。”
我看着他掌心里那颗沾了雨水、有些黏糊糊的糖,又看看他亮晶晶的、带着点讨好和期待的眼睛。
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又软又涩。
“好!”我接过那颗糖,剥开黏在糖纸上的糖,看也没看就塞进嘴里。劣质的甜味混着雨水和淡淡的血腥气在口腔里化开,有点奇怪,但又莫名地……很暖。
“走!换衣服去!别着凉了!”我把另一颗糖塞回他手里,“你的,自己吃!”
雨越下越大,砸在屋顶的茅草上,噼啪作响。
破屋里,我和谢言蹊换下了湿衣服(他的衣服还是太小,我的外衫太大,穿在他身上像唱戏的),挤在灶膛边烤火。跳跃的火光映着两张洗干净的脸。
“哥,”谢言蹊小口小口地舔着那颗饴糖,忽然小声问,“拜了把子……是不是以后……真的一直是兄弟了?”
“那当然!”我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苗蹿高了些,“文书都写了!血手印都按了!祖宗都见证过了!板上钉钉!以后咱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呸!不对,是亲姐弟!比亲的还亲!”
他低着头,没说话,只是小口舔糖的动作更慢了,嘴角却悄悄地、一点一点地弯了起来。
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
日子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至少,谢言蹊不再像惊弓之鸟。他依旧话不多,但眼神里多了点活泛气儿,看我的时候,也不再是纯粹的恐惧。
他开始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比如天刚蒙蒙亮,他就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提着家里那个破木桶,去村头那口老井打水。小小的身子摇摇晃晃,打满半桶水,一路歇几次才能提回来,倒进快要见底的水缸里。
我睡眼惺忪地起来看到,水缸里多了小半缸清水,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以后打水叫哥!”我揉着他的小脑袋。
他摇摇头,小声说:“我能行。哥……你可以多睡会儿。”
家里的柴火快没了。我扛着柴刀,准备去后山砍点枯枝。谢言蹊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我后面。
到了林子里,我笨手笨脚,半天砍不断一根稍粗的树枝。谢言蹊却像只灵活的小猴子,在灌木丛和低矮的树枝间钻来钻去,不一会儿就捡了一大捆细小的、干燥的枯枝,用藤条捆得整整齐齐。
“哥,这些引火好。”他把柴捆放在我脚边,小脸上沾了点泥,眼睛亮晶晶的。
我看着他那捆柴,再看看自己脚边那几根歪歪扭扭的粗枝,默默收起了柴刀。
行吧,生存技能再次被碾压。捡柴小能手,非他莫属。
最要命的是吃饭问题。
我尝试着煮了几次饭,不是糊锅就是夹生。炒菜?那更是灾难现场。油星子溅得到处都是,菜要么齁咸要么没味,炒出来黑乎乎一坨,连我自己都难以下咽。
谢言蹊每次都默默地吃,从不抱怨。
直到有一次,我雄心勃勃想做个土豆炖肉(肉是里正家办喜事,我厚着脸皮去帮忙洗碗,人家给的一小块边角料),结果差点把灶房点了。浓烟滚滚,我被呛得眼泪鼻涕横流跑出来。
谢言蹊默默地从角落搬来个小板凳,踩上去,拿起锅铲,像个小大人一样,动作麻利地把锅里半焦的土豆和肉块扒拉出来,又往锅里添了点水,搅了搅。
然后,他跳下板凳,把一碗勉强能看的、糊糊状的“土豆炖肉”端到我面前。
“哥,吃。”他声音平静。
我看着他小脸上蹭的锅灰,再看看那碗卖相惨不忍睹但至少没毒的东西,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被孩子养着”的羞耻感。
“那个……言蹊啊,”我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要不……以后做饭的活儿……还是你来?”
他抬起头,大眼睛眨了眨,很认真地说:“好。”
从此,家里掌勺大权,正式移交六岁孩童。
生活清苦,但似乎有了点盼头。
我琢磨着怎么赚钱。坐吃山空不行,那点糙米和土豆撑不了几天。
原主懒,家里没地,就屋后一小块菜地也荒着。
我想起以前看的小说,穿越女靠美食发家?可我那手艺……还是别祸害乡亲了。
做肥皂?香皂?玻璃?别逗了,化学方程式早忘光了。
思来想去,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上山。
后山不高,林子挺密。春天了,野菜野果应该不少。运气好,说不定能采点蘑菇,或者挖到点值钱的草药?
这天天气好,我背上家里唯一的破背篓,带上小锄头(谢言蹊捡柴火用的),准备进山。
“哥,我也去。”谢言蹊立刻放下手里正在剥的豆子(准备午饭),跑到我身边。
“山里可能有蛇虫,危险。”我有点犹豫。
“我不怕!”他挺起小胸脯,“我认识路!还认识好多能吃的叶子!”
我想起他捡柴火的利索劲儿,点点头:“行!跟紧哥!”
后山的林子比我想象的茂盛。空气清新,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谢言蹊果然像回了家一样。他灵活地在前面带路,小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地面和灌木丛。
“哥!看!荠菜!包饺子可香了!”他指着草丛里一簇开着小白花的嫩绿野菜。
“哥!那边!野葱!炒鸡蛋好吃!”
“哥!小心刺!那是刺泡儿,红的才能吃,酸酸甜甜的!”
他像个小小的博物学家,如数家珍。
我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跟在他后面,他指哪我挖哪。背篓里很快铺了一层鲜嫩的荠菜、野葱,还有几颗红艳艳的刺泡儿。
“言蹊,你真行!”我由衷地夸赞,摘了一颗熟透的刺泡儿塞进他嘴里。
他眯起眼睛,满足地嚼着,小脸上满是得意。
我们越走越深,林子也越发幽静。突然,谢言蹊停住了脚步,小鼻子抽了抽。
“哥!你闻!”
我使劲嗅了嗅,除了草木清香,好像……是有股淡淡的、奇异的香味?有点像……橘子皮混着某种香料?
“这边!”谢言蹊拉着我,拨开一片茂密的藤蔓。
眼前豁然开朗一小片空地。空地边缘,紧挨着一块巨大的岩石,生长着几株奇怪的植物。半人多高,叶子细长,开着不起眼的小白花。但那奇异的香气,正是从它顶端结着的几颗青绿色、拇指大小的椭圆形小果子散发出来的!
“这……这是什么?”我从未见过。
谢言蹊眼睛发亮,声音带着点激动:“是山胡椒!也叫木姜子!我爹……以前带我采过!做鱼去腥,炒菜增香,可好吃了!晒干了还能卖钱!药铺有时候收!”
山胡椒?木姜子?我好像有点印象,是种香料!
看着那几株挂满青果的灌木,我仿佛看到了一串串铜钱在向我招手!
“太好了!快摘!”我立刻放下背篓,和小不点一起,小心翼翼地采摘那些青翠欲滴的小果子。果子很嫩,一碰就掉,我们摘得格外小心。
背篓的角落里,很快堆起一小捧散发着浓郁香气的山胡椒果。
“别摘光,留点小的,等它再长长。”谢言蹊小声提醒,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农。
“嗯!听你的!”我乐得合不拢嘴。
回家的路上,我们脚步都轻快了许多。背篓里除了野菜,还有了能换钱的宝贝。
路过村口那棵大槐树,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在树下玩石子。看到我们,其中一个穿着绸布坎肩、长得胖墩墩的孩子,正是之前被我在祠堂前“英雄救美”时忽略了的另一个小霸王——钱富贵。他爹是村里少有的富户,开了个杂货铺。
钱富贵看见谢言蹊,又看到他背篓里露出的新鲜野菜和刺泡儿,眼珠一转,带着两个跟班就拦住了我们的路。
“喂!拖油瓶!”钱富贵叉着腰,趾高气扬,“背的什么好东西?拿出来给少爷我瞧瞧!”
谢言蹊脚步一顿,下意识地往我身后缩了缩,小手抓紧了背篓带子。
我眉头一皱,把谢言蹊护在身后,冷着脸:“钱富贵,干什么?又想抢东西?”
“谁抢了?”钱富贵翻了个白眼,指着谢言蹊的背篓,“他一个吃白食的,能有什么好东西?肯定是偷的!本少爷检查检查!”
说着,他伸手就要来扯谢言蹊的背篓。
“滚开!”我一把拍开他的胖爪子。
“你敢打我?!”钱富贵没想到我这么横,愣了一下,随即恼羞成怒,“给我上!把背篓抢过来!”
他身后两个小跟班平时就唯他马首是瞻,立刻张牙舞爪地扑上来。
要是以前,谢言蹊肯定吓得掉头就跑或者任人欺负了。
但这次,他非但没跑,反而猛地从我身后钻出来,像只被激怒的小豹子,张开瘦小的手臂挡在我前面(虽然只到我腰那么高),对着扑过来的跟班大声喊道:
“不准抢!这是我哥的东西!谁敢动!”
他声音因为激动而尖利,小脸涨得通红,眼神却凶得很。
我愣了一下,随即心里涌上一股暖流。好小子!有胆气!
钱富贵也被谢言蹊这副拼命的样子吓了一跳,但他仗着人多,更恼火了:“反了你了!给我打!”
两个跟班已经冲到近前,其中一个伸手就去推谢言蹊。
我眼神一厉。
“找死!”
我可不是吃素的!连王二狗我都揍了,还怕你们几个小崽子?
我一把将谢言蹊拉到身后,抬脚就踹在那个伸手推人的跟班肚子上!力道控制着,不会真伤着,但足够让他哎哟一声,捂着肚子蹲下去。
另一个跟班挥着拳头冲过来,被我侧身躲过,顺手抓住他的胳膊,一拧一带,直接把他摔了个**墩儿。
动作干净利落,得益于原主这具身体干惯了粗活的力气,和我现代看过的几部动作片(虽然主要靠王八拳)。
三下五除二,两个跟班都躺在地上哼哼唧唧。
钱富贵傻眼了,看着一步步朝他走近的我,吓得连连后退,胖脸上的肥肉都在抖:“你……你……后娘瘟……你想干什么?我告诉我爹!”
“告诉你爹?”我狞笑着捏了捏拳头(其实手指咬破的地方还有点疼),“好啊!顺便告诉你爹,你带着狗腿子,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还欺负我兄弟!看里正是信你这个抢东西的小**,还是信我这个在祖宗面前立了誓、要保护兄弟的姐姐!”
我特意把“祖宗面前立了誓”几个字咬得很重。
钱富贵显然也听过我在祠堂的“壮举”,脸色白了白,色厉内荏地喊道:“谁……谁抢了!我就是看看!”
“看看?”我指着地上那两个还没爬起来的跟班,“看看需要动手?需要推人?”
“我……我……”钱富贵词穷了,看着我又凶又横的样子,再看看谢言蹊虽然害怕却紧紧抓着背篓、站在我身边的样子,他最终一跺脚,撂下句狠话,“你们等着!”然后拉起地上的两个跟班,灰溜溜地跑了。
围观的孩子发出一阵哄笑。
我这才转身,蹲下来看着谢言蹊:“没事吧?吓着没?”
谢言蹊摇摇头,小胸脯还在微微起伏,但眼睛亮得惊人,看着我,小声说:“哥……你真厉害。”
我揉揉他的脑袋,心里美滋滋的:“那必须!说了罩着你!走,回家!今天加餐!”
背篓里那捧山胡椒,像是我们小小的宝藏。
我把它们小心地铺开在窗台上晾晒。谢言蹊每天都去翻动几次,宝贝得不得了。
几天后,青翠的果子变得有些干瘪,颜色也深了些,但那股奇特的香气更加浓郁了。
“哥,晒好了。”谢言蹊捧着一小把干山胡椒,献宝似的递给我。
我捏起一颗闻了闻,香气扑鼻。这玩意儿,在缺调料的古代农村,绝对是宝贝!
“走!哥带你去换钱!”我豪气干云。
目标:钱记杂货铺。
钱富贵他爹钱有财,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留着两撇小胡子,眼睛滴溜溜转,一看就很精明。他正坐在柜台后面拨弄着算盘。
看到我牵着谢言蹊进来,他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显然也听说了我最近的“丰功伟绩”和儿子吃瘪的事。
“苏娘子,有事?”他语气冷淡,带着防备。
我懒得废话,直接把那小捧干山胡椒放在柜台上。
“钱掌柜,看看这个,收不收?”
钱有财瞥了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随即又恢复精明:“哦,山胡椒啊。这玩意儿山上多的是,不怎么值钱。”
“是吗?”我笑了笑,也不急,“我闻着挺香的。听说炖鱼炖肉去腥增香是一绝?镇上馆子里好像挺稀罕这个味儿?”
钱有财捻起一颗,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又用手指搓了搓:“嗯……品质还行。不过,量太少了。顶多……给你五文钱。”
五文钱?够买两个鸡蛋了。但我看他刚才那表情,绝对不止这个价。
“五文?”我嗤笑一声,作势要把山胡椒收回来,“那算了,我留着自家用,还能多吃两顿香的呢!言蹊,走,咱去问问村头李屠夫,他杀猪炖肉多,肯定识货!”
“哎哎哎!别急啊苏娘子!”钱有财果然叫住我,脸上堆起假笑,“做生意嘛,可以谈!十文!怎么样?够厚道了吧?”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十五文。少了不卖。我明天还去采,量大管够。”我抛出一个诱饵。
钱有财眼珠转了转,似乎在权衡。这山胡椒确实是个好东西,镇上一些讲究的饭馆会收,价格比普通香料高不少。村里人懒,又不太认识,或者嫌麻烦不愿意跑山里去采。如果能长期收……
“行!十五文就十五文!”钱有财一拍大腿,像是吃了多大亏,“苏娘子爽快!以后采到好的,尽管送我这里来!价格好商量!”
他数出十五个铜板,叮叮当当地放在柜台上。
我一把抓起铜板,塞进怀里,心里乐开了花。十五文!这可是我们姐弟俩自己挣的第一笔钱!
“谢了钱掌柜!”我拉着谢言蹊,昂首挺胸地走出杂货铺。
谢言蹊一直没说话,小脸上却洋溢着兴奋的红晕。出了门,他紧紧挨着我,小声问:“哥,我们……有钱了?”
“对!有钱了!”我捏了捏他的手,感受着怀里那十五个沉甸甸的铜板,“走!哥给你买好吃的去!”
我拉着他,直奔村口那个挑着担子卖零嘴的老汉。
“老伯,来两根糖葫芦!”我财大气粗地喊。
老汉笑眯眯地递过来两根红艳艳、裹着晶莹糖壳的山楂糖葫芦。
我把其中一根塞到谢言蹊手里:“给!尝尝!”
谢言蹊拿着糖葫芦,眼睛瞪得溜圆,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他小心翼翼地伸出小舌头,舔了一下那层亮晶晶的糖壳,眼睛瞬间幸福地眯了起来。
“甜!”他小声说,又舔了一下。
“傻小子,咬一口!”我笑着,自己也咬了一大口。酸甜的山楂混合着脆甜的糖壳,在嘴里化开,幸福得直眯眼。
“哥,你也吃!”谢言蹊把他那根糖葫芦往我嘴边递。
我看着他清澈的眼睛,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就着他递过来的姿势,咬下了顶端最大最红的那颗山楂。
“嗯!真甜!”我含糊地说。
他看着我吃,笑得眉眼弯弯,这才心满意足地小口咬着自己那根。
夕阳西下,我和谢言蹊一人举着一根糖葫芦,走在回家的土路上。金色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糖葫芦很甜。
日子,好像也慢慢有了甜味。
靠着时不时上山采点山胡椒、野菜、蘑菇(谢言蹊成了我的活体指南针),偶尔运气好挖到点常见的草药,我们手里渐渐攒下了一小串铜板。
虽然依旧清贫,但至少不用再为下一顿饭发愁。谢言蹊的小脸上也多了点肉,不再是之前那种吓人的瘦削。
我以为日子会这样磕磕绊绊却也平淡安稳地过下去。
直到这天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