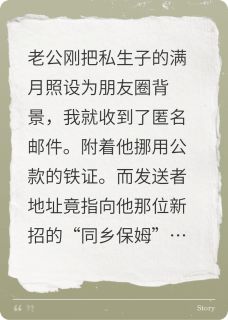
“哦?邮箱?匿名信?”他的声音再响起时,那点温和伪装被撕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一种刻意的、被冒犯后的“震惊”和“好笑”,“欣欣,我说什么来着?
肯定是竞争对手!那些眼红我们厂有点起色的小人在使坏!搞这种下三滥的把戏扰乱军心!
你怎么还信了?”他语调陡然严厉起来,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训斥味道:“那些东西能信吗?
指不定就是PS出来的!你身为老板娘,这点判断力都没有?心思全放那上面去了,
爸的身体还管不管了?厂里现在正是关键时候!我这几天为了那笔大订单跑断了腿,
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他开始了。指责,推诿,反咬一口,
顺便给自己树一个“为厂奔波”的劳苦人设。一套组合拳行云流水,熟练得令人作呕。
我握着手机,掌心冰凉一片,指甲深陷肉里,才不至于冷笑出声。
“可是……那单据……上面的章……看着……”我故意流露出一点犹豫和动摇,
声音更低更弱,仿佛真的被他那套说辞砸懵了。“欣欣!”顾远航的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怒气,彻底撕破脸皮,“你太让我失望了!为几张破纸你疑神疑鬼,
连带着爸的病都不顾了?你在哪?办公室?等着!我现在马上过去!”电话被粗暴地挂断,
只剩下一串忙音。“嘟…嘟…嘟……”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我慢慢放下手机,
手因为过于用力而微微颤抖。“怎么样?”林雪芬的声音在角落响起,平静无波。
“他急了。”我抬起眼,眼底再无半点之前的惊惶和脆弱,
只剩下冰冷刺骨的恨意和一种即将清算一切的平静,“电话里一套又一套,挂得比谁都快,
演戏演砸了,生怕我再说出点什么。他说……马上就过来。”“好得很。
”林雪芬面无表情地点头,顺手从办公桌角落的笔筒里抽出一支不起眼的记号笔,
扭开笔帽,里面不是笔芯,而是一个小小的发射装置,“就怕他不急。
”她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火柴盒大小的录音终端,上面一排极细微的指示灯闪烁着。
她将发射端对准终端的一个接口,只听“滴”一声极轻的蜂鸣,终端亮起一个小小的绿灯。
她动作流畅地把终端扔回给我,又顺手拿过桌上那个记录着最大一笔亏损项目的文件夹,
猛地将它扫落在地!文件夹撞倒我的水杯,发出刺耳的哗啦声响,几页纸散乱地飘出来,
正好掉在门口位置,杯里的水也迅速在地板上漫延开来,形成一小片狼藉的区域。
“待会儿他进门,你就坐这儿。”她指着散落文件的区域旁边的位置,“表情?
就跟你现在差不多。”她扫了我一眼,我的脸此刻不用演,
也必定是苍白紧绷、含着悲愤的样子,“我该走了。剩下的……”她看向我的眼神,
带着一种冰冷的信任,“唐**,麻烦你演到位,把他钉死。”说完,她迅速转身,
像一条融入阴影的鱼,
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财务办公室的后门——那里通向放清洁工具的小隔间。走廊里很静,
死一般的静。只有水杯破裂的残片在灯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那几页被水浸湿的纸,
半卷着摊在地上,像被人随手弃置的废品。我俯身,捡起其中一张,
湿漉漉的纸面几乎被我搓破。那正是八百万亏损项目的最后一页,
顾远航伪造的签字和他的印章清晰无比。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像钝刀子割肉。
走廊尽头终于传来熟悉的、急促的脚步声,皮鞋底重重敲击在光滑的水磨石地面上,
带着一种来势汹汹的浮躁和焦灼。来了!我捏着那张浸湿变软的文件纸,
感觉肺部的空气被一只无形的手急速抽空,一种类似失重的眩晕感猛地攫住了我。
视线开始模糊,
变成了一片晃动的色块——那杯子的反光、散落的纸页、地板上的水渍都变成了旋转的漩涡。
巨大的恐惧和一种更汹涌的反抗欲在胸腔里激烈冲撞,快要炸开。顾远航猛地推开门,
力道大得门板“砰”一声撞在墙上反弹回来又关上。“唐欣!”他几乎是吼进来的,
脸色因为疾步和装出来的愤怒而涨得通红,额角青筋毕露,眼神如同冰冷的探照灯,
子、摔在地上的水杯、散落的文件和……捏着湿透纸张、身体微微摇晃、脸色惨白如纸的我。
他冲到我面前,一把狠狠攥住我拿着文件的那只手腕!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
“你看看你!弄成什么鬼样子!”他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声音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
“就为了几张不知哪个龟孙子塞给你的破纸!你就敢跟我闹?疑神疑鬼,哭哭啼啼,
还有点老板娘的样子吗!”他另一只手猛地指向散落在地上的文件,
“还有心思看这些狗屁报表?!我不是说了我在忙大订单?!你这是在拖我后腿!
”他越说越激动,试图用吼声和气势彻底碾碎我的怀疑,
掩盖他眼底深处那一掠而过的心虚。手腕处传来的剧痛瞬间压过了眩晕。
我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要被他捏裂了!在他那扑面而来的、充满酒气和虚假愤怒的吼叫声里,
我的怒火“腾”一下顶到了天灵盖,烧得我浑身血液都沸腾起来!我像突然惊醒的猎物,
猛地用尽全身力气甩开他的手!“拖你后腿?!”我声音拔高,带着尖利的嘶哑,
眼眶瞬间就红了——这次是真的被气红的,“顾远航!你看看清楚!这到底是什么!
”我把那张湿透变形的纸举到他鼻子底下,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剧烈地颤抖,“八百万!
整整八百万!你跟我说是设备维修?!这是什么维修单?!
维修单上为什么盖着‘宏图贸易’的合同章?宏图那间破门脸,能修得了进口包装生产线?!
”每一句质问都像鞭子一样抽出去。顾远航瞳孔猛缩!
脸上那愤怒的面具出现了一丝明显的裂痕。宏图贸易!那是他秘密转移资金的通道之一!
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我会精准地戳到这个点!更没想到我拿着的正是这份该死的单子!
“你……你懂什么!”他色厉内荏地吼回来,声音因心虚而弱了半分,随即又拔高,
“商业机密!签个**维修外包协议不行吗!这有什么问题?
你一个成天围着医院灶台转的女人懂什么运作流程?少在这给我瞎掺和!
我看你就是失心疯了!”他伸手就要来夺那张纸。“宏图贸易的法人是谁?!
”我没有退让,反而向前逼近一步,用比他更大、更尖锐的吼声压回去,“是刘老三!
是你那个开**、三年前就卷款跑路的赌棍牌友!”这句话,像一颗点燃的炸弹,
被我狠狠砸了出来!办公室狭小的空间里,空气仿佛瞬间被抽干了。
顾远航那只伸出来夺纸的手僵在了半空中,所有的动作和表情都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他的脸上血色“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煞白一片,连嘴唇都在哆嗦。
那双刚才还盛满虚假怒火的眼睛里,只剩下了最原始的惊恐和被撕破一切伪装的难以置信。
他似乎想说什么,嘴唇翕动了一下,却只发出一种类似垂死鱼类的嗬嗬漏气声。
贸易……刘老三……**……这些从我这个“只懂围着灶台转”的妻子嘴里爆出来的词,
像淬毒的钢针,精准地扎穿了他最后一层防护!彻底击碎了他编织的谎言王国!
原来我真的知道了?知道得如此深入?这死寂般、令人窒息的几秒钟,
比任何刀光剑影都更有力地宣告了他的完败。我死死盯着他瞬间灰败的脸,
那种猎物终于踩入陷阱的掌控感,夹杂着无边愤怒和悲凉,像滚烫的岩浆在我胸口奔涌。
下一秒——办公室那扇薄薄的木门被从外面重重推开!“刘老三?**?
”突兀的声音如同冰冷的铁锤,瞬间砸碎了办公室内凝固的对峙。
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不合身廉价西装的男人堵在了门口。
闲云阁”的“朋友”——放高利贷起家、这几年摇身一变号称“民间资本运作人”的张麻子!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流里流气的年轻混混。
张麻子那张坑洼不平的脸上全是错愕和刚刚酝酿到一半的贪婪被打断的愠怒。顾远航的脸,
惨白得像一张揉皱了的废纸,刚才的震惊和恐慌还未退去,
此刻骤然叠加了被债主堵门的难堪和恐惧,眼珠子都瞪圆了。“顾老板!
你不是拍胸脯说你这厂子现金流稳稳当当,拿股份抵押绝对铁板钉钉?!这叫铁板?!
”张麻子几步跨进来,指着散落一地的文件和被我举在手里正滴水的单据,嗤笑道,
“连你婆娘都追着你要钱?八百万!刘老三?宏图?**当老子是瓜娃子好糊弄嗦?!
”一口夹杂着市井气的方言喷薄而出。顾远航猛地回过神,脸上肌肉抽搐着,
试图挤出一个安抚的笑:“张、张哥!误会!这都是误会!厂子里的事情复杂,
我跟我老婆……闹点别扭!不影响咱谈正事!走走走,
咱换地方说……”他慌不迭地去推张麻子的胳膊,想把瘟神弄走。“误会?
老子在隔壁包间茶都灌了一肚子,耳朵没聋!”张麻子一把甩开顾远航的手,
力气大得他一个趔趄,眼神却像淬了毒的刀子一样钉在我脸上,“弟妹是吧?这闹的哪一出?
顾老板,你这抵押品,啧啧,水分有点大哦?”他显然不是来主持公道的,而是嗅到了腥味,
想趁机压价捞一笔大的。顾远航急了,声音都变了调:“张麻子!
我跟唐欣的家事轮不到你插嘴!我们马上出去谈!”“顾远航!”我厉声尖叫,
泪水瞬间夺眶而出(一半是愤怒激出来的,另一半是给张麻子看的),
举起那张湿淋淋的单据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刻意放大,每一个字都像泣血的指控,
“爸现在还在ICU一天一万地烧着钱!我等你这钱救命!你说钱压在设备上!好!
你告诉我!这宏图贸易是什么设备?!你把我家厂子当什么了?!你的私房钱提款机吗?!
”“闭嘴!”顾远航恼羞成怒,彻底撕破脸皮,狰狞地扬起巴掌!
这一巴掌夹带着他滔天的恐慌和暴戾!“啪!”一声脆响,并非抽在脸上。我早有防备,
在那巴掌挥过来的瞬间,身体一偏,同时手里捏着那张纸的手臂猛地向上格挡!
纸张被他粗大的手指扫到,本就湿软的纸张瞬间被撕裂,一大半碎片飘落。但另一小半,
被我死死捏住的残存部分,正好扫在他鼻梁上那副价值不菲的金丝眼镜!
眼镜被他自己的力道带飞出去,“哗啦”一声摔在几米外的水泥地上,镜片当场碎裂!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更是火上浇油。顾远航眼前一花,彻底暴怒失去了理智:“唐欣!你找死!
”他像一头红了眼的疯牛,不管不顾地朝我扑过来!
张麻子带来的混混眼疾手快(更像是怕顾远航真发疯毁了他们“生意”),
一把从后面死死抱住了顾远航的腰:“顾老板!顾老板冷静点!有话好说!”场面瞬间混乱!
顾远航怒吼挣扎,混混奋力箍着他,张麻子一脸幸灾乐祸又带着精明算计地冷眼旁观。而我,
缩在墙角,披头散发,泪流满面,一只手痛苦地捂着方才被他抓红的手腕,
另一只拿着半张湿透残纸的手,正对着张麻子他们进来的门口方向,抖得如风中秋叶。
手臂内侧,那个火柴盒大小的录音终端指示灯在混乱中不易察觉地急速闪烁了几下,
完成了最后一段关键录音的上传——顾远航那句怒吼清晰的“找死”,
成了绝佳的暴力威胁证据。就在这时,办公室虚掩的门又一次被轻轻推开。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工作服、拿着扫帚和簸箕的身影低着头走了进来,动作麻利但有些畏缩,
正是那个清洁工“阿芬”。她似乎被眼前的混乱场面吓住了,站在门口手足无措,
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没人注意到她。顾远航还在和混混扭打,张麻子皱着眉看着手机,
似乎在盘算着什么。我的目光只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林雪芬!
她竟然亲自来做这个“见证者”?或者说,她还有后招?只见林雪芬扮演的阿芬,
低着头慢吞吞地走到办公室中间,然后弯腰,开始小心翼翼地收拾地上的碎玻璃碴。
动作自然到仿佛真的只是在履行她的清洁职责。没有人防备一个扫地的哑巴。
混乱中的顾远航猛地挣脱了混混的束缚,但并没有再次朝我扑来。他喘着粗气,
布满血丝的眼睛先是狠狠剜了我一眼,然后像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
猛地扑向角落一张堆着杂物的旧办公桌!那是厂里老财务退休前用的,
放着些没人要的旧报表。“张哥!你看!你看这个!”他声音发颤,
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疯狂和扭曲的得意,手忙脚乱地从桌子最底下一个抽屉的夹缝里,
猛地抽出一本薄薄的、边缘都磨毛了的手写账簿!“这才是真的!”他因为激动,
声音都劈了叉,“这才是厂子这几年真实的老账本!那女人手上的才是伪造的!都是诬陷!
她就是想夺权!”什么?老账本?我的心猛地一沉!张麻子果然被吸引了,狐疑地看过去。
顾远航急不可耐地翻开那本破旧发黄的账簿,翻到其中一页,
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手写小字和红蓝两色的勾画:“看!你看这记录!
所有的收入支出都是合规的!哪有八百万漏洞!全是她……”他指着我的鼻子,声音扭曲,
“为了跟她那个在医院工作的旧情人合谋弄死我爸,好霸占厂子编出来的!她想把我搞进去,
好跟她情人双宿双飞!”凭空污蔑!颠倒黑白!倒打一耙!这指控如此荒谬又如此恶毒!
我气得浑身发抖:“顾远航!你血口喷人!那本子是……”“闭嘴!”顾远航厉声打断我,
把那账簿举到张麻子眼前,“张哥!你看!上面还有厂里历年收支的原始签章和日期!
这白纸黑字做不了假!就今天!我们现在就去银行验资!只要贷款下来周转开,
我立马让她滚蛋!股份全是我的,抵押绝对铁板钉钉!”他像是彻底豁出去了,
要把所有脏水一股脑泼到我头上,利用这“真账本”挽回局面!张麻子眯着眼,看着那账簿,
似乎在分辨真伪。顾远航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精光。
就在这决定成败的窒息一刻——一直蹲在地上默默捡玻璃渣的“阿芬”突然抬起了头。
“那个……”她怯怯地、小小声地开口,带着浓重的、属于保姆阿芬的川渝口音,小心翼翼,
一副“憋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插嘴”的样子。
所有人的目光下意识地被这不合时宜的怯懦声音吸引过去。
“顾老板……”林雪芬扮演的阿芬缩着肩膀,看向顾远航,
脸上混杂着困惑和一种底层人不懂规矩的“冒失”,小声嘟囔,
“您手上这个账本……今天上午……我打扫这层楼道的时候,
瞅见……瞅见你搁在隔壁那间空仓库的碎纸堆里翻出来的……后来……你让我把垃圾扔了,
我……我看这……纸壳子还挺硬实,
就……就随手垫在那个……您桌子抽屉底下……怕它晃悠有响声,
吵到您……”她的声音不大,带着一种粗鄙的不谙世事,却在死寂的办公室里砸出惊涛骇浪!
轰!我的大脑像被一道雪亮的闪电劈开!刚才那点被污蔑的恐慌瞬间消失!原来是这样!
顾远航根本不是“发现”旧账本,是他临时伪造、然后塞进那抽屉底下垫桌脚的!
他甚至吩咐过“阿芬”扔掉!而他以为一个“乡下没见识的保姆”,根本看不懂那些是什么,
也不会记着这点破事!蠢货!他以为只有自己在玩弄人心?
张麻子张大的嘴巴能塞进一个鸡蛋,看看顾远航手里那个“货真价实”的旧账本,
又看看地上散落的、印着大红公章的“假文件”,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额角青筋一根根暴凸出来,眼神变得凶狠无比!他混迹江湖多年,
立刻就把这拙劣的把戏看得清清楚楚!被耍了!还是被当着他面耍了!“顾、远、航!
”张麻子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字,声音低沉得如同即将爆炸的**桶,
“你……拿老子当猴儿耍?!还当着你婆娘面搞这套?!**你八辈祖宗!
”顾远航的表情彻底僵死,如同一尊被瞬间抽走了魂魄的泥塑木偶。
他手里那本刚刚还被视若救命稻草的“真账本”,此刻轻飘飘地如同一张烧给鬼的冥纸。
完了!什么都完了!他精心策划的“翻盘”,当着债主和我这个“敌人”的面,
被自己最看不起的哑巴保姆一句话戳得稀烂!他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眼神由呆滞迅速转为狂乱的绝望!“张哥!你听我解释!不是那样的!这蠢婆娘胡说八道!
”他像溺水的人抓向张麻子。张麻子“呸”地一口浓痰就啐在他脚边:“解释**!滚蛋!
拿一堆废纸烂账就想诓老子钱?你也不打听打听你张爷爷是干啥的!今天这笔账,
咱回头有的是法子细算!”他恶狠狠地说完,转身就朝门口走,
临走前那吃人的眼神狠狠刮过顾远航,又像看一件垃圾一样瞥了我一眼。那混混也立刻撒手,
厌恶地甩开顾远航,跟上张麻子,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走廊。办公室门敞开着,
顾远航保持着那个前扑伸手挽留的动作,像一个凝固的、极其丑陋的雕像。
整个空间只剩下他粗重如拉风箱般的喘息声,还有摔坏的眼镜碎片在灯光下散发的微弱寒光。
我站在原地,浑身冰凉还未完全退去,但胸口那股几乎要炸裂的愤怒和悲凉,
在经历了这荒谬绝伦的起落、目睹他最后的疯狂表演后,竟奇迹般地沉淀下来,
化为一滩冰冷的、彻底的决绝。张麻子临走前那句话,
已经宣告了顾远航被那些豺狼抛弃的下场。
林雪芬扮演的“阿芬”早已不知何时悄然退了出去,像个从未存在过的幽灵。够了。
这场闹剧该结束了。我慢慢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刚刚混乱时滑进去的),指纹解锁,
指尖冰冷却异常平稳地划开屏幕,
U盘里的内容……还有方才混乱中被上传的、他对我喊“找死”的录音……所有的一切材料,
在指尖快速归类整合,然后在通讯录里,直接选择了“省经侦总队举报平台”,
匿名发送键就在眼前。顾远航终于猛地回过神。刚才的狂怒和绝望像是耗尽了最后的气力,
此刻只剩下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恐慌。他僵硬地转过身,目光触及我手中屏幕的那一刹那,
瞬间明白了我在做什么!“欣欣!欣欣不要!”他声音陡然拔高,尖锐得变了调,
带着巨大的恐惧和哀求,跌跌撞撞地朝我扑过来,“别发!求你了!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想想爸!想想厂子!我进去了厂子就完了!爸怎么办!”他涕泪横流,
那张刚才还狰狞扭曲的脸此刻只剩下彻底的卑怯和摇尾乞怜的绝望,他企图用我爸来撼动我。
他的手指带着令人作呕的黏腻汗水,离我的手腕只有几厘米!屏幕右下角,
一个极不起眼的图标在闪烁——那是林雪芬留下的文件传输完成提示。
我的指尖没有半分犹豫,重重按下了那个红色的【发送】图标。
“嘀——”一声极轻微的、代表信息已发送成功的提示音响起。
顾远航伸过来的手像被无形的东西烫到,猛地僵在半空。他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了,
从哀求到震惊,再到一种无法理解的、仿佛被最亲的人背叛的茫然,
最后全都溶解在一种死灰般的绝望里。他张着嘴,像一个突然被抽空了所有气体的人偶,
无声无息地,双膝一软,整个人如同烂泥般瘫软下去,重重地跪在了冰冷湿滑的地板上。
结束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一片狼藉。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瘫软的身体和散落一地的“证据”,
心底却是一片前所未有的、冰冷的平静。刚才那滴落眼泪的地方早已干涸,留下一点涩意。
手机又震了一下。不是警报声,是一条简短的短信提示音。我划开屏幕。
没有发件人号码显示。短信只有一行字,像淬火的钢铁烙印在视网膜上:【材料齐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