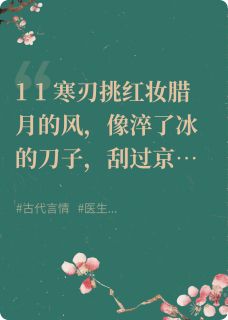
疏影轩的日子,是沉入深潭的石头,无声无息,激不起一丝涟漪。萧昀自那晚之后,如同消失。林望舒彻底成了这座华丽囚笼里的一抹影子。
春桃每日按时送来三餐,依旧是远远放在门口石阶上,敲一下门便飞快退开。饭菜说不上差,但也绝无优待,冷硬是常态。负责洒扫的老仆沉默得像一块石头,浑浊的眼睛里只有一片麻木的死寂,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单调得令人心头发慌。
唯一能透气的,是那个小小的院子。几竿翠竹在冬日里也顽强地保持着一点绿意,林望舒便每日在固定的时辰,站在廊下,看着竹影在地上缓慢移动,以此来计算时辰。午后,她坐在唯一一扇能望见一小片天空的窗边,望着高墙切割出的那一方灰白,久久出神。黄昏时分,远处隐约传来府中其他地方的模糊声响——或许是人声,或许是器物碰撞,那是属于这座庞大王府运转的动静,提醒着她外面还有一个世界,一个与她隔绝的世界。
她恪守着“安分守己”的表面功夫。只是在深夜,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她会从贴身的小荷包里,摸出几根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的银针。这是她生母留给她唯一的念想,也是幼年体弱多病时,一位云游的赤脚郎中教她的保命手艺。指尖捻动冰冷的银针,在昏暗的油灯下反复练习那几个早已烂熟于心的穴位,是她在绝望中抓住的一丝微弱慰藉,证明自己并非全然无用。
然而,这方寸之地的平静,终究被一个飘着细雪的黄昏打破。
院墙根堆积杂物的角落,传来一阵极力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声,伴随着痛苦的**。那声音微弱,像受伤的小兽,却像一根针,刺破了疏影轩死水般的寂静。
林望舒的心猛地一跳。犹豫片刻,一种医者的本能还是驱使她循着声音找了过去。在杂物和冰冷墙壁的狭窄缝隙里,蜷缩着一个小小的身影。是厨房那个叫小豆子的烧火丫头,不过八九岁年纪,此刻小脸煞白,额头上全是冷汗,嘴唇被她自己咬得发白,一只小手死死捂着右下腹的位置,身体因为剧痛而微微抽搐着。
她看到林望舒,惊恐地睁大了眼睛,身体猛地往后缩,想把自己藏进更深的阴影里,呜咽声也戛然而止,只剩下急促而痛苦的喘息。那双大眼睛里,盛满了对王府主子们本能的恐惧。
“别怕,”林望舒立刻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柔和无害,像安抚一只受惊的小兽,“小豆子?你怎么了?告诉……告诉我。”她差点脱口而出“姐姐”,但想到自己的身份,硬生生改了口。
小豆子看着她,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和痛楚,泪珠大颗大颗滚落,却倔强地摇着头,不敢说话。她认得这是王爷新娶的夫人,是高高在上的主子。
“是肚子疼吗?很疼?”林望舒放得更轻缓,目光落在她死死捂住的位置。
小丫头犹豫了很久,腹部的剧痛似乎战胜了对主子的恐惧,才极其轻微地点了一下头,小脸皱成一团,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流。
“让我看看,好吗?或许……或许我能帮你。”林望舒试探着伸出手,动作缓慢而清晰,避免任何惊吓到她。她的眼神坦然而温和,没有半分主子看下人的轻慢。
或许是那眼神里的温和起了作用,或许是她此刻的痛楚实在难以忍受,小豆子终于颤抖着,极其缓慢地松开了捂着肚子的手。她破旧的棉袄下摆被撩起一点,露出右下腹的位置。那里的皮肤绷紧,林望舒隔着衣物轻轻按压了一下,硬邦邦的,小丫头立刻痛得倒抽冷气,身体蜷缩得更紧。
肠痈!而且是缩脚肠痈!(#“缩脚肠痈”生动描绘了患者在发病时,因疼痛而蜷缩患侧下肢以减轻痛苦的典型姿势!)
林望舒心头一沉。这病发作起来凶险异常,若不及早处理……在这深宅大院,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丫头,谁会为她寻医问药?等待她的,或许就是无声无息地“病逝”,像一粒尘埃消失。
“别怕,”林望舒立刻稳住心神,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安抚力量,“我能帮你,但你要听我的,不能再乱动。”她快速解下腰间原本用作装饰的一条柔软丝绦,“把这个咬住,会有点疼,忍一忍。”
小豆子懵懂地看着她,又看看那丝绦,最终还是颤抖着张开了嘴。林望舒迅速将丝绦塞进她齿间让她咬住,随即从贴身的小荷包里,摸出了那几根随身携带的银针。细长的银针在暮色中闪过微光。
凝神静气,无视周遭的寒冷和潜在的窥视,林晚指尖捻动银针,快、准、稳地刺入小豆子腹部几处关键穴位——足三里、上巨虚、阑尾穴。手法是她反复练习过无数次,刻入骨髓的本能。
“呃……”小豆子身体猛地一僵,随即,一股浊气随着轻微的“噗”声排出,她紧绷的身体奇异地松弛下来一些,紧皱的小眉头也稍稍舒展,咬着的丝绦也松开了些。
“好了些,对吗?”林望舒轻声问,指尖继续捻动银针,引导着气机,缓解着炎症带来的痉挛。
小豆子含着泪,用力地点点头,看向林望舒的眼神里,那浓重的恐惧终于被一种难以置信的、依赖的光芒取代。疼痛真的减轻了!
林望舒守了她很久,一边捻针,一边低声和她说着话,分散她的注意力。直到暮色四合,风雪似乎更大了些,小豆子腹部的硬块明显变软,疼痛大大缓解,她才小心地起针。又撕下自己中衣干净的里衬,匆匆写了个简单的方子(蒲公英、败酱草、红藤,都是些王府药房可能有的、不易引人注目的草药),塞进她手里,压低声音叮嘱:“收好。明天想办法,找相熟又可靠的人,去药房抓这些药,三碗水煎成一碗,早晚各一次,连喝三天。记住,别让人看见这字条,抓药也要悄悄的。”
小豆子紧紧攥着那布条,像攥着救命稻草,大眼睛里泪光盈盈,用力地点头,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哭腔:“谢……谢谢夫人!”
“嘘——”林望舒竖起手指,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墙根下只有她们两人。“快回去吧,别让人看见你在这里。”她帮她整理好衣服,催促道。
小丫头挣扎着站起来,虽然还有些虚弱,但疼痛已消了大半。她一步三回头地看我,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风雪迷蒙的甬道尽头。
林望舒站在原地,看着空无一人的墙角,寒风卷着雪粒子刮在脸上,冰冷刺骨。但掌心,似乎还残留着施针时银针微弱的温热,和小丫头身体放松下来的温度。一种极其微弱的、几乎被遗忘了的感觉,在心口悄然滋生。
那感觉,叫做活着。不仅仅是被迫地、无声无息地苟延残喘,而是……似乎还能做点什么,还能触碰到一点……活着的意义。那几根小小的银针,在这冰冷的囚笼里,为她撬开了一道极其细微的缝隙。
从那天起,疏影轩这方小小的囚笼,似乎裂开了一道极其细微的缝隙。
起初,只是小豆子。她会在清晨天色未明时,偷偷将一小包还带着露水的、沾着泥土的新鲜草药放在我院门内侧的石阶下。有时是几株蒲公英,有时是几片车前草的叶子,都是些不值钱但有用的东西,是她能偷偷从王府偏僻角落寻到的“谢礼”。林望舒会在无人时悄悄收起来,洗净晾干,小心地收好。
渐渐地,风声,在这座看似密不透风的王府底层,以一种极其隐秘的方式悄然流动。
一个负责浆洗的老嬷嬷,不知从何处听闻,在一个深夜里,捂着肿得老高的半边脸,带着满身皂角味和痛楚的**,踟蹰地敲开了疏影轩的门。她得了严重的“痄腮”(腮腺炎),又不敢告假,更不敢请大夫,怕丢了这赖以糊口的差事。昏暗的油灯下,她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哀求,声音嘶哑含糊:“夫人……老婆子……实在疼得受不住了……”
林望舒没有多问,只示意她进来。借着油灯的光,林望舒看到了她红肿热痛的脸颊,皮肤绷得发亮。依旧是银针,配合着捣碎的仙人掌糊敷上去。几天后,老嬷嬷红肿消退,她再来时,手里多了一小篮子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藏了很久的干枣,放下就走,千恩万谢都堵在喉咙里,只用粗糙的手抹了抹眼角。
再后来,是一个在花园里修剪花木时不小心被毒虫蜇了手的年轻花匠,手臂肿得发亮,疼痛钻心,连工具都拿不稳。一个在前院伺候茶水、因主子暴怒而失手打碎茶盏被鞭笞了后背的小厮,伤口在闷热的夏日开始红肿溃烂,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林望舒的“病人”,身份越来越杂,病症也五花八门。无一例外,都是些王府底层挣扎求生、病痛缠身却又求医无门、不敢声张的可怜人。他们像黑暗中的蝼蚁,凭着本能嗅到一丝微弱的光亮和温暖,便悄无声息地汇聚而来。治疗都在深夜,地点或在疏影轩内,或在更隐蔽的角落。春桃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但她选择了沉默,有时甚至会帮忙望风。
疏影轩,这个原本象征着放逐与禁锢的角落,在王府森严壁垒的阴影下,竟诡异地成了一个隐秘的、散发着微弱药草清香的避风港。林晚成了他们口中,带着敬畏和感激,只敢在无人处低声念叨的“影子夫人”。
她依旧深居简出,恪守着“安分守己”的表面功夫。只是在深夜,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那盏小小的油灯下,银针的光芒不时亮起,草药的苦涩气息悄然弥漫。这方寸之地,成了她在这冰冷囚笼里,唯一能自由呼吸、证明自己并非全然无用的空间。那些带着痛楚而来、带着感激和希望而去的眼神,是支撑她继续捱下去的微光。
只是,她从未忘记这座王府真正的主宰是谁。每一次施针,每一次触碰这些伤痕累累的生命,她都会下意识地瞥一眼窗外沉沉的黑夜,警惕着任何一丝可能打破这份隐秘平静的脚步声。那柄新婚之夜悬于她颈侧的匕首寒光,始终如影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