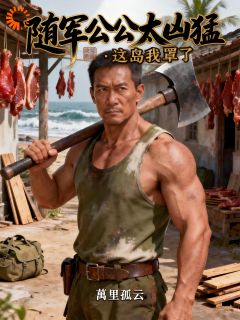
刚出火车站,一股子带着腥咸味儿的热浪就劈头盖脸地闷下来。
这哪是空气,分明是刚揭锅盖的蒸笼,黏糊糊地往毛孔里钻。
陈大炮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这汗水跟不要钱似的往下淌,把他那件扣得严严实实的旧军装浸成了深绿色。
周围的人群像是没头苍蝇,乱哄哄地挤作一团。
扛大包的“扁担”、拉板车的车夫、抱着孩子寻亲的妇女,还有那一双双贼眉鼠眼在人群里乱瞟的该溜子。
所有人的目光,在触碰到陈大炮的一瞬间,都会像触电一样缩回去,然后自觉地让出一个圆圈。
没办法,这老头太吓人了。
一米八五的大高个,杵在那儿跟座黑铁塔似的。
前后背着两个快要把帆布撑破的行军囊,手里提着两口特制的樟木大箱子,腰上别着一把板斧,手里还牵着一条只有半截尾巴、眼神凶恶的大黑狗。
这一身行头加起来,少说三百斤。
可他呢?腰杆笔直,脚底生风,大气都不带喘一口。
“大爷……坐……坐车不?”一个胆子稍大的三轮车夫凑上来,眼神直往那两个沉甸甸的箱子上瞟,喉结上下滚动。
“去码头两块钱,您这货重,得加五毛。”
陈大炮停下脚,侧过头。
老黑配合地呲了呲牙,喉咙里发出那种护食的低吼。
“两块五?”陈大炮的声音像是砂纸磨过铁锈。
“你怎么不去抢?”
在这个猪肉才一块钱一斤的年头,两块五够买两斤半大肥肉了。
车夫被那双布满血丝的虎眼一瞪,吓得退了两步,赔着笑脸:
“那……那您看着给?”
“不坐。”
陈大炮回答得干脆利落。
他不是没钱,怀里揣着两千多巨款呢。
但他陈大炮的钱,是要留给孙子买奶粉、给儿媳妇买老母鸡的,给这种坐地起价的奸商?做梦。
他紧了紧肩膀上的背带,勒得肌肉微微隆起。
不就是二十里地吗?
当年负重越野五十公里都能跑下来,这才哪到哪?
就在他准备迈开步子硬走的时候,一阵轰隆隆的引擎声传来。
那声音他太熟悉了。
这是解放CA10卡车特有的咆哮声,听着像老牛喘气,但在老兵耳朵里,那就是亲切的乡音。
陈大炮猛地抬头。
只见不远处的树荫下,停着两辆盖着绿帆布的军卡。
车旁边站着几个穿着绿军装的小年轻,正拿着花名册点名,一群剃着板寸、胸口戴着大红花的新兵蛋子正排队往车斗里爬。
送新兵去海岛的?
陈大炮那双耷拉着的眼皮猛地抬起,精光四射。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他调转方向,牵着老黑,提着箱子,径直朝那辆军卡走去。
“站住!干什么的?”
刚靠近警戒线,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就端着枪拦了上来,一脸警惕地盯着这个全副武装的“悍匪”。
主要是陈大炮这形象实在太不像好人。
这一身煞气,再加上腰间那把斧头,怎么看都像是刚打劫完下来的山大王。
“别紧张。”陈大炮停下脚步,把手里的箱子往地上一顿。
咚!
地面似乎都颤了两下,激起一片尘土。
那小战士眼皮子一跳。好家伙,这得有多重?
“找你们管事的。”陈大炮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包被汗水浸湿的大前门,动作慢条斯理。
“我是去海岛驻地探亲的军属。”
“探亲?”小战士明显不信。
“探亲带斧头?”
“这叫工具。”
陈大炮懒得解释,冲着车头那个正拿着本子扇风的军官扬了扬下巴。
“那个谁,一毛二,过来搭把手。”
一毛二,那是排长。
那军官听到有人这么豪横地喊自己,皱着眉头走过来。
是个黑脸汉子,看着精干,肩膀上的肩章在阳光下有点反光。
“老乡,这是军车,不拉客。”
排长上下打量了陈大炮一眼,语气硬邦邦的。
“探亲自己去买船票。”
陈大炮没生气,反而乐了。
这脾气,对他胃口。
他也不废话,单手解开上衣口袋的扣子,掏出一个红皮本本,递了过去。
“自己看。”
排长狐疑地接过本本,翻开第一页。
刚才还不耐烦的脸色,瞬间凝固了。
退伍军人证明书。
姓名:陈大炮。
部队代号:xxxx侦察连。
职务:炊事班班长(**侦察排长)。
立功记录:个人二等功一次,集体三等功三次。
排长猛地合上本子,啪地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老班长!”
这一声喊得中气十足,把周围的新兵蛋子都吓了一跳。
在这个年代的部队里,老兵那就是天。
更别说这种拿过二等功、干过侦察连炊事班长的狠人。
谁都知道,侦察连的炊事班,那背锅都能跑过步兵连的尖刀班,那是狠人中的狠人。
“行了,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陈大炮摆摆手,随手把那包大前门扔给排长,“蹭个车,方便不?”
“方便!太方便了!”排长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赶紧给陈大炮散烟。
“老班长您去哪个岛?要是顺路,直接给您送家属院门口!”
“南麂岛。”
“巧了!咱们这就是去南麂岛送给养和新兵的!”
排长一拍大腿,“就是这车斗里……条件差了点,还得跟新兵蛋子挤一挤,要不您坐驾驶室?”
“不用。”陈大炮拒绝得干脆。
“驾驶室太闷,我不受那个罪。后面挺好,敞亮。”
说着,他弯下腰。
周围的新兵们都在看热闹,心想这老头带这么多东西,不得找两个人抬啊?
只见陈大炮深吸一口气,气沉丹田。
右手抓住那两个捆在一起的樟木箱子——那是实打实的一百多斤重啊!
“起!”
一声低喝。
那两个笨重的箱子,就像是泡沫做的一样,被他单手硬生生提到了半空,划出一道弧线,稳稳当当地落在了近两米高的车斗边缘。
动作行云流水,连那个木箱子都没晃一下。
紧接着,他左手抓起行军囊,也是随手一甩。
砰!
行囊落在箱子上,发出一声闷响。
全场死寂。
那些刚才还在嘻嘻哈哈的新兵蛋子,一个个张大了嘴,下巴差点掉在地上。
这臂力,比他们这帮大小伙子都猛!
排长也是看得直咽唾沫,眼里全是崇拜:
“老班长,您这身手……没落下啊!”
“凑合。”陈大炮拍了拍手上的灰,一脸风轻云淡。
“就是这几年杀猪杀多了,手有点生。”
杀……杀猪?
众人看着他腰间那把斧头,再看看那条凶神恶煞的黑狗,齐刷刷打了个寒颤。
“愣着干啥?老黑,上!”
陈大炮拍了拍狗头。
老黑虽然胖了点(最近肉吃多了),但那是以前跟陈大炮上过山的狗,后腿一蹬,蹭的一下就蹿上了车斗,威风凛凛地蹲在箱子上,俯视众生。
陈大炮单手撑着车板,身体轻盈地一翻,稳稳落在车斗里。
他找了个角落,把箱子摆成个舒服的靠背,大马金刀地坐下。
从兜里掏出一根洗得干干净净的黄瓜,咔嚓咬了一口。
“开车!”
……
军车颠簸在通往码头的土路上,扬起漫天黄土。
车斗里,十几个新兵挤得像沙丁鱼,一个个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出。
所有人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瞟向角落里的那个老头。
陈大炮没理他们。
海风呼呼地灌进车斗,吹散了那股子闷热。
远处,海平线渐渐露了出来。
蓝。
真蓝。
那是和黄土高坡截然不同的颜色。
看着那片无边无际的大海,陈大炮心里那根一直紧绷着的弦,突然颤了一下。
上辈子,他就在电话里听说这海有多大,这浪有多急。
但他一次都没来过。
直到儿子那是盖着国旗的骨灰盒被送回来,他才在新闻里看到这片海。
那是吞噬了他儿子的海。
也是葬送了他全家希望的海。
“建军啊……”
陈大炮在心里默念着儿子的名字,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下那个装着腊肉和奶粉的木箱子。
这箱子硌得慌,但他心里踏实。
这里面装的不是肉,是命。
是给儿媳妇补身子的命,是让大孙子壮壮实实的命。
“大……大爷?”
旁边一个小脸晒得通红的新兵,实在忍不住好奇,壮着胆子问了一句。
“您这斧头……真是杀猪的?”
陈大炮转过头,看了看这个年纪跟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娃娃。
那一瞬间,他眼里的煞气散了,露出了一点长辈特有的慈祥——虽然配上那张严肃的脸,这慈祥看着有点像鳄鱼的微笑。
“嗯,杀猪的。”陈大炮把手里剩下的半截黄瓜递过去。
“吃不?解渴。”
新兵愣了一下,受宠若惊地接过黄瓜。
“到了岛上,别光顾着傻练。”
陈大炮看着这一车稚嫩的面孔,突然开口提点。
“海岛湿气重,晚上睡觉把被子垫厚点。要是腿疼,就去海边找那种带刺的草熬水泡脚。”
新兵们都竖起了耳朵。
“还有,”陈大炮指了指大海。
“别欺负海。浪大的时候别逞能。命是爹妈给的,不是用来喂鱼的。”
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风声和引擎的轰鸣声。
陈大炮不再说话,闭上眼养神。
再有两个小时,就能见到那混小子了。
还有那个娇滴滴的儿媳妇。
听说她是上海人?也不知道吃不吃得惯这大蒜和腊肉。
要是吃不惯……
陈大炮皱了皱眉,在心里盘算着:那就把腊肉切碎了,混在鱼丸里做成汤?或者把猪油炼出来,给她炸小酥肉?
反正老子有的是力气,有的是手段。
就算是用勺子喂,也得把她给喂胖了!
车子一个急刹。
前面传来排长的吼声:“全体都有!下车!到码头了!”
陈大炮猛地睁开眼。
一道刺眼的阳光射进来,他眯起眼,看着那个写着“军事禁区”四个大字的码头大门。
到了。
这是儿子的战场。
从今天起,也是他陈大炮的战场。
“老黑,”他拍了拍狗头,声音低沉有力。
“准备好了吗?咱们去给这岛,立立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