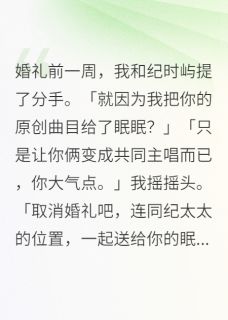
婚礼前一周,我和纪时屿提了分手。「就因为我把你的原创曲目给了眠眠?」
「只是让你俩变成共同主唱而已,你大气点。」我摇摇头。「取消婚礼吧,
连同纪太太的位置,一起送给你的眠眠妹妹。」「行,那你别后悔。」我转头就走,
没给他反应的时间。纪家的资源我捞够了。年轻的纪时屿也享受过了。
谁要在大好年纪和一个已经三十岁的男人绑定一生啊?1.我推开纪时屿办公室的玻璃门。
大步向前走去。苏以眠在身后娇声喊我:「枕月姐姐!」她小跑两步追出来。
手指拽住我的袖口:「你别生气呀,纪总他只是觉得我的声线更适合这首歌。」
「如果你真的介意,我可以换歌的。」我斜眼扫了一眼她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抬手一根一根掰开她的手指。「你喜欢,就留着吧。」「毕竟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
「当然了,我说的不是我的歌。」身后传来纪时屿不屑的轻笑:「随她闹,
不出三天就得回来求我。」我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纪时屿大概以为我会像从前一样。
在停车场崩溃大哭。或是卑微地回来认错。但我只是给经纪人许如曼打了一个电话。
2.「曼曼姐,婚礼取消了,我和纪时屿分手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因为那首歌?」
「嗯,他把我写给外婆的歌,改成了情歌,作为苏以眠的出道礼物。」
许如曼知道这首歌对我的意义。外婆临终前,我蹲在医院走廊写了这首《外婆桥》。
她长长叹了口气:「枕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明年三个综艺……」
我了然:「都黄了,我知道。」「对不起啊曼姐,连累你了。」
许如曼提高了声音:「说什么傻话呢?」「老娘带了你这么多年,
从地下Livehouse带到金曲奖,缺他纪家那几个破项目?」
但她话锋一转:「不过,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你知道京圈封杀令有多可怕。
上次得罪他们圈子沈家的那个演员,现在还在横店当群演。」
我打开车门:「最坏也不过就是回到从前嘛,大不了我再回酒吧驻唱。」
「小时候外婆就和我说过,东边不亮西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反正只要活着,只要有手有脚有脑子,我们肯定会迎来美好生活的!」后视镜里,
纪时屿公司门前的石狮子渐渐远去。我想起第一次和纪时屿去纪家。
他父亲用钢笔点着我说:「小江啊,在京城,有些台阶不是努力就能跨上去的。」现在,
我亲手把台阶拆了。3.北京的夜晚灯火通明。我沿着东三环漫无目的地开。车辆穿梭,
霓虹闪烁。写字楼里陆续有人走出来。西装革履的白领们站在路边等车,满脸疲惫。
转过下个路口,几个戴着安全帽的工人正蹲在路边吃盒饭。他们身后的豪宅,
标价是我这辈子都赚不到的数字。这座城市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我降下车窗,让夜风灌进来。
红灯前停下时,一滴水珠突然砸在方向盘上。我伸手去擦,才惊觉是自己在哭。真没出息。
我狠狠抹了把脸。却想起五年前那个雪夜。那时候我刚满二十岁,**两家酒吧的驻唱。
为了省打车钱,我经常背着吉他走三站地铁回学校,冻得耳朵通红。
那天纪时屿就坐在最角落的卡座。昏暗的灯光也难掩他与生俱来的贵气。
我在艺术学院见过太多好看的男生。但像纪时屿这样的还是头一个。他慵懒地靠在卡座里,
却莫名让人觉得难以靠近。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他点了一打啤酒,一口没喝。
就那样盯着我唱完最后一首《飞鸟》。「这歌写得**带劲。」散场后他堵在后门。
呼出的白气扑在我脸上。「我叫纪时屿,能请你吃个夜宵吗?」后来我才知道,
那晚他本该去参加某个大院千金的生日宴。但他开着那辆招摇的保时捷。
跟我去了学校后门的麻辣烫摊子。我穿着三十块钱的雪地靴。他踩着**版的马丁靴。
我们一起蹲在马路牙子上。就着北风分食一碗加了双份辣椒的麻辣烫。绿灯亮了,
后面的车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我猛踩油门,眼泪却越发汹涌。
4.其实我一直明白和纪时屿之间的差距。所以和他在一起后,我比以往更加努力。
除了两家酒吧的驻唱以外,我还接婚礼和商务宴会的演出。有时候几家婚礼和宴会撞在一天。
我就把多余的生意介绍出去,赚中间差价。五年前的直播唱歌赛道还没现在拥挤。
我直播一晚上就可以赚母亲一年的工资。纪时屿总说我太拼:「小江同学,我养不起你吗?」
我笑着摇摇头。比起沉沦在他的甜言蜜语中。母亲的教诲更让我铭记:「枕月,
这世上最靠不住的就是男人。你爸当年走的时候,连双袜子都没给我们娘俩留。」
我记得十岁的那场大雨。父亲搂着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口。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枕月,
这是你弟弟。」雨水顺着父亲的伞沿往下淌。在地上汇成一条小河。把我和他隔在两岸。
那年过年只有我和母亲两人。「枕月,记住了,男人的钱再多也是男人的,
他愿意给你是他的事,但你自己必须得有赚钱的能力。」所以就算纪时屿再宠我,
我也从没停下过工作。他送我的包我背。但一定会存够买同款的钱。
他带我去的高级餐厅我吃。第二天照样啃着面包赶场子。他给我的选秀资源我接。
拿了奖我想尽办法接商演接广告变现。我会借势。但从没想过依附。
我享受和他缠绵的每一刻。但情欲退去后,贤者时刻的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银行。
那里面的数字才是我真正的底气。没办法,在我这里的排序永远是我自己,钱,纪时屿。
纪时屿和我开玩笑说:「江枕月,你该不会把我当免费鸭王了吧?」
我趴在他胸口笑:「是啊,还是身材最好的那种。」有时候我也会恍惚。
纪时屿带着我去他小时候住的四合院。纪母悄悄把玉镯子塞给我。我差点就要相信,
门第、阶级、资源,这些在我们的爱情面前好像不值一提。但走出纪家,
看着大街上繁忙的人群。我又很快清醒。我的困境,不是谈个恋爱,结个婚就能解决的。
纪时屿的别墅、豪车、家族企业,都是纪家的。他能给我的,随时都能收回去。
就像我父亲当年能头也不回地离开。我爱纪时屿。但爱自己,胜过爱他。
5.推开京郊出租屋的门。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隙里斜斜地照进来。收拾行李时才发现,
这间五十平的小屋竟塞了这么多东西。衣柜里几套昂贵的礼服,都是纪时屿送的。
我一件件取下来,叠好放进防尘袋。三年前直播收入高峰时,我攒够了在京城的首付。
也确实动过买房的念头。但又不想太早的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城市。更不想早早背负房贷。
现金不是用来持有的。而是用来保持选择的自由。
我把钱投给了母亲的同学在杭州开的音乐培训机构。当时所有人都说北京房子永远涨。
我却把大部分积蓄换成了股份。现在想想,那可能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不然也不会有如今说走就走的勇气。钢琴上放着我早期创作的歌曲《飞鸟》的词谱。
【我宁愿做只不归巢的鸟,也不要被镀金的笼子困住一生。
】其实我本来也没想过和纪时屿结婚。6.我向来不相信靠婚姻改变阶层这些鬼话。
时常和纪时屿这个圈子里的人交往。看多了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几代人的积累,
踩着刀尖杀出来的一片天。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给你一个不相关的人?凭爱情吗?
第一次去纪家时,纪父坐在主位。斜着眼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个遍。「听说小江是唱歌的?」
「在哪个剧团?」「酒吧驻唱,偶尔也接婚庆演出。」餐桌上一片死寂。
纪时屿在桌下握住我的手,掌心都是汗。饭后纪父把我叫到书房:「时屿从小叛逆。」
「但他最后总会明白,有些游戏规则不是靠情情爱爱就能打破的。」自那天之后,
纪时屿发了疯似的说背叛全世界也要娶我回家。他故意带着我去三亚过年。
家里打来几十个电话都不接。他把纪父介绍的相亲对象,大院领导的千金,
晾在餐厅四个小时。为了躲避家里安排的联姻,他连续几周睡在我的出租屋。「江枕月,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娶你吗?」落地窗外是凌晨三点的北京。「我不想过我爸那种人生,
也讨厌成为我爸那样的人。」「娶个门当户对但没感情的老婆,自己在外面莺莺燕燕。」
纪母出了名的贤惠大度。能微笑着和小三同桌吃饭。纪父带着新欢出席,
她可以优雅地夸那姑娘的穿搭好看。这种阶级的**和人母。
向来是世俗鼓吹的女性幸福的终极模板。但实际上,
她们却过着牢狱一般饱受禁锢与束缚的生活。而我只想忠诚于自己的欲望。无拘无束活着。
可纪时屿把头埋在我颈窝:「江枕月,给我个家吧。」「不是纪家那种,
是只有我们俩人的家。」我承认有那么一刻的心软和感动。我伸手盖住他的眼睛,
感受着掌心渐渐湿润。「好。」又一次因为纪时屿,打破了自己的原则。说来也可笑。
后来让纪父松口的不是纪时屿的坚持。而是江明杰的新老婆和新儿子出车祸死了。
他开始联系我这个女儿。我莫名其妙成了京圈独生女。7.虽然比不上纪家。
但江家在京城也算有头有脸。纪时屿也是在这时候变的。他不再睡在我狭小的出租屋里。
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酒会上。身边总是带着不同的漂亮女孩。
散场后随手在奢侈品店买个包带给我:「逢场作戏而已,你才是我要娶回家的人。」
他的喜好倒是一直没变。喜欢没有背景,但长得漂亮的小网红,小明星。
尽情享受着她们的追捧和崇拜。我冷眼看着他砸钱捧苏以眠出道。
然后开始要求我像纪母那样识大体。「你怎么不跟那些太太们聊天?
我妈这个年纪都已经能帮我爸打理半个公司了。」
纪时屿反抗的从来不是他的家庭和他所处的阶层。他只是想换个方式享受特权。
我答应结婚本身也不是图什么纪太太的身份。至于圈子里的资源,有就尽情享受。
没有我也赚差不多了。只是当初心疼他眼里的泪光。可现实告诉我,心疼男人是倒霉的开始。
纪时屿变成了他讨厌的人。也变成了我讨厌的人。打包好最后一个行李箱。
我收到了纪时屿好友秦易成的消息。【嫂子,别闹了行吗?都要结婚了。】【屿哥就是玩玩,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圈子就这样。】【你看看外面多少人盯着纪家少奶奶的位置。
】我回了他一句【神经病】。【新中国成立多少年了你们还搁这儿玩三妻四妾这一套呢?
野人没开化吗?恶不恶心啊?】杭州的合伙人给我发来了新工作室的图片。西湖边,玻璃屋,
灯火透亮。我回了一句【明天见】。登机口的玻璃映着北京最后的夜色。
这座城市给过我梦想,也给过我幻灭。从酒吧驻唱到万人演唱会。
从直播间只有几百人到站在大舞台的中央。纪时屿参与了我人生的每一个高光时刻。登机前,
我还是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候机大厅空空荡荡。嗯,这样最好。
爱情从来不是我人生的必需品。再见,北京。再见,纪时屿。我把手机关了机。
连同纪时屿新发来的消息。一起消失。8.飞机降落在杭州萧山机场。天刚蒙蒙亮。
手机上跳出一连串消息。最早的是凌晨四点。【明天再去试一次婚纱?
设计师说最后改了一次腰线。】然后是六点:【你把我那件灰色西装放哪了?
】最新的一条是十分钟前:【接电话!】我慢悠悠地打了辆车,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直接设置了勿扰模式。车窗外,杭州的清晨像一幅水墨画,西湖上还笼着薄雾。
司机热情地介绍着沿途风景。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杭州的天气比北京湿润多了。
连风都是温柔的。我的合伙人周阿姨站在门口冲我挥手。我深吸一口气,
拎着行李走向新生活。杭州这边的生意一直不错。来培训学习的网红络绎不绝。
附近国际幼儿园和国际小学的孩子,占据了一半生源。还有从周边城市慕名而来的。
周阿姨说我可以躺着数钱了。但我停不下来。趁着刚分手的伤心情绪还很饱满。
我把自己关进房间,与世隔绝。连写了三首歌曲。一写起来就忘情了,发疯了。
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窥探自己。一次又一次重塑自我。一次又一次泪流满面。
哭累了就沉沉睡去。睁眼继续创作。饿了就喝两口水。再次走出房间时已经是三天后的傍晚。
杭州的夜晚一样灯火通明。但这座城市和北京不同。在北京,
入夜后的长安街总带着某种肃穆的威压。经过二环内某些大院门口,
连路灯都像是刻意调暗了几度。而杭州的夜是流动的,鲜活的。南山路热闹非凡。
年轻人三三两两聚在露天座位。说着天南地北的方言。西湖边的长椅上,
有抱着吉他唱歌的大学生。也有拿着电脑加班到深夜的程序员。这座城市不关心你的出身。
只在乎你能否抓住下一个风口。我懒得化妆,也不在意会不会被粉丝认出来。
我把及腰卷发扎成土气低马尾。戴着遮住半张脸的框架眼镜。独自去了钱塘江边的一家清吧。
不远处的卡座里,几个年轻男孩正在玩骰子。其中一个穿黑色衬衫的帅的格外醒目。
侧脸在灯光下棱角分明。我举起酒杯冲他示意。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灿烂的笑容。
五分钟后,他端着酒杯坐到了我旁边。9.没意思。勾勾手指头就来了。除了帅一无是处。
「杭州人?」他问。我晃着酒杯。「新杭州人,北京来的。」「巧了,我上海来的。」
「做互联网的,刚融资成功。」我们聊得很投机。他给我讲创业的艰辛,
我给他讲音乐圈的趣事。两杯酒下肚,他的手自然地搭在了我的椅背上。
「要不要去江边走走?」他凑近我耳边问。我笑着答应。却在起身时巧妙地避开了他的手。
「好啊,不过你的酒我请了,不喜欢占男人便宜。」江边的风带着湿润的水汽。男孩叫陈敬。
试图牵我的手,我假装撩头发躲开了。他突然说:「你很像我的初恋。」
我忍不住笑出声:「这招太老套了吧?」「是真的,她也是搞艺术的,后来去了纽约。」
我望着江对岸的灯光,感觉索然无味。陈敬很好。年轻有为,长相出众。
但这些根本吸引不到我。因为我都有。「加个微信?」他晃了晃手机。我拒绝了。
这些年轻男孩就像餐前开胃酒,浅尝辄止才有意思。真要论起段位,
他们不及纪时屿的十分之一。不过纪时屿也老了,没什么意思。但有什么关系呢?
杭州的夜还长。我有的是时间慢慢品尝。10和陈敬分别后。我回到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