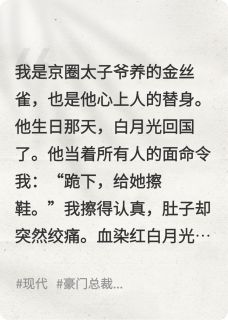
我是京圈太子爷养的金丝雀,也是他心上人的替身。他生日那天,白月光回国了。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命令我:“跪下,给她擦鞋。”我擦得认真,肚子却突然绞痛。
血染红白月光的钻石高跟鞋时,他正笑着吻她。后来我远走他乡,他疯了一样找我。
拍卖会上重逢,我戴着价值连城的古董戒指举牌:“三亿,买周家破产。”而他的白月光,
正跪着给我擦鞋。---浓得化不开的夜,沉甸甸压在“云顶”会所巨大的水晶吊灯上。
空气里浮动着昂贵的酒气、雪茄的辛辣,还有一丝丝被空调冷气压下去,
却依然顽强透出来的、属于金钱与权力的躁动。我端着沉重的托盘,
上面几只水晶杯里琥珀色的液体微微晃荡,折射着迷离的光。腰很酸,
廉价制服粗糙的布料摩擦着皮肤,提醒着我与这纸醉金迷格格不入的身份。一个趔趄,
托盘猛地一倾。冰凉的液体泼溅而出,
几滴正好落在旁边卡座伸出的那只锃亮的手工皮鞋尖上。“嘶——”一声夸张的抽气。
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卡座里那张英俊得近乎刻薄的脸抬了起来。周聿怀,
京圈里人人捧着供着的太子爷。他靠在那儿,像一头慵懒的豹子,眼神却冷得淬冰。
他旁边依偎着的几个男女,立刻噤声,看好戏似的目光齐刷刷射向我。“没长眼睛?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冰锥,轻易刺穿喧嚣的背景音。心脏在肋骨后面疯狂擂鼓。
我死死咬住下唇内侧的软肉,尝到一丝铁锈味,才勉强压下喉咙口的颤抖。弯下腰,
本能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洗得发白、边缘都磨毛了的旧手帕——那是弟弟小宇在医院用过的,
上面还残留着消毒水的味道。“对不起,周少。”我的声音低得像蚊蚋。
就在我的手快要触碰到那沾了酒渍的鞋尖时,一股巨大的力道猛地攥住了我的手腕!
骨头被捏得生疼,我被迫抬起头,撞进周聿怀深不见底的眸子里。那里面没有怒火,
只有一种……令人心寒的审视,像是在挑剔一件物品的瑕疵。“苏晚,”他薄唇轻启,
每个字都淬着冰渣,“你身上这股子穷酸气,熏得我头疼。
”他另一只手慢条斯理地拿起桌上半杯残酒,手腕优雅地一翻。哗啦!冰凉的液体兜头浇下,
顺着额发、脸颊狼狈地往下淌,浸透了劣质制服的领口,狼狈又冰冷。
周围的嗤笑声像细密的针,扎遍全身。“擦干净。”他松开手,
随意地指了指地上那一小滩酒渍和他依旧锃亮的鞋面,仿佛刚才泼酒的不是他。然后,
他懒洋洋地靠回沙发,目光掠过我的头顶,投向门口的方向,那冰封般的眼底深处,
倏然裂开一丝难以察觉的亮光。我僵硬地蹲下去,那块洗得发白的旧手帕紧紧攥在手里,
指关节绷得发白。粗糙的布料用力擦拭着冰凉光滑的地砖,也擦着那沾了酒液的鞋尖。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不知道是屈辱还是别的什么,
一股尖锐的绞痛毫无预兆地从下腹猛地窜起,瞬间攫住了所有神经。
“唔……”一声压抑的痛哼从齿缝里溢出。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阵骚动。
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清脆悦耳,节奏分明,带着天生的优越感。整个喧闹的卡座区,
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我下意识地抬起头。光影交错处,林薇站在那里。
一身当季高定的米白色裙装,勾勒出完美的曲线,海藻般的卷发慵懒地披在肩头,
笑容明媚张扬,像一朵精心培育、在聚光灯下盛放的温室玫瑰。她的目光扫过全场,
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惊讶和久别重逢的欣喜,最终,精准无误地落在了周聿怀身上。
周聿怀脸上的冰霜瞬间消融殆尽,嘴角扬起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近乎温柔的弧度。
他推开身边的人,径直起身,大步朝门口迎去。他张开手臂,林薇像一只归巢的蝴蝶,
轻盈地扑入他怀中。“薇薇。”周聿怀的声音低沉温柔,带着失而复得的珍视,
清晰地穿透寂静的空气,钻进我的耳朵里。“聿怀哥!”林薇的声音娇甜得能滴出蜜来,
“我回来啦!想死你了!”他们旁若无人地拥抱,林薇纤细的手臂环着他的脖颈,
整个人几乎挂在他身上。周聿怀的手稳稳地托着她的腰,低头,额头亲昵地抵着她的。
整个世界的喧嚣都远去了。只剩下腹中那不断加剧的、撕裂般的绞痛,
还有眼前那刺眼的一幕。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捏得血肉模糊,
每一次跳动都牵扯着四肢百骸,带来麻木的钝痛。眼前阵阵发黑,
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廉价的制服布料。“薇薇,累不累?嗯?
”周聿怀的声音是化不开的蜜糖,他旁若无人地替林薇理了理耳畔一丝不存在的乱发,
动作轻柔得像对待稀世珍宝。“还好啦,就是想快点见到你嘛!”林薇娇笑着,眼波流转,
像含着一汪春水。她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蹲在地上的我,
那双漂亮的眼睛里瞬间掠过一丝毫不掩饰的鄙夷,如同看一粒碍眼的尘埃,随即又快速移开,
仿佛多看一眼都会脏了她的眼。周聿怀揽着她的腰,像拥着最珍贵的战利品,
转身朝卡座最中心的位置走去。经过我身边时,林薇那双镶满碎钻的银色高跟鞋尖,
几乎要踢到我的膝盖。周聿怀的脚步顿了一下。他没有看我,
目光依旧胶着在林薇明艳的脸上,仿佛在欣赏一幅绝世名画。薄唇轻启,
吐出的话语却像淬了剧毒的冰凌,精准地刺向我:“苏晚,还愣着干什么?”他的声音不高,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清晰地回荡在骤然安静下来的空气里,“薇薇的鞋脏了。跪下,
给她擦干净。”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炸开。周遭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
只剩下尖锐的耳鸣。卡座里那些看好戏的目光,此刻更是肆无忌惮地黏在我身上,
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和残忍的兴奋。林薇微微扬着下巴,
嘴角噙着一抹胜利者般矜持又得意的浅笑。腹中的绞痛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像有无数把烧红的刀子在里面疯狂搅动。冷汗顺着额角滑落,滴进眼睛里,一片模糊的刺痛。
我死死咬住下唇,血腥味瞬间弥漫口腔。不能倒在这里。为了小宇的医药费……求生的本能,
或者说是对那笔悬在弟弟生命线上的钱的恐惧,压倒了所有屈辱。膝盖像是灌了沉重的铅,
又像是被无形的丝线操控着,一点点、极其缓慢地弯曲下去。粗糙的地砖冰冷坚硬,
硌着膝盖骨,寒意瞬间穿透薄薄的裤子。我伸出手,指尖控制不住地颤抖,几乎是痉挛着,
再次摸向口袋里那块洗得发白、边缘磨损的旧手帕。布料粗糙的质感磨着指腹。
我艰难地、一点一点地抬起头,视线越过林薇那光洁纤细的脚踝,向上看去。
周聿怀正微微倾身,专注地听林薇说着什么。他英俊的侧脸线条柔和,
唇角带着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宠溺的笑意。林薇则踮起脚尖,凑到他耳边,红唇轻启,
不知说了句什么。周聿怀低低地笑了起来,那笑声低沉悦耳,带着全然的放松和愉悦。然后,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在迷离的光影中,在林薇含羞带怯的目光里,周聿怀微微侧过头,
无比自然地、无比珍重地,吻上了她的唇。像慢放的电影镜头。
那是一个轻柔的、充满占有欲和宣告意味的吻。周聿怀的手掌托着林薇的后颈,
动作带着不容置喙的强势,却又蕴含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温柔。林薇闭着眼,
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脸颊泛起动人的红晕,仿佛沉浸在最甜美的梦境里。
时间,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就在他们唇瓣相触的瞬间,一股温热的、无法控制的暖流,
猛地从我身体最深处汹涌而出。伴随着一阵天旋地转的剧烈眩晕和撕心裂肺的剧痛。
“呃……”一声破碎的**从喉咙深处逸出,再也压制不住。我眼前彻底一黑,
整个人像被抽掉了所有骨头,软软地向前栽倒。意识消失前的最后一秒,
视野里只有一片刺目的猩红——那粘稠的、温热的血,正汩汩地从我身下蔓延开来,
像一条绝望的暗河,
无情地浸染了林薇脚上那双价值不菲的、闪烁着冰冷光芒的钻石高跟鞋鞋尖。
那片刺目的猩红,成了我坠入黑暗深渊前,唯一烙刻在视网膜上的印记。消毒水的气味,
浓烈得呛人。意识像是沉在冰冷浑浊的水底,每一次试图上浮,
都被沉重的疲惫和无边的钝痛狠狠拖拽回去。眼皮有千斤重,我艰难地掀开一条缝隙。
惨白的天花板,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鸣。“醒了?”冰冷的声音,毫无起伏,
像手术刀刮过金属。我猛地一颤,涣散的视线艰难聚焦。周聿怀站在床边,
高大的身影逆着窗外的天光,投下一片压迫感十足的阴影。他穿着挺括的黑色大衣,
领口一丝不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眼底深处,
残留着一丝尚未褪尽的、属于另一个女人的温柔余烬,此刻却像冰层下的火焰,灼得人发慌。
“孩……”干裂的嘴唇翕动,喉咙里火烧火燎,挤出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没了。
”他打断我,声音干脆利落,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在陈述一件无关紧要的旧物处理结果。
他甚至没有看我,目光落在自己修长干净的手指上,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心口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掏空,只剩下一个灌满寒风的巨大窟窿。痛到极致,
反而麻木了。我闭上眼,浓密的睫毛剧烈地颤抖着。“聿怀哥,医生怎么说?
”病房门被推开,林薇走了进来。她换了一身香奈儿的软呢套装,妆容精致,
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果篮,像个探视好友的优雅名媛。她快步走到周聿怀身边,
自然而然地挽住他的手臂,关切的目光落在我苍白的脸上,
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冰冷的快意。“死不了。
”周聿怀的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他终于把目光转向我,那眼神锐利如刀,
带着审视货物般的冷漠。“苏晚,你倒是挺会挑时候。”他微微俯身,
一股清冽的雪松气息混合着林薇身上甜腻的香水味扑面而来。一张薄薄的支票,
被他两根手指夹着,随意地丢在我盖着白色被单的腿上。纸片轻飘飘的,却像烧红的烙铁,
烫得我皮肤生疼。“五十万。”他盯着我,眼神里没有任何愧疚或怜惜,
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和急于摆脱麻烦的厌烦,“够你弟弟再撑一阵了。拿着钱,
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更别出现在薇薇面前碍眼。”他顿了顿,唇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你该清楚,你存在的意义,从来都只是因为她不在。”每一个字,都像淬毒的针,
狠狠扎进我早已血肉模糊的心脏深处。支票冰冷的纸张边缘硌着腿,那上面的数字,
像是对我过去所有隐忍、付出和那个无声消逝的小生命最冷酷的嘲讽。
林薇依偎在周聿怀身边,微微蹙着眉,
用一种带着怜悯实则高高在上的语气轻声劝道:“聿怀哥,别这样,
她刚失去孩子……也挺可怜的。”她说着“可怜”,目光却轻飘飘地扫过我,
像在看一只路边垂死的流浪猫狗。周聿怀没再说话,只是伸手,
极其自然又充满占有欲地揽住了林薇的腰,转身就朝病房门口走去。那背影,挺拔、决绝,
带着新欢在怀的春风得意,没有一丝留恋。病房门轻轻合上,隔绝了外面的一切。死寂。
冰冷的空气沉重地挤压着肺部。我僵硬地转过头,目光落在窗外。铅灰色的天空,
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一只孤零零的麻雀扑棱着翅膀,撞在冰冷的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然后歪歪扭扭地飞走了。视线缓缓移回腿上那张支票。五十万。
弟弟小宇在无菌舱里挣扎求生的脸,和那滩刺目的、属于我孩子的鲜血,
在眼前疯狂交织、重叠。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够了。真的……够了。
我用尽全身残存的所有力气,抬起那只没有输液的手。指尖触碰到冰冷的支票边缘,然后,
猛地攥紧!刺啦——一声清脆的裂帛声响彻死寂的病房。薄薄的纸张在我指间被撕成两半,
然后是四半、八半……直到变成一堆再也无法拼凑的、细碎的纸屑。白色的碎屑,
如同祭奠的纸钱,纷纷扬扬,从颤抖的指间滑落,飘散在惨白的病床和冰冷的地面上。窗外,
那只麻雀早已消失不见。铅灰色的云层翻滚着,酝酿着一场未知的风暴。三年后。伦敦,
苏富比拍卖行。空气里弥漫着陈年羊皮纸、昂贵雪茄和顶级香水混合的独特气味,
一种沉淀着巨大财富与隐秘欲望的味道。水晶吊灯的光芒璀璨却不刺眼,
柔和地洒在深红色的天鹅绒座椅和那些衣着考究、面容矜持的竞拍者身上。
我坐在二楼视野绝佳的VIP包厢里,透过单向玻璃,俯瞰着下方人头攒动的大厅。
身上一袭剪裁完美的霁青色旗袍,丝滑的料子上用银线绣着若隐若现的缠枝莲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