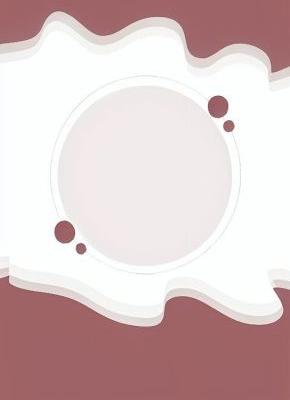
夜已极深,城市的灯火像一封被揉皱又摊开的信,闪着微茫的光。林砚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把最后一页稿纸撕碎。那是他第十一次被出版社退稿的长篇——《北溟有雁》。
"林老师,我们欣赏您的历史功底,可市场需要‘爽点’。"编辑的语音还在耳边回荡。
他抬头,看见一颗流星划破霾色天空,拖着长长的尾。那一瞬,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的话:"砚儿,若有一日你撑不下去,就去老宅的东厢,把祖传的‘归鸿匣’打开。"
林砚苦笑。父亲故去七年,他一次也没回去过。
流星熄灭的刹那,城市的灯同时黑了。整栋楼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按进深海。
黑暗里,只有那只小小的归鸿匣在书桌上发出幽蓝的光。
林砚抱着匣子,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下到东厢。门楣上积着一寸厚的灰,铜锁却自己咔哒一声开了。
匣子里躺着一张泛黄的雁皮纸,还有一枚黑铁钥匙。纸上是父亲的笔迹:
——"欲归鸿,先入梦;欲入梦,先忘川。"
黑铁钥匙插入空气,竟像插入了一扇看不见的门。
门开处,风雪扑面而来。
他下意识闭了眼,却仍能感到雪粒像细碎的针扎进皮肤,带着一种久违的、近乎疼痛的清醒。耳畔风声猎猎,如千万只白鸟振翅掠过,又似有人在远处低低呼唤他的名字,声音被风撕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一截尾音,像断弦的琴音,颤颤地滑进耳廓里。林砚喉头发紧,指节因过度用力而发白,匣子几乎要从怀里滑落。他想起父亲最后一次离家,也是这般大雪,背影被风刮得歪斜,像一株被岁月压弯的竹,却始终没有回头。如今,那背影与眼前翻涌的雪幕重叠,竟分不清是记忆还是幻境。
再睁眼时,木梯、东厢、灰尘尽数隐去,脚下是一条狭长的冰桥,桥身以整块墨玉雕成,纹理里渗着细碎的银光,仿佛有人把碎星撒进了石头的血脉。桥下却无深渊,只有一片静止的雪原,雪色白得发蓝,像被月光浸泡了千年,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林砚试着呼吸,寒气顺着鼻腔一路割进肺里,却意外地干净,像是把积年的尘垢都洗刷一空。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并不觉得冷——或者说,冷意穿透了皮肤,却触不到血液,仿佛这副躯壳在此地只是借来的容器,真正被冻住的,是胸腔里那颗迟迟不肯跳动的心。
匣子在怀中微微发热,像一块被体温捂暖的炭。林砚低头,看见雁皮纸上的字迹竟在雪光中浮动,墨迹化作细小的黑蝶,振翅欲飞。他伸手去捉,蝶群却倏地散开,重新聚成一行新的字:
——"雪深处,有旧宅,宅中无灯,灯在心。"
字迹浮现的刹那,冰桥尽头亮起一点微芒,昏黄如豆,却在漫天雪色里倔强地亮着,像是谁隔着岁月,把最后一盏未熄的灯留给了他。林砚迈出第一步,靴底与冰桥相触,竟发出清脆的玉磬声,一声接一声,在空旷的雪原上荡出层层涟漪。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背《诗经》,读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时,父亲忽然停下来,指着窗外初雪说:"你记住,雪不是冷的,是烫的。烫得能把人骨头里的旧疤都燎出来。"那时他不懂,此刻脚下每走一步,膝盖处便隐隐作痛——那里有一道旧疤,十二岁那年爬树摔断腿留下的。如今疤口被雪光撕开,疼得钻心,却奇异地让他确认,自己仍活着,仍行走在某条真实与虚幻的缝隙之间。
风忽然转了向,雪粒斜斜地拍在脸上,像细小的耳光。林砚抬手去挡,却透过指缝看见那盏灯近了。灯下是一座宅院,门楣低矮,瓦当残缺,雪堆在檐角,像给破旧的屋檐缝了一圈银边。门是虚掩的,缝隙里漏出一线暖光,在雪地上切出一道窄窄的口子,仿佛有人用指甲在冰面上划了一道,露出底下深埋的血色。林砚站在门前,忽然怯了。匣子在此刻重若千钧,压得肋骨发疼。他想起父亲离家前夜,母亲把同样的匣子交给他,说:"等你敢打开它,再去找你爸。"那时他十五岁,把匣子塞进床底,锁了七年。如今锁开了,他却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来寻父,还是来寻一个迟来的答案。
门轴发出一声长叹,像是老人在喉咙里滚动的痰音。院内积雪盈尺,唯有一株老梅,枝桠横斜,花瓣却红得刺目,像是谁把伤口倒扣在枝头。梅树下摆着一张石桌,桌上摊着未完的棋局,黑子白子交错,竟是一副死局。林砚走近,发现黑子全是父亲的笔迹,白子则是母亲生前抄的诗句,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被雪水晕开,墨迹蜿蜒如泪痕。他伸手去触,棋子却在他指尖下碎成齑粉,雪一般簌簌落下,在石桌上积成两小堆,黑与白,泾渭分明。匣子在此刻剧烈震动,几乎要挣脱他的怀抱。林砚慌忙按住,却听见父亲的声音从梅树深处传来,沙哑得像被雪水泡过的旧纸:
"砚儿,你来了。"
他猛地转身,梅枝间空无一人,唯有风过处,花瓣纷纷扬扬,像一场迟到的红雪。声音却继续响着,这次更近,几乎贴在他耳后:"雪是烫的,你记得吗?烫得能把谎话都烧成灰。"林砚的指尖开始发抖,匣子锁扣"嗒"地弹开,雁皮纸与钥匙浮空而起,纸面化作漫天黑蝶,钥匙则化作一道乌光,直刺入梅树树干。树皮裂开一道缝,缝里透出幽蓝的光,像是一口被冰封的井。林砚听见井底传来水声,咕咚,咕咚,像是谁在吞咽着无法言说的秘密。
他跪下来,把脸贴向裂缝。井水映出他的倒影,却是一张少年的脸——十二岁的林砚,膝盖上还带着新鲜的血痂。少年在井里对他笑,笑得牙齿雪白,眼瞳却黑洞洞的,像两口枯井。少年张口,声音却仍是父亲的:"你恨我吗?恨我丢下你和这盘死棋?"林砚的喉咙里涌上一股铁锈味,他想说"不",却吐不出一个字。少年继续笑,笑着笑着,眼里忽然涌出泪来,泪珠滚落井中,竟化作一枚枚黑子,叮叮当当沉了底。井水随之上涨,幽蓝的光漫过裂缝,漫过林砚的指尖,冰凉得像是父亲离家那夜,母亲握住他手腕的温度。
雪忽然停了。风也止了。整个世界安静得能听见心跳。林砚抬头,看见梅树下的石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扇半开的窗。窗内灯火摇曳,映出父亲佝偻的背影。他正伏案写着什么,笔尖在纸上沙沙游走,像是要把一生的悔悔都写进那张薄薄的纸里。林砚想喊,却发现自己的声音被冻在了喉咙里。他只好一步一步走过去,每一步都在雪地上留下一个深坑,坑底渗出暗红的水,像是从地心涌出的血。窗内的父亲忽然停笔,转过头来——那张脸竟与井中的少年重合,皱纹里藏着十二岁的泪痕,眼瞳却深不见底。
父亲对他伸出手,掌心向上,纹路里嵌着细小的雪粒。"砚儿,"他说,"棋局我解不开,钥匙你拿走吧。"林砚低头,看见那枚黑铁钥匙静静躺在父亲掌心,却比记忆中更黑,像是吸尽了所有光。他伸手去接,指尖相触的刹那,钥匙忽然化作一滴墨,渗入父亲掌纹,又顺着血脉蜿蜒而上,爬上父亲眼角,化作一颗将坠未坠的泪。父亲笑了,笑得像是要把整张脸撕裂:"去吧,去把雪烧起来。"
话音未落,窗内的灯火倏地熄灭。黑暗如潮水涌来,淹没了梅树、石桌、老宅,甚至淹没了林砚自己。他抱紧空空的匣子,在黑暗中下坠,下坠,直到听见一声熟悉的"咔哒"——铜锁重新合上的声音。黑暗散去,他发现自己仍站在东厢门前,灰尘簌簌落在肩头,像一场迟到的雪。匣子在怀里,锁扣紧合,仿佛从未打开过。唯有雁皮纸上的字变了:
——"雪已燃,归鸿将至。"
林砚抬手,摸到脸上冰凉的泪。膝盖上的旧疤隐隐发烫,像是被雪烫伤的印记。他忽然明白,父亲留下的从来不是谜底,而是一把钥匙——能打开自己心门的钥匙。雪原、老宅、梅树、死局,不过是那把钥匙转动的声响。真正的归鸿,是他自己。
东厢外,雪无声落下,覆盖了所有脚印,像是从未有人来过。唯有匣子深处,传来一声极轻的"咚",像是有什么东西,终于落回了原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