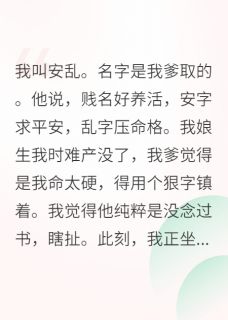
我叫安乱。名字是我爹取的。他说,贱名好养活,安字求平安,乱字压命格。
我娘生我时难产没了,我爹觉得是我命太硬,得用个狠字镇着。我觉得他纯粹是没念过书,
瞎扯。此刻,
我正坐在这个四面漏风、头顶见光、桌椅腿没几条全乎的“清风书院”里唯一的完整板凳上,
冷眼看着院子里那棵半死不活的老槐树。树叶子稀稀拉拉,跟我兜里的铜板一样。三天前,
我还是个在互联网大厂卷生卷死、为KPI熬秃了头的社畜安总监。一觉醒来,
就成了这个也叫安乱的、爹刚病逝、除了一**债和这座破败书院啥也没留下的古代小可怜。
原主的记忆像劣质幻灯片,断断续续。只记得她爹安秀才,考了一辈子举人没考上,
心灰意冷开了这间书院,收点束脩糊口,结果糊着糊着,把自己糊没了。
债主们闻着味儿就来了。“安小娘子,你爹欠我那二两银子的药钱,
你看……”街口卖棺材的老王头,搓着手,眼神在我身上和这破院子间来回扫,
大概在估量我值不值二两银子。“王伯,您看这书院,”我抬手指了指头顶的窟窿,
“值钱不?要不您搬走抵债?”老王头噎住,看着那几根朽木椽子,
脸皱得像他卖的劣质棺材板。“还有我这儿!安秀才去年借的一石糙米!
”粮铺的赵婶嗓门洪亮。“赵婶,米吃进肚子早化成那啥了,”我一脸诚恳,
“要不您把我爹坟刨开,看看还能不能捡回点谷壳?”赵婶被我噎得直翻白眼。最后,
**着这张在甲方爸爸面前千锤百炼过的嘴皮子,和“书院好歹是个产业,
逼死我你们一分捞不着”的流氓逻辑,暂时稳住了这群债主。条件是:三个月内,
连本带利还清所有债务。否则,这书院归他们拆了卖木头,
我……估计得去抵给老王头当棺材铺的招牌。压力山大。
我围着这个所谓的“书院”转了三圈。就三间半塌的土坯房,一个比狗啃过还乱的院子。
学生?一个没有。名声?大概比老王头的棺材还晦气。唯一的资产,
是原主爹留下的一屋子发了霉的经史子集,还有半块磨秃了的砚台。开局一把烂牌,
还是沾了屎的那种。但我安乱,最擅长的就是把烂牌打出花来。第一步,得有个招牌。
我翻出家里最后半块黑炭,在门口那块摇摇欲坠的木牌子上,
唰唰写下几个大字:【包教包会!包你认字算账不被坑!学不会?倒贴钱!
】落款:清风书院·安先生。字歪歪扭扭,胜在够大,够直白。这年头,
能供孩子正经念书考科举的都是殷实人家,谁看得上这破落户开的野鸡书院?我的目标客户,
是那些挣扎在温饱线上,又不想让孩子一辈子当睁眼瞎的平头百姓。认字,会算数,
知道点律法常识,进城卖菜不被坑,看个契约不吃亏——这才是他们的刚需!
招牌挂出去第一天,门口聚了一堆看热闹的街坊。“安小娘子,你这……包教包会?
真的假的?”卖豆腐的刘大娘一脸怀疑。“童叟无欺!”我拍着胸脯,“学不会,
我倒贴您十个大钱!”“那……束脩多少?”旁边挑担卖柴的李叔问到了关键。
我伸出两根手指。“二两银子?抢钱啊!”人群炸了锅。“想什么呢!”我吼了一嗓子,
压住嘈杂,“二十个铜板!一个月!管一顿晌午饭!”死寂。二十个铜板,
也就够买几斤糙米,还管一顿饭?“安小娘子,你……没疯吧?”刘大娘小心翼翼地问。
“疯没疯,试试不就知道了?”我咧嘴一笑,“前三天,免费!分文不取!学得不好,
您扭头就走,绝不拦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穷病之下,必有贪小便宜的。当天下午,
我的“清风书院”迎来了第一批“学生”。五个。最大的十四岁,叫温烈,
是西街铁匠温老黑的儿子,长得跟小牛犊子似的,一脸倔强,是被他爹拿烧火棍撵来的,
让他来学认字,免得将来给人打铁连契约都看不懂,被人坑死。最小的才七岁,
是刘大娘的孙子,叫豆子,挂着两筒清鼻涕,纯粹是听说管饭才来的。另外三个,
也都是街坊邻居家半大不小的皮猴子。
看着这五个高矮不齐、眼神里充满怀疑和好奇的小萝卜头,我深吸一口气。很好,创业团队,
齐活儿。教学第一步,不是之乎者也。我搬了块还算平整的石头当讲台,手里捏着根树枝。
“今天,教你们第一个字!”我用树枝在泥地上划拉,“看好了!
”一个大大的、歪歪扭扭的“钱”字。孩子们:“???”“钱!就是铜板!就是银子!
就是能买米买肉买新衣裳的好东西!”我声音洪亮,“认不认识?
”豆子吸溜着鼻涕:“安先生,我认识铜板!”“很好!”我点头,
“那你们想不想以后认识更多的‘钱’?想不想自己也能挣到‘钱’?
”小牛犊子温烈哼了一声,但眼睛盯着那个“钱”字没挪开。“第二个字!
”我又写了个“契”。“这个字念‘契’!契约!就是摁手印的纸!看不懂这个,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我用树枝点着地上的字:“钱!契!记住了吗?今天回去,
把这两个字,写十遍!写会了,明天有肉吃!”肉?!五个小脑袋瞬间抬起来,眼睛放光。
“真…真有肉?”温烈怀疑地问。“安先生说话算话!”我拍板。认字,
从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开始。兴趣和食欲,是最好的老师。第二天,五个孩子,一个不少,
全来了。温烈交上来的泥地作业,虽然丑得像蚯蚓爬,但“钱”和“契”字勉强能认出来。
我二话不说,把昨天当掉原主唯一一根银簪子换来的钱买的半斤肥肉,切了薄薄的五片,
用水煮了,一人一片。那点肉腥味,香得五个孩子差点把舌头吞下去。“看见没?
这就是认字的好处!”我趁热打铁,“明天,教你们算数!学会了算数,
卖菜就不会被人骗秤!”生存的压力,和肉片的诱惑,
让这几个皮猴子爆发了惊人的学习热情。我的教学方式,也简单粗暴到令人发指。
没有四书五经,没有子曰诗云。全是干货。
面、油、盐、布、工、价、斤、两……实用算数:加减乘除(简单的)、算账、看秤、量尺。
穿插着讲点最基础的律法常识:比如签契约要按手印,借条怎么写,
被人打了该找谁(府衙的差役)……教材?不存在的。大地当纸,树枝做笔。偶尔捡点废纸,
写上字当宝贝传阅。晌午饭?糙米粥管够,运气好能飘点油花,或者加几片菜叶子。就这,
对这群孩子来说,已经是美味。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豆子回去帮刘大娘看豆腐摊,
居然认出了“豆”“腐”“三”“文”几个字,还奶声奶气告诉奶奶,
隔壁摊的秤可能有点问题,因为他用我教的法子,偷偷比划了一下。
刘大娘惊得差点把豆腐拍自己脸上。温烈他爹温老黑,有次接了笔小活,对方欺负他不识字,
契约写得模棱两可,想赖账。温烈梗着脖子,指着契约上的关键处,
磕磕巴巴但异常坚定地说:“这…这里写了!‘工成即付’!‘即’就是‘马上’的意思!
安先生教的!”温老黑差点抱着儿子哭出来,硬是讨回了工钱。口碑,这东西就像风,
挡不住。尤其是底层老百姓的口碑。“清风书院”这个名字,在城南这片贫民区,
悄悄传开了。“听说没?安先生那儿,真能学到东西!”“可不是!我家二狗子学了半个月,
去粮店帮工,掌柜的夸他算账快!”“才二十个铜板!还管饭!比请个伙计划算多了!
”学生,从五个,慢慢变成了十个,十五个……我的书院,像个热闹的集市。
院子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孩子,泥地上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字,
算盘声(我自己用木片和算珠串了个简易的)、背口诀声、争论声,混杂着糙米粥的香气,
充满了勃勃生机。债主们偶尔路过,看着这热火朝天的景象,眼神复杂。
老王头嘀咕:“这小娘子,还真有点邪门……”我兜里的铜板,叮叮当当,开始有了点分量。
除了必要的开销(主要是买粮食),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都攒着准备还债。
日子似乎有了奔头。直到那天下午。书院的门,被一脚踹开了。不是夸张,是真的“踹”。
那扇本就摇摇欲坠的破木板门,**一声,直接脱离了门框,哐当砸在地上,扬起一片尘土。
院子里瞬间安静。所有孩子都吓得缩起了脖子,惊恐地看着门口。进来三个人。
为首的是个穿着绸缎长衫、挺着肚子、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男人。脸皮白净,
但眼神里透着股油腻的精明和居高临下的傲慢。他身后跟着两个膀大腰圆、满脸横肉的家丁,
一看就是专业打手。这架势,跟黑社会收保护费似的。“谁是管事的?
”绸缎男捏着一块雪白的手帕,捂着鼻子,嫌弃地打量着这个破院子,声音尖细。
我放下手里教孩子们认“秤”字的木片,拍了拍手上的灰,走上前。“我是安乱,
这里的先生。阁下踹坏我的门,打算怎么赔?”我的声音很平静,甚至没什么火气。
在职场**多年,这种装腔作势的货色见多了。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露怯。
绸缎男显然没料到我这么直接,愣了一下,随即嗤笑一声,用手帕扇了扇风。“赔?呵,
一个破落户的烂门板,也值当爷赔?”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轻蔑,
“你就是那个安秀才的女儿?开这个什么……野鸡书院,坑蒙拐骗的安先生?”“坑蒙拐骗?
”我挑眉,“阁下有何指教?”“指教?”绸缎男哼了一声,
从袖子里慢悠悠掏出一张叠好的纸,刷地抖开,“认识字吧?看看这个!”我接过来。
是一张盖着鲜红官印的告示。内容大意是:本府为整饬学风,规范书院,
特令所有开馆授业之所,须经“文教司”核准,取得“授业凭信”。无凭信者,
视为非法办学,即刻取缔,并课以重罚。落款是府衙,日期是……半个月前。
我心里咯噔一下。文教司?这古代还有教育局?原主爹的记忆里,开个私塾,
好像没听说要什么官方牌照啊?这破地方,官老爷们平时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看清楚了?
”绸缎男得意洋洋地收回告示,“本老爷姓富,富守仁,‘文教司’新上任的司事!
专管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野路子!”富守仁?这名字跟他这做派,真是绝配的讽刺。
“所以呢?”我看着他。“所以?”富守仁像看傻子一样看我,“你这破地方,脏乱差!
误人子弟!非法办学!立刻给我关门!学生遣散!否则,
”他指了指身后两个凶神恶煞的家丁,“别怪我不客气!”“安先生!
”温烈蹭地一下站起来,小牛犊子似的挡在我前面,瞪着富守仁,“你凭什么赶我们走!
我们在这儿学得好好的!”“就是!我们不走!”豆子和其他孩子也鼓噪起来,虽然害怕,
但还是七嘴八舌地喊着。“反了天了!”富守仁脸色一沉,对着家丁一挥手,
“给我把这群小崽子轰出去!把这破院子给我砸了!”两个家丁狞笑着就要上前。“慢着!
”我的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冰冷,带着一种在职场高压下淬炼出的压迫感。
两个家丁脚步一顿。富守仁皱眉看我:“怎么?还想抗法?”我往前走了一步,
直视着他那双写满贪婪的眼睛,忽然笑了。“富司事,您新官上任,三把火。
烧到我这个破院子里来,真是蓬荜生辉。”我语气甚至带点恭维,但眼神没温度,“关门,
没问题。只是……”我故意顿了顿,环视了一圈院子里愤怒又害怕的孩子们,
还有门外探头探脑、敢怒不敢言的街坊邻居。“只是我这书院里,二十几个孩子,
都是左邻右舍街坊的孩子。他们爹娘,
有打铁的、卖豆腐的、挑粪的、扛包的……都是靠力气吃饭,脾气可能都不太好。
”我看向温烈:“温烈,你爹今天在家打铁吗?”温烈挺起胸膛,大声回答:“在!
我爹说今天要打把好刀!”我又看向另一个孩子:“二狗子,你爹今天是不是去码头扛活了?
”二狗子点头:“嗯!我爹说今天货多,跟十几个叔伯一起!”“哦……”我拖长了音调,
转回头,看着脸色微变的富守仁,“富司事,您看,这孩子们没学上,回家一哭闹,
他们那些干力气活的爹娘,要是知道了是您这位‘文教司’的大老爷,
亲手断了他们孩子唯一认字算账、将来可能不用再卖苦力的念想……”我凑近一步,
压低了声音,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您说,这些泥腿子,要是发起浑来,三更半夜,
往您那体面的府邸门口泼点粪,或者不小心把您家后院的墙砸个窟窿……府衙的差役老爷们,
管不管得过来?又愿不愿意为了您这点‘公务’,天天跟一群红了眼的苦哈哈耗着?
”富守仁的脸色,由白转青,再由青转红。他死死盯着我,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
他当然明白我的意思。强龙不压地头蛇。他这“文教司”司事,听着威风,
实际上就是个清水衙门里的闲职,没什么实权。真惹恼了这一片抱团的穷苦人,明枪易躲,
暗粪难防。府衙的差役?谁会为了他这点屁事,去得罪一群光脚不怕穿鞋的?
“你……你威胁本官?”他色厉内荏,声音都有点抖。“不敢。”我退后一步,
笑容可掬,“小女子只是跟富司事您,陈述一下‘关门’之后,可能发生的一点‘小麻烦’。
毕竟,和气生财嘛。”我特意在“财”字上,加重了语气。富守仁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
他捏着手帕的手,指节发白。显然,他在权衡。硬来,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沉默了几秒,
他忽然皮笑肉不笑地咧开嘴:“呵呵,安先生……好口才。”他收起了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又恢复了那副油腻腔调:“本官也是按章办事,为了孩子们的前程着想嘛。
既然安先生这里……教得还不错?”他环顾了一下,眼神里依旧充满鄙夷,但语气缓和了,
“那也不是不能通融。”来了。戏肉来了。“富司事的意思是?”“这个‘授业凭信’嘛,
”富守仁慢条斯理地捋着他的小胡子,“也不是不能办。就是需要点……嗯,‘核准费’,
还有书院各项条件的‘勘验费’、‘文书费’……杂七杂八加起来,也不多。
”他伸出三根胖乎乎的手指头,在我眼前晃了晃。“三十两银子?”我心里冷笑,
真敢开口。三十两,够普通人家吃用几年了。“安先生真会说笑!”富守仁夸张地摇头,
“是三百两!一次性缴清!保你书院顺顺当当,绝无后顾之忧!”三百两?!
院子里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孩子们都吓傻了。三百两!把我连人带书院拆零碎了卖,
也凑不出这个零头!这就是明抢!吃准了我拿不出,好名正言顺地赶我走,
或者……他肯定还有后手。果然,看我沉默(主要是被这狮子大开口惊的),
富守仁得意地笑了,压低声音:“当然,安先生若是手头一时不便,
本官……也不是不能体谅。这样,我有个折中的法子。
”他绿豆大的眼睛闪着精光:“城南‘明德书院’的吴山长,是我的至交好友。他那书院,
地方宽敞,名师坐镇,正是用人之际。安先生你这里的学生嘛,虽然资质差了点,
但吴山长心善,愿意接收。你呢,就带着这些学生,去明德书院‘挂靠’。”“挂靠?
”我明白了。“对!挂靠!”富守仁一副施舍的嘴脸,“学生还是你的学生,
你还管着他们。束脩嘛,你照收。只是这场地、名头,用的是明德书院的。你每月,
只需向明德书院缴纳一笔小小的‘管理费’即可。不多,每人……嗯,十五个铜板吧。如何?
”图穷匕见。什么狗屁授业凭信!什么非法办学!都是幌子!
他就是看中了我这里聚集起来的生源!想用官府的牌子压我,
逼我把辛辛苦苦招来的学生和收到的束脩,白白分一大块给那个什么“明德书院”!
他自己从中抽成!每人每月十五个铜板?我总共才收二十个!还要管一顿饭!去掉成本,
基本白干!等于我累死累活,替他和他那个“至交好友”打工!好一招釜底抽薪!
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我看着他那张贪婪**的脸,胃里一阵翻腾。“富司事,
”我慢慢开口,声音冷得像冰,“我的学生,虽然穷,但骨头不软。我安乱开的书院,
地方是破了点,但脊梁骨是直的。挂靠?给别人当孙子?还要倒贴钱?
”我嗤笑一声:“您这折中的法子,怕是折了我的骨头吧?”富守仁脸上的假笑瞬间冻结,
变得阴沉无比:“安乱!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官好言相劝,是给你脸!没有授业凭信,
你这破地方,今天就得关门!我看谁敢拦!”他身后的家丁再次上前,气势汹汹。“安先生!
”温烈又要冲上来。我一把按住他,脑子里飞速运转。硬顶?顶不住。
那两个家丁一看就是练家子,我们这群老弱妇孺加半大孩子,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喊街坊?
街坊们怕官,未必敢真为了我跟官府的人动手,顶多背后骂几句。怎么办?难道真要屈服?
看着富守仁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我肺都要气炸了。老娘当年在互联网大厂,
跟几千万的项目,跟难缠的甲方斗智斗勇都没怂过!
今天能被你这古代土鳖用这种下三滥手段拿捏了?就在这时,门外看热闹的人群里,
一个清朗又带着点戏谑的声音响起:“哟,富司事,好大的官威啊!
这是要把人家孤儿寡母的饭碗,往死里砸?”所有人循声望去。
只见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色长衫的年轻人,抱着胳膊,
斜倚在门框上(门板还在地上躺着)。他看起来二十出头,身材颀长,眉眼清俊,
嘴角挂着一丝懒洋洋的笑意,但眼神却很亮,像淬了寒星的刀锋。
他整个人透着一股……矛盾的气质。落魄,但又不羁。懒散,却又锐利。富守仁看到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