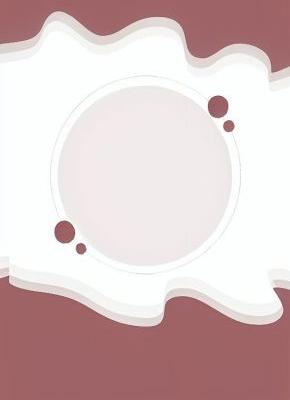
(高中时我是个小混混,她是年级第一的学霸。每次逃课翻墙,
总能看见她坐在墙角的秘密基地看书。我笑她书呆子,
她平静反问:“你为什么要故意考零分?”那年深夜,她为我包扎打架的伤口,
月光下我偷亲了她的额头。十年后同学会,她已是知名律师,而我依旧漂泊无依。
众人嘲讽间,她忽然起身,拿出泛黄的笔记本:“2013年4月12日,
今天他又考了零分,但我知道,他是把唯一一张答题卡塞给了被校园暴力的我。
”)_________________墙头碎掉的砖石窸窸窣窣地往下掉,
沈川单手一撑,利落地翻上来,骑在墙头。下午三四点的阳光还有点刺眼,他眯缝着眼,
嘴里叼着根干枯的狗尾巴草,视线习惯性地往墙角那片浓密的香樟树荫下扫。果然,又在。
林晚舟。那个名字总是贴在成绩单最顶端的女生。此刻正安安静静地坐在树荫底下的石凳上,
膝盖上摊着一本厚得能砸死人的书,微微低着头,脖颈弯出一道白皙又脆弱的弧线。
阳光透过枝叶缝隙,在她洗得发白的校服上跳跃,
也在她浓密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颤动的阴影。这地方是学校后墙一个废弃的角落,僻静,
没人打扰,是沈川逃课出去的必经之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林晚舟的秘密读书角。
沈川啧了一声,吐掉嘴里的狗尾巴草,轻巧地跳下墙头,拍了拍手上的灰,
吊儿郎当地走过去。“喂,书呆子。”阴影挪动,笼罩了她书页上的光。林晚舟没被吓到,
甚至连头都没抬,只是目光从书页上微微上移,隔着一层薄薄的镜片,安静地看着他。
那眼神太静了,像深潭的水,反而让准备了一肚子嘲弄话的沈川有点不自在起来。
他踢了踢脚边一颗小石子,石子咕噜噜滚开。“天天抱本书啃,不腻啊?读傻了都。
”她合上书,封面上是几个艰涩的英文单词,沈川一个都不认识。“翻墙会扣班级操行分。
”她声音平平的,没什么情绪。“关你屁事。”沈川嗤笑,下意识摸了摸颧骨,
那里前天打架留下的淤青还在隐隐作痛,“老子乐意。”他等着她像其他好学生那样,
要么皱起眉头走开,要么板着脸训斥几句“不知上进”。但他等来的,只是一片沉默。
林晚舟只是看着他,那双过于平静的眼睛,像是一下子看进了他骨头缝里。然后,
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像颗钉子,猝不及防地砸进他耳朵里。“你为什么要故意考零分?
”沈川脸上的痞笑瞬间冻住了。心里那根一直绷得紧紧的、自以为无人察觉的弦,
猛地被人拨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嗡鸣。周围的空气好像都跟着震了震。
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几乎要跳起来,嗓门猛地拔高,
试图用声势掩盖那瞬间的慌乱:“你胡说什么?!老子就是不会!懒得写!谁故意了?!
”林晚舟没反驳,也没害怕,只是重新低下头,打开了膝盖上的书,
轻声说:“快打上课铃了。”那样子,仿佛刚才那句石破天惊的问话,
只是随口一提今天天气不错。沈川一口气堵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憋得难受。
他狠狠瞪了她一眼,却发现人家根本不在意,注意力早已回到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上。
他觉得自己像个对着空气挥拳的傻子,最终只能悻悻地“操”了一声,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
背影都带着一股恼羞成怒的狼狈。之后好些天,沈川翻墙都刻意避开了那个时间点。
也说不上为什么,就是不太想看见那双过分安静的眼睛。再次狭路相逢,是在一个深夜。
沈川刚跟校外一群找事的社会青年干了一架,一挑三,虽然没吃大亏,
但胳膊被碎玻璃划了道口子,**辣地疼。他咬着牙,嘴角也裂了,渗着血丝,
一身狼狈地翻回学校,想溜回宿舍清理。路过那片香樟树荫时,他鬼使神差地停了一下。
夜很深了,角落里黑黢黢的,应该没人。他刚松了口气,
一个清冷的声音就从黑暗里响起来:“你又打架了。”沈川吓得一哆嗦,差点没跳起来。
定睛一看,林晚舟居然还坐在那张石凳上,借着远处路灯透过来的一点微弱的光,
看着……一本单词书?“**!你有病啊?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儿装鬼?”沈川心有余悸,
口气冲得要死。林晚舟合上书,站起身走过来。她个子不高,堪堪到他肩膀,走近了,
能闻到她身上一股淡淡的、好闻的肥皂清香,混着一点墨水的味道。她没理会他的叫嚣,
目光落在他流血的手臂上,眉头几不可见地蹙了一下:“你需要处理一下。”“用不着!
”沈川别开脸,想走。她却挡在他面前,语气是不容拒绝的平静:“会感染。”说完,
她也不管他同不同意,转身走回石凳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巧的急救包。沈川愣住了。
这书呆子,大半夜的,书包里还装着这个?她站在那儿,看着他,眼神在月光下清凌凌的。
沈川脚底下像生了根,那声“滚开”在喉咙里滚了几滚,莫名其妙地咽了回去。
他磨磨蹭蹭地走过去,别扭地在她面前坐下,把受伤的胳膊伸过去,
嘴里还不肯服软:“…事儿真多。”林晚舟没接话,拧开一瓶矿泉水,又拿出棉签和碘伏。
她的动作有点生涩,但异常仔细小心。冰凉的液体触到伤口,沈川疼得“嘶”了一声,
肌肉猛地绷紧。“忍着点。”她说,声音低低的,像夜风。他不动了。月光很好,
水银一样倾泻下来,把她整个人都笼在一层柔和的光晕里。他能看清她低垂着的眼睛,
长长的睫毛投下小小的阴影,还有她鼻梁上那副略显老气的眼镜,
以及她微微抿着的、没什么血色的嘴唇。她离他很近,近得他能感受到她的呼吸,很轻,
带着一点温暖的湿意。周围太安静了,只有棉签擦过伤口的细微声响,
还有不知名夏虫的鸣叫。他闻着她身上那股干净的肥皂香,看着她在月光下格外柔和的侧脸,
心里那点暴躁和戾气,像是被这月光和她的动作一点点抚平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的悸动,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撞得他胸口发麻。鬼使神差地,
他低下头,嘴唇飞快地、轻得像一片羽毛似的,碰了一下她的额头。冰凉的,
带着夜露的湿润和一丝碘伏的味道。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滞了。林晚舟的动作瞬间僵住了,
棉签掉在地上。她猛地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愕然地睁大,看着他,
里面清晰地映出他同样惊慌失措的脸。沈川像是被烫到一样弹开,猛地站起身,
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狂跳,几乎要要撞出来。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吐不出。
下一秒,他转身就跑,几乎是落荒而逃,受伤的胳膊甩动着,疼痛都感觉不到了,
只有额头上那片刻冰凉柔软的触感,和那双震惊的眼睛,反复灼烧着他。那天之后,
沈川躲她躲得更厉害了。偶尔在校园里远远看见,都会立刻绕道走。高考像一阵狂风,
卷着所有人仓促地往前奔。再后来,就是各奔东西。他再也没见过林晚舟。……十年。
同学会的请柬发到他那个几乎要废弃的邮箱时,
沈川正被房东堵在门口催缴拖欠了两个月的房租。他赔着笑脸,说了半箩筐好话,
才把人暂时哄走。关上门,破旧的老公寓里弥漫着一股泡面和陈旧家具混合的味道。
他靠在门上,疲惫地搓了把脸。手机屏幕亮着,邮件里“林晚舟”三个字像根细针,
轻轻扎了他一下。他去参加了。穿着唯一一件还算体面的衬衫,坐在包厢最角落的位置。
看着周围那些依稀还能看出当年模样的同学,如今大多西装革履,
言谈间不是上市融资就是学区房,意气风发。他沉默地喝着桌上的免费茶水,
像个误入的局外人。然后包厢门被推开,林晚舟走了进来。时光似乎格外优待她。
褪去了少女时期的青涩和单薄,代之以一种干练而优雅的气质。剪裁合体的白色西装套裙,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自信的声响。她脸上画着精致的淡妆,眼神沉静而锐利,
唇角带着得体疏离的微笑。有人热络地迎上去,称呼她“林大律师”。
她一眼就看到了角落里的他,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半秒,没有任何波澜,又自然地移开,
仿佛只是扫过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沈川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收紧,
攥紧了廉价的玻璃茶杯。胸口某个地方,闷闷地涩了一下。饭桌上,
话题不知怎么就被引到了过去。几个喝高了的老同学开始忆往昔,说着说着,
就提到了当年每次考试都稳坐倒数第一宝座的沈川。“川哥当年可是风云人物啊!哈哈哈,
门门零蛋,也是种本事!”“听说现在搞……呃,自由职业?”语气里的揶揄掩饰不住。
“当年要不是林大学霸总在老师那儿帮你打圆场,
你估计早就被劝退了吧哈哈……”哄笑声中,沈川感觉像被人剥光了扔在聚光灯下,
那些刻意尘封的难堪和自卑汹涌地冒出来。他扯了扯嘴角,想配合地笑一下,
却发现脸上的肌肉僵硬得很。他端起酒杯,想用一口辛辣的液体压下喉咙口的堵塞感。
就在这时,一直安**着、对周遭奉承和闲聊都只是淡淡回应的林晚舟,忽然放下了筷子。
陶瓷磕碰在骨碟上,发出清脆一响。整个包厢竟因为这微小的一声,诡异地安静了一瞬。
所有人都看向她。只见林晚舟拿过放在身旁的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个本子。
不是现在律师常用的平板或笔记本电脑,而是一个很旧、边角都磨得起了毛的软皮笔记本。
封皮是那种早已过时的淡黄色。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她站起身,高跟鞋清晰地敲击地面,
一步步走到沈川面前。包厢里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送风声。她打开笔记本,翻到某一页。
纸张已经泛黄,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清秀工整的字迹,是那种典型的好学生的笔记。
她抬起眼,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沈川骤然僵住的脸上。她的声音不大,
却清晰无比地落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像冰珠砸落玉盘。“2013年4月12日,天气晴。
”她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念得无比清晰。“今天物理小测,他又考了零分。但我知道,
他不是不会。”“他是把唯一一张答题卡,
从桌子下面塞给了当时被隔壁班那群人吓得发抖的我。”“我的答题卡,被他们撕了。
”沈川手里的酒杯,“哐当”一声掉在桌上,酒液泼洒出来,浸湿了他廉价的衬衫袖口。
他却毫无所觉,只是猛地抬起头,瞳孔剧烈地颤抖着,难以置信地看向她。
满堂的喧哗像被一只无形的手骤然掐断。酒液顺着粗糙的桌布边缘,一滴、两滴,
落在沈川的裤子上,冰凉地洇开一小片。但他完全感觉不到,所有的感官,所有的意识,
都被那个站在他面前,握着泛黄笔记本的女人攫取了。耳边嗡嗡作响,
那些刻意遗忘的、属于十年前那个闷热下午的画面,裹挟着灰尘与阳光的味道,
猛地撞进脑海。逼仄的楼梯间。被撕得粉碎的、写满了工整公式的答题卡纸屑,
雪花般散落一地。隔壁班那几个以欺负人为乐的男生,围着那个瘦小的身影,哄笑声刺耳。
他本来只是路过,想躲清静去天台抽烟,却一眼看见了被围在中间的她。低着头,
肩膀微微发抖,像一片被狂风摧残的叶子,却死死咬着嘴唇,一声不吭。那一刻,
说不清为什么,一股无名火猛地窜上头顶,烧掉了他所有的理智和“少管闲事”的准则。
后来呢?后来就是混乱。他冲上去,推开为首的那个胖子,骂骂咧咧。推搡,叫骂,
拳头砸在肉体上的闷响。他其实没那么能打,只是够狠,不要命似的。
背后不知道挨了多少下踹,**辣地疼。混乱中,
干净却空白的答题卡——他本来打算交白卷气气那个总找他麻烦的物理老师——几乎是本能,
他趁着扭打的间隙,一把塞进她手里,压低声音吼:“快走!”她惊慌地抬头,
眼睛红得像兔子,里面全是水光。“可是你……”“别废话!滚啊!
”他恶声恶气地推了她一把,转身迎上又一记拳头。再后来,
他被闻讯赶来的教导主任拎到办公室,窗外是那几个男生恶人先告状的得意嘴脸。
他懒得解释,梗着脖子,对所有质问报以沉默和冷笑。最后的结果,无非是请家长,写检讨,
通报批评。物理小测,他交了白卷,一个大大的零分,鲜艳刺目。他以为自己掩护得很好,
这一切都会随着那张被撕碎的答题卡一起,被扫进记忆的垃圾堆。他从未想过,
会有第二个人知道真相。更没想过,知道的人,会是她。而且,她记了十年。
林晚舟的目光穿越了十年的时光,终于稳稳地、重重地落回他身上,那双平静的眼睛里,
翻涌着他从未见过的、复杂而汹涌的情绪。她看着他,继续念出了那页日记的最后一句,
声音微微哑了下去,却带着千斤的重量:“他替我挨了打,背后被踹了很多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