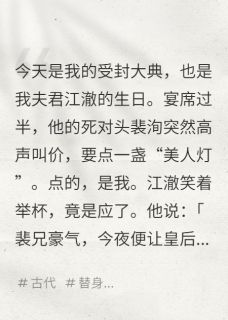
今天是我的受封大典,也是我夫君江澈的生日。他当着满朝文武,亲自为我戴上凤冠。
宴席过半,他的死对头裴洵突然高声叫价,要点一盏“美人灯”。点的,是我。
江澈笑着举杯,竟是应了。他说:「裴兄豪气,今夜便让皇后陪你尽兴。」
我看着他眼底对那个白月光——裴洵亲妹妹裴月的愧疚,忽然就懂了。我缓缓起身,
走到大殿中央,接过侍者递来的酒。「既然陛下将臣妾当做玩物赏人,那臣妾也自寻个新主。
」我对着错愕的裴洵,一饮而尽。「这盏灯,我接了。」「但从今往后,江澈你点的不是灯,
是你江家的坟。」1我垂下手臂,沉重的凤冠压得我脖颈发酸。金杯里的酒液晃动,
映出大殿之上,我夫君江澈那张含笑的脸。他没有看我,他在看裴洵。
那是一种混杂着歉意、纵容,甚至带着一丝病态讨好的表情。我懂了。三年来,
我早已学会读懂他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尤其是当他想起裴月的时候。我一步步走下高台,
脚下织金的地毯软得像棉花,却踩得我骨头生疼。满朝文武的目光像无数根针,扎在我身上。
羞耻感像潮水,一波一波地冲刷着我的天灵盖。我走到裴洵面前。他坐在那里,
依旧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可我知道,他并没有真的在笑。他只是在看一场荒唐的戏。
而我,就是戏里的那个小丑。我端起酒杯,对着他。「裴大公子,这杯酒,我敬你。」
裴洵没动,只是看着我。「皇后娘娘客气,这盏灯,裴某还未付钱。」「不必了。」
我一口饮尽杯中烈酒,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我将空杯倒置,重重地磕在桌案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钱,江澈已经替你付了。」「用我苏瑾的尊严,用镇国公府的颜面,
用这大周朝的国母之位,够不够?」说完,我不再看任何人,转身就走。身后,
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议论声。我能感觉到江澈的视线,
像一道冰冷的利剑,钉在我的后心。可我没有回头。裴洵跟了上来,他的披风擦过我的手臂。
我们就这样,在一国之君的注视下,在一众朝臣的惊愕中,走出了这座金碧辉煌的牢笼。
马车行驶在深夜的街巷,最终停在了一座僻静的别院前。裴洵的人将我引至一间雅致的厢房,
然后便悄无声息地退下了。他没有碰我,甚至没有多说一句话。只在临走前,他停在门口。
「苏瑾,你到底想做什么?」我没有回答。他似乎也并不期待答案,转身阖上了门。
房间里燃着安神的熏香,和我坤宁宫里用的一模一样。呵,又是裴月喜欢的味道。
我卸下那顶几乎压断我脖子的凤冠,随手扔在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我看着铜镜里那张脸。这张脸,七分像裴月。三年前,正是因为这张脸,
江澈在众多贵女中一眼选中了我。那日,他还是太子,他抚摸着我的脸颊,
动作轻柔得像是对待一件稀世珍宝。我以为那是爱意。直到他开口。「安分守己,
做好像她的人,你想要的一切我都能给你。」他的声音很温柔,
温柔得像一把裹着蜜糖的刀子,一寸寸捅进我的心里。他说。「别妄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尤其是我的心。那里面,早就住满了。」「你要记住,你只是她的影子。」那时我太年轻,
以为只要我足够好,足够爱他,总有一天,他会看到我,而不是透过我,去看另一个人。
我天真地以为,我可以成为那个例外。现在想来,真可笑。我从回忆中抽离,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镜中的女人,脸上没有一丝悲戚,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冷。
过去三年顺从又卑微的爱慕,不过是我一个人自导自演的独角戏。入戏太深的人,是我。
而他,从始至终,都是那个最清醒的看客。从今往后,不会了。苏瑾已死,
死在那场盛大的册封典礼上。活下来的,只是一个来讨债的恶鬼。2天刚蒙蒙亮,
院外就传来一阵嘈杂的甲胄碰撞声。是江澈的禁军。他动作倒是快。我推开窗,
看到裴洵正站在院中,与禁军统领对峙。禁军统领高声叫嚷。「裴大人,陛下有令!
皇后苏氏私德有亏,秽乱宫闱,请您立刻将人交出,否则便以同谋论处!」
裴洵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自己的袖口。「张统领好大的官威。本官只知皇后乃一国之母,
乃陛下正妻,受朝堂礼法所立。不知这‘私德有亏’是哪条王法?又是谁定的罪?
三司会审了吗?宗人府下文了吗?」他几句话,堵得那张统领面红耳赤。
「你……你这是要抗旨不成!」「本官不敢。只是凡事要讲规矩,陛下也不能例外。
你若有圣旨,便拿出来。若没有,就请回吧。惊扰了皇后凤驾,你担待不起。」
禁军被堵在门外,一时竟不敢妄动。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江澈的耐心有限,
裴洵也护不了我多久。我走到他身后。「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裴洵转过身,打量着我。
「你又能给我什么?」「一个扳倒江澈的机会。」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
「我知道你一直在查江澈与前朝余孽勾结的证据。我这里有。」
裴洵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我凭什么信你?」「就凭我是苏瑾,镇国公的女儿。
我父亲一生忠烈,绝不会任由一个勾结乱党的君王,毁掉这大周江山。」「也凭,我恨他。」
我没有给他追问的机会,转身回了房。我需要时间,更需要他的庇护。他会同意的,
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同一个人。3独自一人时,那些被刻意压制的记忆,
又如附骨之疽般涌了上来。一年前的冬天,梅林。那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江澈心血来潮,
要带我去赏梅。他说,阿月最喜欢冬日的红梅。我穿着单薄的宫装,
在寒风中陪他站了两个时辰。就在那时,刺客出现了。混乱中,一支淬了毒的箭,
直直射向江澈的心口。我几乎是凭着本能,扑到了他的身前。箭矢穿透皮肉的闷响,
清晰得可怕。我感觉不到痛,只觉得后背一阵冰凉,随即是滔天的热意涌出,
染红了身下的白雪。倒下前,我看到了江澈震惊的脸。那一刻,我甚至还在奢望,
我用命换来的,会不会是他的一丝真心。我在病榻上昏迷了三日。醒来时,房间里很暗,
只有江澈和他心腹的说话声。心腹的声音带着后怕。「陛下,这次多亏了娘娘,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听到了江澈的一声轻笑。那笑声很轻,却像一把淬了冰的锥子,
扎进我的耳朵里。他说。「是啊,幸好伤在背后。」「若是伤了这张脸,
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像的了。」轰的一声。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名为“爱恋”的弦,彻底断了。
原来,我的命,我的奋不顾身,在他眼里,都比不过这张酷似别人的脸。从那一刻起,
我心里的爱意,便已彻底死去。剩下的,只有麻木的扮演。大殿上的决裂,
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现在,我不想再演了。这出戏,该换个主角了。
4江澈最终还是退兵了。不是因为裴洵,而是因为朝堂上那些迂腐的言官。
“皇后出走”的丑闻,他捂不住了。我猜,此刻的他,应该回了坤宁宫。
那个我住了三年的地方。裴洵的人传来消息时,印证了我的猜想。江澈在坤宁宫待了一整夜。
他大概是想去找一些我存在的痕迹,来证明我只是在闹脾气,证明我还会回去。他会失望的。
坤宁宫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所有宫人都守着规矩。但他会发现,
所有真正属于“苏瑾”的东西,都不见了。我亲手为他绣的香囊,没了。
我彻夜为他抄写的诗集,没了。我闲来无事养在窗台上的那盆兰花,也没了。那里干净得,
就像我从未住过一样。他会发怒,会质问宫人。但没人能回答他。因为那些东西,
都被我亲手烧了,在我决定离开的那一天。最后,他会在床下,发现一个落了灰的木盒。
他会打开它。里面,是他三年来赏赐给我的所有东西。东海的珍珠,西域的宝石,
江南的锦缎。所有的一切,都是裴月生前最喜欢的款式和颜色。他曾以为这是恩赐,
是我天大的福分。在盒子的最底下,他会看到一张纸。上面是我留给他的最后八个字。
“赝品归位,两不相欠。”5裴洵将一封密信递给我。「如你所料,他气疯了,
砸了半个坤宁宫。」我展开信纸,上面是父亲的笔迹,报了平安,让我勿念。
这是我通过裴洵的关系网,联系上的家族旧部。我需要他们。「他现在一定很恐慌吧。」
我轻声说。裴洵看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些什么。「他失去的不是一个皇后,
而是一个他早已习惯的影子。一个能让他心安理得怀念我妹妹的影子。」「他不是爱我妹妹,
他只是爱那种‘爱着’的感觉。如今影子没了,他的深情也就无处安放了。」
我将信纸凑到烛火上,看着它化为灰烬。「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等。」
我看向窗外漆黑的夜。「等他出招。他越是愤怒,就越容易出错。」江澈,
你以为你失去的只是一个赝品吗?不。你失去的,是你皇位的基石。镇国公府数代忠良,
我父亲在军中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你当初娶我,固然是为了我这张脸,
又何尝不是为了安抚我父亲,稳固军心?如今,你亲手将这一切都毁了。
你以为我只是一个任你摆布的玩偶。你很快就会知道,玩偶也是会咬人的。而且,
会咬断你的喉咙。6江澈的后招,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也更狠。他没有再派人来裴府要人。
一道圣旨,直接送到了镇国公府。父亲被下了天牢。罪名是,通敌叛国。真是个不错的罪名,
足以诛九族。第二日,皇榜贴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三日后,午时,法场问斩镇国公苏威。
同时,一辆马车停在了裴府门前,传召我与裴洵,法场“观刑”。这是阳谋。
他就是要逼我出去,逼我自投罗网。法场之上,人山人海。我穿着一身素衣,
与裴洵并肩站在监斩台上。江澈就坐在最高处,穿着明黄的龙袍。他看到我,笑了。
那笑容里,满是势在必得的傲慢。他朝我举了举酒杯,像是在说,你看,你还是回来了。
我看着被押在法场中央,满身血污却依旧脊梁挺直的父亲,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午时三刻已到。监斩官扔下了令牌。
“斩”字还没喊出口,江澈却抬了抬手。「且慢。」他站起身,一步步从高台上走下来,
走到我父亲面前。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说些什么。但他没有。
他只是从侍卫手中拿过一个古朴的玄铁盒子。「镇国公,朕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交出镇国印信,朕可饶你不死。」父亲冷笑。「乱臣贼子,也配提‘镇国’二字?」
江澈也不恼。「朕知道,印信需由苏家嫡系血脉之血才能激活。来人,取血。」
立刻有侍卫上前,用匕首划破了我父亲的手指。鲜血滴落在玄铁盒子上,却毫无反应,
只是顺着盒身滑落。江澈的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他转过头,看向我。「苏瑾,
你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没用?」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全身。
「因为朕早就知道,你父亲,根本不是关键。」他一字一句,声音不大,
却像惊雷在我耳边炸开。「朕费尽心机迎娶你,让你当上皇后,你以为,
真的只因为你长得像阿月吗?」「朕的情报说,能激活印信的真正嫡系血脉,是你这一代!」
他的话音刚落,一辆囚车被缓缓推了上来。囚车里,是一个蜷缩着的身影。那是个男孩,
看起来不过七八岁的年纪,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身上穿着破烂的囚服,脸上满是污垢。
可那双眼睛,那张脸的轮廓,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像我,也像父亲。是我苏家的血脉!
江澈走到囚车前,一把揪住男孩的头发,将他的脸抬了起来,展示给所有人看。「苏瑾,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从未谋面的亲弟弟,苏长庚。你们苏家藏得可真好啊,
在乡下藏了这么多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
弟弟……我竟然还有一个弟弟……江澈对着我,露出了他最残忍,也最得意的笑容。「现在,
朕给你最后一个选择。」「要么,你交出真正的印信,然后乖乖回到朕的身边,
做一辈子听话的傀儡。」「要么,朕就当着你的面,将他活活放血,用他的命,
来激活这镇国印信。」「你选一个吧,我的好皇后。」7时间仿佛静止了。
法场上所有人的声音都消失了,我只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和囚车里那个孩子微弱的喘息。
那是我的弟弟。我从未见过,却血脉相连的弟弟。江澈用他来威胁我。用我至亲的性命,
来逼我就范。裴洵上前一步,想说什么,我却抬手制止了他。我看着高高在上的江澈,
看着他那张志在必得的脸。我缓缓地,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我听到自己声音,
平静得不像话。「放了我父亲和我弟弟。我跟你回去。」江澈笑了,笑得畅快淋漓。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非要闹得这么难看。」他挥了挥手,父亲和弟弟被带了下去。
我能感觉到裴洵的目光,充满了不解和担忧。我没有看他,只是用口型,
无声地对他说了一个字。“拖。”然后,我转过身,一步步走向江澈,
走向那个我刚刚逃离的,更华丽的囚笼。回到宫中,我被软禁在了坤宁宫。江澈大概是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