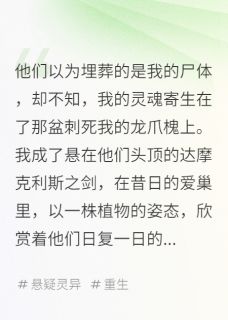
他们以为埋葬的是我的尸体,却不知,我的灵魂寄生在了那盆刺死我的龙爪槐上。
我成了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昔日的爱巢里,以一株植物的姿态,
欣赏着他们日复一日的恐慌,等待着亲手将他们拖入地狱。【1】意识回笼的瞬间,
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混杂着我最熟悉的松脂与湿润泥土的气息。我死了。
这个认知清晰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思维。最后的记忆,是我最爱的丈夫顾衍,
用我最得意的盆栽作品——那盆被我命名为「龙爪探海」的龙爪槐,
用那根我亲手雕琢、状如龙爪的锐利枯枝,狠狠刺穿了我的心脏。
我甚至还记得他脸上那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杀人后的惊恐,不是失手误杀的悔恨,
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冰冷的、带着一丝快意的残忍。他说:「林静,别怪我,
你的艺术太烧钱了,而我,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开始?用我的命和我的钱?
我奋力想睁开眼,想嘶吼,想质问,可我发不出任何声音,也感觉不到四肢的存在。
我的视野一片怪异,像是透过无数细小的缝隙在观察这个世界,高高在上,
又带着植物特有的、静默的广角。我看到了我的尸体,就倒在工作室的地板上,
鲜血从心口汩汩流出,浸润了名贵的波斯地毯。而「我」,
正被摆放在尸体旁边的红木几案上。我,成了那盆龙爪槐。我的意识,我的灵魂,
被禁锢在了这盆亲手养育了十年,最终却夺走我生命的植物里。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水分从根系缓缓向上输送,
能感觉到工作室里微弱的气流拂过我的每一片叶子。我甚至能「看」到顾衍,
我那情深义重的丈夫,正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现场。他戴上手套,用抹布擦拭着我「身上」
那根作为凶器的枝干,将上面的血迹和他的指纹擦得一干二净。然后,他将我的尸体拖拽着,
伪造出被钝器击打头部的假象,又翻箱倒柜,制造出入室抢劫的场景。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冷静得可怕,仿佛排练了千百遍。做完这一切,他脱掉手套,
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领,脸上瞬间切换成一副悲痛欲绝的表情,颤抖着拿出手机,
拨通了报警电话。「喂……警察吗?我……我妻子……她……她出事了!就在我们家!
快来人啊!」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恰到好处的哽咽与惊慌,逼真到如果我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会被他这影帝级别的演技所蒙骗。电话挂断,他脸上的悲痛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冷的审视。他走到我的尸体旁,蹲下身,眼中没有半分爱意,
只有对一件物品的估价。「林静啊林静,你这双摆弄盆景的手倒是巧,可惜,脑子太笨了。」
他轻声呢喃,像是在对我,又像是在对自己说,「你的保险金,你的遗产,
足够我和微微过上好日子了。你就安心地去吧,你的那些宝贝盆栽,我会替你『照顾』好的。
」微微?白微?我最好的闺蜜,我最信任的妹妹,那个一口一个「静姐」,
说要跟我学一辈子盆景艺术的女孩?巨大的震惊和背叛感化作无形的惊雷,
在我的意识里炸开。我感觉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盆中的泥土簌簌作响。
顾衍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疑惑地抬起头,看向我所在的这盆龙爪槐。
他的目光与我无形的视线在空中交汇。我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惧,
随即又被他强行压下。他冷笑一声,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伸出手,
轻轻抚摸着我一片肥厚的叶子。「怎么?死了都不安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充满了威胁,
「林静,别忘了,你现在只是一盆不会说话的植物。我能让你『活』,也能让你彻底枯死。
给我安分点,否则,我不介意把你连盆带土,一起扔进焚化炉。」
冰冷的恶意顺着他的指尖传来,让我如坠冰窟。我猛然意识到,他或许……知道些什么。
他知道我的灵魂没有消散,他知道我在这盆栽里!不,这不可能!这太荒谬了!
可他那笃定的眼神,那充满威胁的话语,又让我不得不信。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警笛声。顾衍的脸上再次堆满了悲伤,他最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像是在警告一只不听话的宠物。然后,他快步跑去开门,用他那副悲痛欲绝的腔调,
迎向了即将到来的警察。而我,只能以一株植物的形态,静静地立在这片血泊之中,
眼睁睁看着凶手在我面前上演着一出天衣无缝的戏码。无尽的怨恨与冰冷的绝望,
像疯狂的藤蔓,瞬间缠绕住我的灵魂。顾衍,白微。我一笔一划地,
在心里刻下了这两个名字。只要我还在,只要这盆龙爪槐还存在于世,我发誓,
我会让你们的「全新开始」,变成一场永无宁日的噩梦。【2】警察很快拉起了警戒线,
为首的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眼神锐利如鹰的男人。同事们叫他陈队,陈默。他沉默寡言,
但目光所及之处,仿佛能洞穿一切虚妄。顾衍的表演还在继续。
他声泪俱下地讲述着自己如何回家,如何发现惨剧,每一个细节都编造得天衣无缝。
他说自己下午一直在公司开会,有几十个同事可以作证。「我妻子是个盆景艺术家,
平时很少与人结怨,唯一的爱好就是侍弄这些花花草草……怎么会有人这么残忍,
为了点钱就下此毒手……」他说着,还假惺惺地走到我面前,
用一种饱含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这盆龙爪槐。「这是静静最得意的作品,
她说这盆龙爪槐有灵性,是她的心头肉……」陈默的视线顺着他的话,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的目光很沉,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审视和探究。他绕着我走了两圈,最后,
视线定格在那根作为凶器的枝干上。「这根树枝很特别。」陈默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平稳,
「看起来像是被人精心打磨过,边缘非常锋利。」顾衍的心跳明显漏了一拍,
但他很快掩饰过去,悲伤地说:「是的,这是盆景的一种技艺,叫做『舍利干』,
是静静亲手做的。她说,这能让盆景更具苍古之美。谁能想到,这竟成了……」
他说不下去了,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抽动起来。陈默没有安慰他,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
转头对身边的法医说:「重点检查死者心口的伤口,和这根树枝的形态做比对。」法医点头,
开始工作。而我,则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陈默身上。我能感觉到,这个男人不好骗。
他身上有一种不被情绪左右的冷静,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正准备剖开顾衍伪装的外衣。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熟悉的身影扑了进来。「静姐!」是白微。
她穿着一身素雅的白裙,脸上挂着泪痕,看起来比顾衍还要悲痛。她踉跄着扑到我的尸体旁,
哭得撕心裂肺。「静姐!你怎么就这么走了!是谁这么狠心啊!你醒醒啊!」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了真相,我一定会被她此刻的真情流露所打动。顾衍立刻上前,将她扶起,
拥入怀中,轻声安慰:「微微,别太难过了,你要保重身体……」两人相拥而泣,
在众人眼中,一个是痛失爱妻的丈夫,一个是痛失挚友的妹妹。多么感人肺腑的画面。
可是在我的视角里,我却清晰地看到,在旁人看不到的角度,顾衍的手,正充满安抚意味地,
在白微的后背上缓缓摩挲。而白微埋在他怀里的脸上,
嘴角勾起了一抹若有若无的、得意的微笑。我的「叶片」因为愤怒而剧烈地颤抖起来。
这细微的动静,再次吸引了陈默的注意。他不动声色地走了过来,目光再次落在我身上。
他似乎有些疑惑,为什么一盆室内盆栽,会在没有风的情况下,抖动得如此厉害。他伸出手,
似乎想触碰我。就在他的指尖即将碰到我叶子的瞬间,我集中了全部的怨念与恨意,
将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顺着他的指尖传递了过去。陈默的身体猛地一僵,
如同触电般缩回了手。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诧,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又抬头看了看我。
那眼神,不再仅仅是审视,而是多了一丝……无法言说的惊疑。「陈队,怎么了?」
旁边的小警察问。陈默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但他的眉头却锁得更紧了。他绕到我的另一侧,
视线越过我的枝叶,正好看到顾衍和白微那短暂而隐秘的对视。那一眼里,
包含了太多信息——安抚、警告,以及共享秘密的默契。这一切,都被陈默尽收眼底。
他的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但我能感觉到,怀疑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调查在继续,
法医的初步结论出来了:死者死于心脏被锐器刺穿,与这盆龙爪槐的枝干形状高度吻合。
死亡时间大概在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而顾衍提供的完美不在场证明,
恰好覆盖了整个时间段。一切的证据,都指向了一场失败的入室抢劫杀人案。
顾衍和白微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放松。只有陈默,在所有人都准备收队的时候,
又一次走到了我的面前。他静静地站着,看了我许久。「你说,植物真的有灵性吗?」
他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旁边的小警察挠挠头:「陈队,您说什么呢?」陈默没有理他,
只是自言自语般地说道:「如果真的有,那它一定看到了全部的真相。」说完,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在那一瞬间,我仿佛从他深邃的眼眸中,看到了一丝承诺。
顾衍,白微,你们的表演,或许能骗过所有人,但你们骗不过他,更骗不过我。
这场复仇的游戏,才刚刚开始。【3】我的葬礼办得风光而体面。
顾衍为我挑选了最贵的墓地,举办了最隆重的仪式。在葬礼上,他念着我亲手为他写的情书,
讲述着我们之间那些甜蜜的过往,泣不成声。「林静,你是我此生的挚爱,
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光。你走了,我的世界也塌了……」台下,亲朋好友们无不为之动容,
纷纷上前安慰这个「可怜」的男人。而我,作为他口中的「挚爱」,
却被他当成一件普通的装饰品,摆放在灵堂最显眼的位置。我冷冷地「看」
着这场由我的血肉和生命堆砌起来的盛大演出,心中没有悲伤,只有彻骨的寒意。
白微则以我「最好妹妹」的身份,全程陪伴在顾衍身边,她穿着黑色的丧服,脸色苍白,
眼神哀戚,时不时用手帕擦拭着眼角,将一个悲痛欲绝的闺蜜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宾客散尽后,灵堂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前一秒还悲痛得站不稳的顾衍,瞬间直起了腰,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哪还有半分悲伤。「累死我了。」他扯了扯领带,语气里满是厌烦,
「总算结束了。」白微立刻体贴地走上前,为他捏着肩膀,声音娇媚入骨:「衍哥,
辛苦你了。不过,你的演技真好,把所有人都骗过去了。」「那当然。」顾衍得意地一笑,
反手将她揽入怀中,手指不规矩地在她腰间游走,「不这样,怎么能让他们相信,
我有多爱那个女人?」「那……你爱过她吗?」白微仰起头,眼中带着一丝挑衅。
顾衍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随即化为不屑的冷笑:「爱?或许吧。我爱她的钱,
爱她能为我提供一个安逸的创作环境,更爱她那份愚蠢的、无条件的信任。但人嘛,
总是会腻的。尤其是她那副永远沉浸在自己世界里,对几根破树枝比对我还上心的样子,
我早就受够了!」他顿了顿,低头在白微的唇上狠狠亲了一口。「还是你最好,微微,
你才是我想要的女人,热情、奔放,懂得享受生活。」白「微」娇笑着,
双手环住他的脖子:「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我可不想一直这样偷偷摸摸的。」「快了,宝贝。」顾衍的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等她的保险金和遗产一到手,我们就去国外,买个小岛,过我们神仙般的日子。
至于这里的一切,就让它随着林静那个蠢女人一起埋进土里吧。」他们就在我的灵堂里,
在我的「面前」,肆无忌惮地亲吻,规划着他们用我的生命换来的未来。那一刻,
我感觉我的灵魂像是被投入了岩浆之中,灼热的恨意几乎要将我整个意识焚烧殆尽。
我想要尖叫,想要冲过去撕碎他们虚伪的面具!
嗡——灵堂里的水晶吊灯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嗡鸣,灯光疯狂地闪烁起来,忽明忽暗,
像是接触不良。正在亲热的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猛地分开。「怎么回事?」
白微有些惊慌地四下张望。「估计是线路老化了吧。」顾衍皱了皱眉,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他的眼神却下意识地飘向了我所在的方向。他的眼中,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恐惧和疑虑。
我立刻收敛了所有外放的情绪。我不能暴露自己。在没有足够的力量将他们一击毙命之前,
我必须忍耐。我要让他们在最放松、最得意的时候,感受到最深沉的恐惧。灯光闪烁了几下,
又恢复了正常。「你看,没事了。」顾衍强作镇定地笑了笑,
但他的额头已经渗出了细密的冷汗。白微还是有些害怕,她紧紧抓住顾衍的胳膊,
声音发颤:「衍哥,我……我总觉得这里阴森森的。林静她……她会不会……」「胡说什么!
」顾衍厉声打断了她,像是在呵斥她,又像是在给自己壮胆,「人死如灯灭!
她已经变成一捧骨灰了!别自己吓自己!」他嘴上说得强硬,却不敢再在这里多待一秒,
拉着白微匆匆离开了灵堂。他们走后,空旷的灵堂里只剩下我。我静静地立在黑暗中,
感受着体内那股因为极致愤怒而觉醒的、微弱却真实的力量。刚才的灯光闪烁,
就是我的杰作。虽然还很微弱,但这是一个开始。顾衍,白微,你们以为结束了吗?不,
这只是开始。你们的恐惧,就是我最好的养料。我会一点一点,吸食你们的恐惧,
壮大我的力量,直到有一天,我能亲手把你们拉进我所在的地狱。葬礼之后,
顾衍将我搬回了家,就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用他的话说,这是为了「睹物思人」,
向所有人展示他的深情。实际上,我知道,他是为了监视我。
他依然怀疑我的灵魂还在这盆栽里,他要将我放在眼皮子底下,确保我不会「兴风作浪」。
多么可笑。他亲手将我变成了这副模样,现在又反过来恐惧我。很快,
我的巨额保险金和所有遗产都到了顾衍的账上。他一夜之间,
从一个靠妻子养活的、郁郁不得志的建筑师,变成了身价不菲的富豪。而白微,
也迫不及待地,以「为了方便照顾悲伤的顾大哥」为由,光明正大地搬进了我和顾衍的家。
她睡我的床,用我的梳妆台,穿我没来得及穿的新衣服,甚至,她还想动我的那些盆栽。
「衍哥,这些盆栽占地方,看着也晦气,不如都处理掉吧?」一天,她依偎在顾衍怀里,
指着满园的盆景,娇声说道。顾衍正在喝着我珍藏的红酒,闻言,
他看了一眼院子里那些我视若珍宝的作品,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处理掉太可惜了。
林静的这些盆景,每一盆都价值不菲。我准备办个遗作展,还能再捞一笔。」
他的算盘打得真响,连我死后的价值都要榨取得一干二净。白微有些不高兴,
但还是顺从地点了点头。她的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客厅里的我身上。
「那……这盆呢?」她指着我,「这盆是凶器,留在这里,总觉得不吉利。」
她的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和恐惧。【4】听到白微的话,顾衍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放下酒杯,走到我面前,目光阴沉地审视着我。「这盆,谁也不能动。」
他的声音冰冷而坚决,「我要亲眼看着它。」白微不解地走过来,挽住他的胳膊:「衍哥,
为什么呀?看着它,你不会想起林静吗?不会觉得害怕吗?」「害怕?」顾衍冷笑一声,
那笑声里充满了复杂的、扭曲的情绪,「我就是要看着它。我倒想看看,她一个死人,
一株破植物,还能翻出什么浪来!」他的话语里充满了挑衅,像是在对我宣战。我知道,
他在试探我。他在用这种方式,逼我露出马脚。我选择了沉默。
我将所有的力量都收敛回核心,像一棵真正的植物一样,静默无声。我的叶片纹丝不动,
我的枝干沉静如铁。顾衍盯了我很久,似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转过身,
对白微说:「别想那么多了。也许是我想多了,不过是巧合罢了。」然而,从那天起,
他看我的眼神,变得更加频繁和警惕。而我,也开始了我的反击。我发现,
我的力量并非只能制造一些物理上的小动静。当我将意识高度集中时,
我能影响到周围的磁场,甚至……能影响到人的情绪和梦境。尤其是在夜晚,
当他们睡在我的卧室里,与我只有一墙之隔时,我的力量会变得更强。第一个崩溃的,
是白微。她开始做噩梦。每天晚上,她都会在尖叫中惊醒,脸色惨白,大汗淋漓。
「我梦到林静了!」她抱着顾衍,浑身发抖,「她就站在床边,浑身是血地看着我!
她说她好冷,要拉我一起下去陪她!」「是她!一定是她回来了!」
顾衍一开始还耐心地安慰她,说她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她自己心里有鬼。但很快,
他也开始失眠了。我将顾衍内心深处最恐惧的画面,一点一点地投射进他的潜意识里。
我让他「听」到我死前那声绝望的质问,让他「看」到我心口那个血淋淋的窟窿,让他「闻」
到那股永远也洗不掉的血腥味。他的精神状态肉眼可见地差了下去,眼窝深陷,黑眼圈浓重,
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他们开始频繁地争吵。「都怪你!非要把那盆鬼东西放在客厅里!
现在好了,我们谁都别想睡个安稳觉!」白微尖叫着,将一个枕头狠狠砸向顾衍。
顾衍一把推开她,双眼布满血丝,怒吼道:「你以为我愿意吗!不看着它,
我怕她不知道会搞出什么鬼!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人!」「我败事有余?
顾衍你别忘了,当初是谁帮你出谋划策的!是谁帮你处理掉那些证据的!没有我,
你现在说不定已经在牢里了!」「闭嘴!」「啪」的一声脆响,
顾衍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了白微的脸上。白微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而我,在客厅里,
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幕。真好。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全新开始」吗?互相猜忌,互相折磨。
别急,这还只是开胃小菜。他们的恐慌和争吵,像最顶级的肥料,滋养着我的怨恨,
让我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我不再满足于制造噩梦。一天晚上,当他们再次激烈争吵后,
白微哭着跑进了浴室。顾衍则烦躁地在客厅里踱步,最后,他走到我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