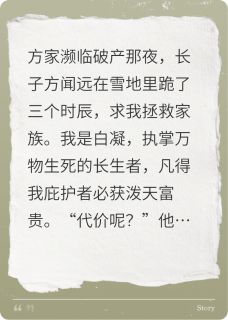
方家濒临破产那夜,长子方闻远在雪地里跪了三个时辰,求我拯救家族。我是白凝,
执掌万物生死的长生者,凡得我庇护者必获泼天富贵。“代价呢?”他声音嘶哑。
我望向阴影里那个桀骜的少年——方家幼子方长庚。后来方家成了首富,
却忘恩负义逼我离开。各大世家争相抢夺我这个“祥瑞”时,
长庚红着眼闯进我的新居:“他们都说你取走我最珍贵的东西...可我心口为什么这么空?
”我抬手抚过他胸膛,那里本该跳动着爱情,如今只剩一个空洞。1雪粒子砸在青瓦上,
像无数细小的鬼魂在叩门。我倚在窗边,看着方闻远在庭院里跪成一座冰雕。三个时辰了,
他的肩头积了厚厚一层白,远看像戴了孝。“白凝姑娘!”他的声音劈裂在寒风里,
“方家三百年的基业,不能毁在我手上!”铜炉里的炭火噼啪一响,我拨了拨香灰。
沉香的气息蛇一样缠绕在梁柱间,却盖不住这座老宅散发的腐朽味。
方家的气数尽了——若我不出手,三日之内,债主会拆了他们的祖宅,
方老爷会吊死在祠堂横梁上,女眷被卖进最下等的窑子。
这些画面在我千年的记忆里重复过太多遍,乏味得令人困倦。“让他进来。”我说。
方闻远几乎是爬进门槛的。暖阁的热气一熏,他脸上的冰壳融化,混着额角磕破的血,
蜿蜒如泪。“方家所有库房钥匙,地契,商号印信都在这里。”他推过一个紫檀木匣,
指甲乌青,“只要您坐镇方家,保我们无病无灾,富贵绵延...”“泼天富贵,
我当然给得起。”我的指尖掠过木匣,没打开。人间钱财对我不过是枯叶,风一吹就散了。
“代价呢?”我问。他喉结滚动:“我的命?”我笑了。笑声惊飞了檐下一只避寒的麻雀,
它撞在冰棱上,直直坠进雪堆。我甚至没抬一根手指。“方大公子,
”我斟了杯滚烫的茶推过去,“你的命,值几个铜板?”他捧着茶杯的手抖得厉害,
水渍溅在昂贵的云锦袍子上。像被抽了骨头的鱼,突然塌下去:“...您要什么?
”我的目光越过他,落在屏风后。一道影子钉在那里,已经很久了。“他。”我轻轻一点。
方闻远顺着我的指尖回头,脸色瞬间惨白。屏风被一脚踹开。少年抱着胳膊斜倚在朱漆柱上,
嘴角噙着冰渣似的笑:“哥,你卖祖产不够,连亲弟弟也要卖了?”方长庚。
方家最不成器的幼子,十五岁,擅斗鸡走狗,恶名冠绝金陵城。此刻他像头被激怒的幼狼,
眼睛烧着两簇暗火,直直刺向我:“妖女!你使了什么邪术蛊惑我兄长?”“长庚!
”方闻远想喝止,却被少年一把推开。他冲到我面前,带起的风掀翻了茶盏。
褐色的茶汤在青砖地上漫开,像一道狰狞的伤口。“听说你能掌万物生死?”他俯身逼视我,
呼吸几乎喷在我脸上,“那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就想掐死你?”我平静地看着他。
多年轻的生命啊,滚烫、鲁莽、带着不自知的诱惑力,像新锻出的刀锋。而我最擅长的,
就是折断这样的刀锋。“方长庚,”我念他的名字,舌尖尝到一丝铁锈般的腥甜,
“你兄长用你,换方家百年荣华。”“你休想——”“再加一条。”我打断他,
“你父亲咯血的病,三日内痊愈。”少年瞳孔骤缩。他父亲榻上缠绵的血痕,
是方家崩塌前最刺目的征兆。他攥紧的拳头咯咯作响,指节白得吓人,却终究没落下来。
“...成交。”两个字从他齿缝里碾出,带着血气。我笑了。掌心向上摊开,
一缕幽蓝的光丝从方长庚心口抽离,缠绕在我指尖,凝成一颗冰珠。他猛地捂住胸膛,
像被无形的箭射穿,踉跄一步。“你拿走了什么?”他喘息着问。“你最珍贵的东西。
”我将冰珠按入自己心口,那里千年冷寂,需要一点鲜活温度,“放心,死不了。
”2方家的崛起像一场诡谲的幻术。我住进方家祠堂后的抱厦。第一夜,
枯了半院的西府海棠突然爆出满枝花苞,沉甸甸压弯了枝条,浓香熏得守夜婆子涕泪横流。
第二天,方老爷喉头那口堵了三年的淤血咳了出来,当夜喝下两碗粳米粥。第七日,
失踪半月的运茶船队奇迹般泊回码头,船舱里不是预想中霉烂的茶叶,
而是价比黄金的南洋香料——商队竟在风暴中歪打正着漂到了香料群岛。泼天富贵,
兜头砸下。方长庚是唯一没被砸晕的人。他成了拴在我脚踝上的锁链,
被迫每日踏进这间“妖窟”。“妖女,你用的什么邪法?”他总这么开场,
把食盒“哐当”掼在桌上。方家上下视我为神明,只有他梗着脖子,像随时准备就义的囚徒。
“把屋顶的瓦掀开三寸。”我慢条斯理地搅动药盅,里面炖着方老爷的续命参汤。“什么?
”“今日申时三刻有雨,”我舀起一勺深褐药汁,“雨水落进药盅,你父亲的病根才能除尽。
”他脸色变幻,终究咬了牙,飞身蹿上房梁。申时三刻,惊雷准时炸响,
铜钱大的雨点砸进掀开的瓦缝,一滴不漏地坠入药盅。药汁沸腾般翻滚起来,异香弥漫。
他淋得透湿,盯着那碗药,像盯着一条毒蛇。“怕我下毒?”我端起药盅抿了一口。
苦涩灼烧舌尖,是活着的滋味。他一把夺过去:“方家欠你的,我还!别动我家人!
”他仰头灌药,喉结急促滚动,药汁顺着下颌淌进衣领。雨声渐密。我看着他湿漉漉的睫毛,
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另一个这样倔强的少年。那人最终化为我掌中一捧灰,风一吹就散了。
“方长庚,”我鬼使神差地开口,“我取走的东西,你真不想知道是什么?”他抹了把嘴,
药渍在唇边蹭开,像一道血痕:“只要不是良心,随你拿。”良心?我几乎笑出声。
长生者最不需要的,就是良心。但方长庚有。他嘴上骂我妖女,
却会在雷雨夜抱着剑守在我抱厦外,
因为“方家不能背逼死女人的恶名”;他偷看过我施术救回难产的母马,
第二天把一篮还沾露水的枇杷放在我窗下,
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封口费”;方老爷大宴宾客炫耀家中“祥瑞”时,
只有他注意到我蹙眉忍受着满堂浊气,一脚踹翻了炭盆:“熏死人了!都滚出去!
”火焰腾起的刹那,他挡在我身前,袖口溅上火星也浑然不觉。烟气缭绕中,
他回头瞪我:“发什么呆?不怕烧成秃毛凤凰?”那一刻,心口那颗冰珠突然发烫。
烫得我指尖一颤,杯中酒液泼湿了衣襟。危险。我对自己说。取走他爱情的时候,
我分明检查过,那颗心应该彻底冷了。可为什么...他眼中跳动的火光,
比任何法术都灼人?3方家成了江南首富。金子流水般涌来,
方闻远腰间的玉带扣从翠玉换成帝王绿,又换成整块剔透的羊脂白玉。他不再踏足抱厦,
只命人送来更贵重的礼物:南海珊瑚树,西域夜明珠,甚至一尊半人高的血玉观音。
“大公子说,请您多保佑方家子嗣繁盛。”管家谄笑着。我抚过观音慈悲的眉眼。玉质温润,
内里却沁着血丝般的纹路。像方家,表面富丽堂皇,内里早已被贪欲蛀空。
方闻远新纳的第八房小妾上月刚“失足”滑胎,
三房和五房在花园撕打时扯掉了彼此大把头发。这些消息被刻意封锁,
但血腥味瞒不过我的鼻子。方长庚来得也少了。他被推进了方家的权力中心,
跟着账房先生学看账本,陪他大哥巡视码头,甚至开始接触那些“大人物”。每次见他,
他眼底的桀骜就淡一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疲惫。像被强行磨去棱角的石头。
最后一次单独见他,是深秋。他带着一身酒气撞进来,袖口沾着可疑的胭脂。
“妖女...”他含混地喊,踉跄着扑到我的矮几前,“给我醒酒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