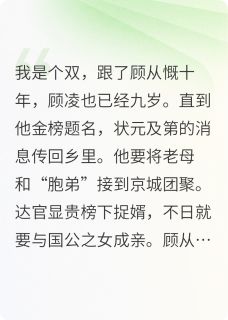
我是个双,跟了顾从慨十年,顾凌也已经九岁。直到他金榜题名,状元及第的消息传回乡里。
他要将老母和“胞弟”接到京城团聚。达官显贵榜下捉婿,不日就要与国公之女成亲。
顾从慨冷声问我:“你走不走?”我抿嘴讪笑:“我一介粗人,况且同主母男女有别,
不好再拖累你的。”顾从慨皱眉不耐:“凌儿,你也不要了?”隐在袖口中的手腕,
抖若筛糠。我点点头:“嗯。”他不欲多言,拂袖而去。深夜河边,男人将我强扯到岸上。
反手一记耳光,目眦欲裂,“你当我是死的?”1当年怀着顾凌的时候,我并不知情。
顾家遭了大祸,顾尚书狱中自裁。全府上下乱作一团,我只是个小书童,并不清楚实情。
不到一月,顾府散尽家财,人去楼空。我跟着顾从慨从京城举家迁徙回到顾母老家。
整整走了三个月。顾凌就是在路上出生。若不是机缘巧合遇见师父,我必定已经一尸两命。
真是个命大的孩子,一路奔波竟也活了下来。我看着顾从慨接过血糊糊的婴儿,
一切都来不及准备。只能随便捡了衣服裹在他身上。他看着刚出世的孩子,眼神幽深不见底。
回到江南老家,顾母对外宣称,顾凌是她遗腹子。众人不免唏嘘。顾母拍拍我的手,
一脸恳切的劝慰我:“小悦,你该明白我的苦心,从慨还年轻,以后是要成家立业的。
”顾母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敢有非分之想。顾府就算败落,也强过许多寻常百姓家。
顾从慨往后总要娶亲,有个儿子,说出去让人笑话。顾凌两岁的时候,家中银钱越用越少,
不免捉襟见肘。当年师傅为我接生,往后每年都来寻我,传授我一些医理。我粗笨愚钝,
并不能融会贯通。师傅却说不着急,慢慢来。我在惠民医馆寻到一份药工的差事,
每月二钱银子。事虽多,却能补贴家用。寒冬腊月的深夜,我冒雪回家,房内亮着烛火,
灶上竟温着一碗肉汤。热气蒸腾下,不免泪目。因这副怪异的身躯,父母弃我如草芥。
自小受的辛酸苦楚,都历历在目。掀开布帘,顾从慨在烛光下看书,顾凌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门外寒风呼啸,我却心口发热。那时觉得,日子总会越来越好。2顾凌长得冰雪可爱。
只是年纪渐大,脾气也大,顽劣不服管教。整日游悦游悦的叫我,我被他叫的烦了便不理他。
谁知抬脚就踢我。我跌在地上,吓得他哇哇大哭。我没处借力,掌心按在割草的镰刀上。
划了个口子,冒着血,难怪他吓得哭。我正想趁机教训两句,他转身就跑。镰刀上带着泥,
伤口很深。我龇牙咧嘴的去冲洗。房里传来顾凌更响亮的哭声,震耳欲聋。
这一听就是被顾从慨揍了。自那以后,顾凌不踢我了,改吐我口水。
也不知道哪来对我这么大的敌意。医馆每月有一日休沐,我手伤了几天,家中杂务没空做。
趁日头高照,洗衣劈柴,添水缸。喂鸡晒被,浇菜地,连看家狗都吃饱喝足。午后,
医馆同僚来寻我,说有急事。我忙赶回医馆,馆主语笑盈盈:“游悦,有好差事给你。
”我讷讷点头。“你去诏狱,给人瞧瞧,你谨慎细致,最合适不过。”我只是区区一个药工,
粗通些医理,若是好差事,哪里轮得到我呢。馆主发话,我不敢推辞,只能硬着头皮应下。
我提着药箱赶到诏狱。我要治的,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正发着高热说胡话。
这男孩就是刘喆。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里面的来龙去脉。当时他只告诉我,他叫刘既安。
一个狱卒给他取的名字。先太子当年卷入巫蛊之乱,发动兵变自保,兵败自缢而死。
留下唯一的血脉,就是刘既安。多年后,先皇处死诬陷先太子的一众党羽,
却并未替先太子沉冤昭雪。刘既安在狱中几经生死,却也活了下来。我这才知道,
馆主为何将这差事派给我。恩威无常,圣心难测。到底是皇室血脉,不能真死了。
也不能放出去,总得有个人担着。直到先皇驾崩前,颁罪己诏,为先太子**。
刘既安从诏狱放出来的时候无处可去。一个半大的孩子,看着我说:“我爹娘都死了。
”我看顾他这几年,心下不忍,便替他寻了医馆的活计。住在医馆执勤,平日做些粗活。
刘既安眼珠子一转,笑呵呵的应下。3我发现顾从慨进了青楼,搂着一个风月女子。回到家,
我质问他。他只沉默不语。我心里想,为什么不反驳呢?你可以说,应酬谈事,这很平常。
你为什么,不说呢。沉默震耳欲聋。我手脚发冷,低头看着身上洗的发白的布袍,
皴裂粗糙的手指,满身的苦涩药味。我有什么资格去质问他。我后来去那间青楼问过。
最便宜的茶资,也要我一年的工钱。接待的多为文人雅士,富商巨贾,消费极高。
我头脑空白,天旋地转,竟腿软站立不住。脑子里却突然蹦出来我那个可笑的存钱匣子。
我想等来年开春的时候,发了年终工钱,买两棵桃树苗种上。顾从慨喜欢吃桃子,
三年就能结果了。晚上,顾从慨叫我去洗漱,我说来了月事不方便。他皱着眉,只好作罢,
对我更是没什么话说。我知他心情不快,也自知身上污秽,并不敢睡在他身边。
我打了地铺躺下,望着窗外月光睡不着。想这些年,怎么活的浑浑噩噩像个笑话。书上写,
人不可自轻自贱。我努力想活的有尊严,活的像个正常人。可是,我做不到。这些年,
我跟顾从慨,过得与平常夫妻无异。有了孩子,有了亲近,有了自以为的“爱”。
让我恍惚以为,老天待我不薄。我懦弱卑怯,浑身打着冷颤,不敢再细想下去。
日子平淡如水的过着。医馆中偶有妓坊的女子来看病,大夫们不愿纡尊降贵看这种脏病,
便都推给我。我看的多了,常听她们闲话家常。“天下男人都一样。”“入土了才老实。
”“什么一往情深,都是狗屁。”妓子突然顿住,娇滴滴放轻了语气:“游大夫,
我不是说你啊,你是好人。”我笑笑,其实很认可她的话,“你说得对,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刘既安提着药从内堂出来,狠狠拍在柜台上。妓子吓了一跳,幽怨道:“小帅哥,
脾气这么大做什么?”我将注意事项写在纸上拿给她。临走前,
妓子娇娇柔柔抛了个媚眼:“游大夫,有空来玩啊,我给你半价。”刘既安脸色更难看了。
我见他身量隐隐都快超过自己,心下了然:“你喜欢她?”刘既安看向我,脸色更沉,
一声不吭,转身走了。我心觉好笑,小兔崽子,谁不是年少懵懂过来的,
被我说一句还不理人了。4“你顾哥,可是青楼常客。”刘既安语出惊人,
吓得我切草药差点切到手指。过年的时候,我见刘既安没处可去,
便将他带回家一道过了除夕,他也算认识顾从慨。我心下如擂鼓,
只知慌忙掩盖:“你怕是认错了人,我没听过这回事。”刘既安挑眉道:“你不知?
”我哪里不知道呢?我俩都分房多年。刘既安幽幽出声,
眼睛像只狡黠的狐狸:“你当心得病。”隐私被人戳破,我耳朵通红。
也不知他什么时候看出来,我跟顾从慨的关系,慌忙辩解:“你小孩子家,别乱说。
”刘既安脸上有些疑惑的看着我,话在嘴边却没往下说。晚上,
顾母说顾从慨今晚跟友人小聚,不回来吃饭了。我见怪不怪,谁知夜里刘既安来找我。
刘既安拽我手,“跟我来。”我刚洗了身子,头发都没擦干,胡乱套了一件袍子。“等等,
去哪呀,太晚了,我还要看孩子。”夜色朦胧,刘既安咧着嘴笑,攥着我手腕的指腹,
粗粝滚烫,“游悦,我还能害你啊。”我不是傻子,我可能大概知道他要带我去哪。
我手臂隐隐发抖,脑中一片乱麻。被带到房间里,听见隔壁颠鸾倒凤中夹杂着熟悉的低喘声,
我的意识才渐渐回笼。墙上还有可视小孔,用来满足低俗的恶趣味。我好像被附身一般,
不由自主凑到小孔前。像个偷窥狂,想要一探究竟。两具交叠的身影,热浪翻滚,红绡帐暖。
云歇雨霁,我后退几步。有些昏昏沉沉,一时都不知道今夕是何年。我看向刘既安,
他眼中带着得逞后的笑意。好像在说,你看吧,我告诉你,你还不信。真像个小孩子,
我无奈的想。我不合时宜的问他:“你哪来的钱,住一晚很贵吧?
”刘既安像个饱含阅历的年长者:“你多操心操心自己,你把日子过明白了吗?
”我过不明白,大家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我被小辈这样说教,竟也不觉得羞赧,
只觉深深的无力。当夜也没心力去想其他,身心俱疲之下,竟在房里昏睡了一晚。
我一大早回家,看见顾从慨竟比我先回来。原以为他要质问我为何夜不归宿。
没想竟是一个字也没提。只淡淡看了我一眼。我心中有鬼,仿佛做了亏心事一般,
竟也有些怕看他的眼睛。脑中跳出昨日翻云覆雨的画面,连忙避开他去换衣服了。
5顾从慨自小饱读诗书,一路考科举做了举人。而后便是进京赶考,参加来年二月的春闱。
那年他才二十三岁。山高路远,我牵着顾凌送他。许是有段日子见不到,气氛烘到这里。
顾从慨看着我,难得露出些温情,深情缱绻依依不舍的样子:“你等我。”我点点头,
“我等你。”等你什么呢?等你回来娶我吗?你走向更好的未来,我却还在泥沼中徘徊。
顾从慨高中状元,风光归故里。能将我一起带回京城,已经是给我脸面了。
谁知我烂泥扶不上墙,在他眼中,我着实是个“抛妻弃子”的负心汉。顾从慨拂袖而去,
带着顾母和“胞弟”回京城安置,婚期将近。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我这个人,生来便是错误。这多活的二十多年,已经是老天眷顾。空荡荡不知来处,
孤零零难觅归途。夜色静谧,寒冬腊月,湖水冷如冰。我却感受不到寒意。水漫过肩头,
眼前白茫茫一片,仿佛是奔向了温暖明媚的桃花源。我听见有人在喊叫,却并不在意。
加紧脚步,只求速死。一阵大力将我拉回岸边。一记耳光将我打醒。
眼前是刘既安目眦欲裂的慌乱,大骂道:“你当我是死的?!”“游悦!我陪你玩这么多年,
你当我是死的!”6我被冻的说不出话,整个身子如癫痫一般抖若筛糠。
刘既安把我扛在肩上,带我回家。我脑子转的很慢,我好累。他烧热水给我洗澡,
为我煮姜汤,衣不解带照顾我。我有些茫然,他凑过来吻我。我很惊愕,抗拒他的碰触。
他用力捏着我下颚,不许我转头。“游悦,我救了你,你就是我的。”这样霸道的话,
我竟无法反驳。夜色深处,刘既安笑出声来:“我当顾从慨男女不忌,原来是有这妙处,
游悦,我稀罕死你了。”我脸烫的能滴出血来,竟有种背着丈夫偷腥的羞耻感。心下苍茫,
又觉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还在乎这些做什么。刘既安趴在我腿上埋怨,说我旷职,
医馆没了我乱成一团。“平日里你大包大揽,都自己干了去,养出一帮废物,
被主治骂的狗血淋头。”我知道他拿话哄我,离了谁,都不会乱。心里却是很受用的。
我进医馆将近八年,上头给我配几个小徒弟帮忙,俨然也算老师傅了。我却不敢随意差遣,
生怕馆主嫌我懒怠不上心。被他恨铁不成钢的骂:“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难道一辈子做药工?”我尴尬的笑笑,辜负了他的期望,心中忐忑了一阵。
我确实是个胸无大志人。如今鬼门关前走过一遭,只觉功名利禄于我如浮云。
更是将破罐破摔贯彻到底,竟有种前所未有的安然惬意。我回医馆点卯,
馆主似笑非笑看我:“给你工钱涨到每月一两银子,年底双薪,滚前厅看诊去。
”我还想摆烂来着,怎么赶鸭子上架呢?我看看刘既安,他上后院帮忙去了。
7师父他云游天下,医术了得。我平日记了不少疑难杂症,等他每年来寻我,便向他请教。
“怎么都是些妇科问题?”师傅吃着烧鸡,喝着桃花酒。“你扎女人堆里去了?
”“师傅你都能帮我剖腹取子,自然是妇科圣手。我深知妇女不易,为妇难,为母难,
想着能治一个是一个。”世上鲜少有女性医者,少有能切身体会妇人之难,孕育之苦,
生产之痛。当年剖腹取子,也是师父无奈之举。我知当日凶险万分,术后缝合,
我饮尽麻沸散。生生将床单抓烂,痛晕过去。术后两月,出血不止。全靠师傅的药吊命,
让我挺了过来。师父说,剖腹取子,我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师傅问我:“孩子他爹呢?
”我无奈道:“我总不能阻止他奔向更好的前程吧。”师傅怒骂:“没出息的东西。
”我缩着脖子怕他打我。师傅又看看刘既安,他如今已搬来与我同住,出入都跟自己家一样。
“这小子又是怎么回事?”我支支吾吾不知怎么解释,又不想骗师傅。刘既安施施然走过来,
双膝下跪,以头磕地。“晚辈拜见大师,游悦同我讲过您对他有救命之恩,授业之恩,
晚辈谢过大师。”“你……”“我是他男人。”师傅显然愣住了,忽的哈哈大笑起来,
揶揄我:“你倒是个有能耐的。”我羞的无地自容,简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8如今我也是小有名气的妇科大夫了,年底还有十多两银钱结余。每日与刘既安同进同出,
他身量比我高出一个头,力气大的吓人。我轻易不敢招惹他。他还在医馆做杂役,
我问他往后打算。刘既安叼着柴杆子漫不经心,“我给你打杂,你养我一辈子。
”我问他:“你不想考个功名?或者学门手艺?”我像个老父亲一般,为他盘算。
刘既安挑眉笑笑,“怎么,我去考个状元,娶个公主回来?”我知他是拿话刺我,并不在意。
“还是你不想养我一辈子?”刘既安将我抱坐在他腿上。我一惊,四下看,赶忙要起身。
他力大无穷,我动弹不得,急得要出汗。他还在我耳边添油加醋:“慌什么?医馆上下,
谁不知道我俩睡一条被子。”我羞的耳朵通红,这知道是一回事,看见又是一回事。
刘既安捏着我下颚,强迫我看着他眼睛。又重复一遍:“我给你打杂,你养我一辈子。
”我从来不信什么一辈子,一辈子太长,我不敢奢望。“……”我告诉他:“你不弃我,
我养你一辈子。”9三年,京城从未有消息传来,想必顾从慨早已娶妻生子。顾凌跟着他,
日子应当是不差的。惠民医馆被当地府衙收编,一跃成为官办性质的医馆。医馆扩建,
人员扩编,一下子多了许多共事同僚。我曾想,就这样把日子过下去。却没料到,
命运从未放过我。一场瘟疫席卷而来,死伤无数。人命如草芥。
我费尽千辛万苦与师傅研制出药方。本以为能结束这场人间炼狱,
却被卷入更加万劫不复的深渊。药方是被谁呈上去的,我不得而知。我知道药方能治瘟疫,
我只希望朝廷尽快拨款下来。救人要紧,时间就是性命。三天三夜,不得安眠。
我终于支撑不住,昏倒在地。醒来便看见刘既安在收拾包袱。我将手抵在额上,头痛欲裂,
有气无力问他:“既安,你做什么?”刘既安见我醒来,跑过来亲了我一下,
手中不停:“我没空跟你解释,我们得赶紧走,离开这个鬼地方。”“啊?”我晕头转向,
“还要等朝廷拨款下来救命呢。”“救个屁,你都自身难保了。”刘既安速度飞快,
胡乱给我套了件衣服,单手扛起我,将我丢到马车上。“等等——”我扒在车门上,
“我要回医馆去,不然那些人都白死了。”“游悦!”刘既安将包袱扔到我怀里,怒目瞪我。
他近些年,收敛了脾气,很少有这样凶我的时候。“我不会害你,
我的暗卫会护送你去前面的镇上。”“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就去跟你汇合,
往后你想去哪去哪。”“跟你游山玩水浪迹天涯,你再给我生个大胖娃娃。
”刘既安说的很快,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车夫扬鞭急赶,马车呼啸而去。我脑子混沌,
来不及消化他的话。出了什么大事?他哪来的暗卫?他去做什么?我要去哪?医馆怎么办?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车夫不让我走,我们在镇上等了三天。没等来刘既安,
却等来了锦衣卫的人马。10我没想到那是我跟刘既安的最后一面。
我跟只属于我的刘既安的最后一面。我被押解进京,马车一路奔驰。
佛有十万火急的事在前面等着我送去项上人头。刘既安给我收拾的包袱被他们拿走。
我被一路送进宫中,伏跪在乾清宫能印出人影的地砖上。手脚僵硬,心口发麻。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韩溪亭,当朝首辅,太子太师。圣上得了瘟疫,
而我就是那个进献药方的人。乾清宫中跪了一地的人,太医太监宫女。
我进来时看见惠民医馆新任的提领,同样跪在乌泱泱的人群里。押我进来的锦衣卫,提醒我,
“这是首辅大人。”我从未见过这种阵仗,怕失了礼数,小命不保,忙磕头请安,
“草民拜见首辅大人。”韩溪亭穿绯色官袍,大马金刀坐在太师椅中。我不懂其中门道,
只觉这首辅大人竟比天子还威严。韩溪亭沉声:“还不快给皇上诊治。”我冷汗涔涔,
手忙脚乱滚到龙榻边探脉。圣上已昏睡不醒。与江南瘟疫症状如出一辙。我如实禀报,
药方对症,不日就能痊愈。我自知,如今小命攥在这韩太师手里。乾清宫灯火通明,
众人皆不敢掉以轻心。太医院按方煎了药给圣上服下。我也得侍奉在侧,禁在宫中不得出。
服药三日,圣上每况愈下。第四日的午夜,乾清宫传出哀鸣。圣上殡天。登基不过六载,
后宫无所出,帝位后继无人。我被押进诏狱严刑拷打。自进宫那一刻起,我就知道。
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我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刑官问我:“想死吗?”我想。
可是我还没再看一眼刘既安,也不知他怎么样了。我还想见见顾凌。也想见见顾从慨。
我不想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死了。我不甘心。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死了。瘟疫远在江南,
怎么圣上就得了。症状一模一样,为什么药方不起效。没人告诉我。
11刑官问我:“你认不认罪?”我不是傻子,谋害圣上,这诛九族的罪我怎么敢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