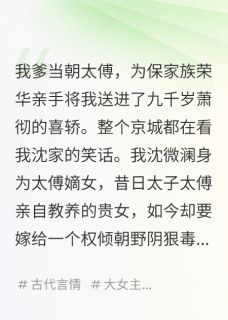
我爹当朝太傅,为保家族荣华亲手将我送进了九千岁萧彻的喜轿。
整个京城都在看我沈家的笑话。
我沈微澜身为太傅嫡女,昔日太子太傅亲自教养的贵女,如今却要嫁给一个权倾朝野阴狠毒辣的太监冲喜。
传闻那九千岁萧彻年近四十暴戾恣睢,因早年受宫刑落下病根已经命不久矣。
我嫁过去就是守活寡,等他一死便要被活活殉葬。
我的未婚夫新科状元郎,第一时间派人送来了退婚书,生怕和我沈家沾上一点关系。
而那高坐龙椅的小皇帝听闻此事,竟抚掌大笑对满朝文武说:“沈家有女堪为忠烈典范,当赏!”
赏我一座贞节牌坊,在我还没死的时候。
我坐在摇晃的花轿里,听着外面若有似无的嘲笑声心中一片死寂。
直到花轿落地,一只冰冷的手掀开了轿帘——轿外站着的不是喜婆,而是一个身着飞鱼服面容冷峻的男人。
他身后是黑压压一片的东厂番役。
他俯身声音没有一丝温度:“夫人,千岁爷等您很久了。”
那一刻我才知道我嫁的不是人是活生生的阎罗王。
而我的夫家是人人闻之色变的东厂。
花轿停在了九千岁府邸的门口。
没有宾客没有喧闹,门口两只巨大的石狮子在夕阳下投出狰狞的影子,朱红色的大门上连个喜字都没贴。
这里不像嫁娶,更像是……押送。
“沈**,请吧。”
领头的番役面无表情地做了个“请”的手势,语气里没有半分尊敬只有公事公办的冷漠。
我提着繁复的裙摆,一步步踏上石阶。
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坟墓上。
我爹沈从安在我临行前跪在我面前老泪纵横。
“微澜,是爹对不住你!但凡有半点法子爹也舍不得你……”
“萧彻掌控东厂权势滔天,连陛下都得让他三分。前几日你哥哥在朝堂上不过是与他政见不合,就被他寻了个由头打入诏狱,若我们不答应这门婚事整个沈家……都要完了啊!”
“你放心爹已经打听过了,那萧彻沉疴已久郎中说他熬不过这个冬天。你且忍耐几个月等他一死,爹立刻想办法把你接出来为你寻一门好亲事……”
我当时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原来我苦读的诗书、我引以为傲的才情和我谨记于心的家族荣耀,在绝对的权势面前一文不值。
我只是个可以被牺牲的筹码。
千岁府内更是死气沉沉。
偌大的庭院见不到几个下人,只有佩刀的番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眼神如鹰隼般锐利。
我被直接带到了一间卧房。
房间很大布置得却极为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
没有丝毫新婚的喜气,只有一股浓重刺鼻的药味混杂着檀香,闻得人头晕脑胀。
“千岁爷身体不适今晚就不见你了。你在此处歇下记住,没有传召不得踏出房门半步。”
一个年长的嬷嬷冷冰冰地交代完,便带着所有侍女退了出去将门从外面锁上了。
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红色的嫁衣像一个巨大的讽刺,沉甸甸地压在我身上。
我没有哭。
眼泪是这世上最无用的东西。
我只是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夜幕。
京城的万家灯火仿佛都与我隔绝了。
这一夜,我枯坐到天明。
没有想象中的折辱,没有传说中那个喜怒无常的太监甚至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若不是空气中那股不散的药味,我几乎要以为这是一场荒唐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