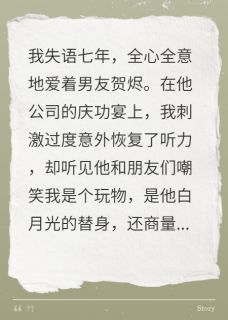
我失语七年,全心全意地爱着男友贺烬。在他公司的庆功宴上,我**过度意外恢复了听力,
却听见他和朋友们嘲笑我是个玩物,是他白月光的替身,
还商量着等她回来就弄死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我攥紧口袋里刚拿到的孕检报告,冷笑一声。
他不知道,能听见一切的我,即将让他为这七年的欺骗付出血的代价!1我踮着脚尖,
将最后一块深蓝色的乐高按进墙里时,贺烬刚好推门进来。「温禾。」我回头,
眼中亮晶晶的。今天是贺烬公司A轮融资成功的庆功宴,也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七年。
我用了一个月,拼了这面三米高的星空乐高墙,作为给他的礼物。我快速地在手机上打字,
把屏幕转向他:「喜欢吗?」他站在我面前,目光却没有落在那面墙上,而是穿过我,
投向了身后巨大的落地窗。他的那帮狐朋狗友,正簇拥着一个穿着高定礼服的女人走进来。
贺烬的嘴唇动了动,吐出的,却不是我的名字。「简吟,喜欢吗?」那两个字,
像淬了冰的钢针,扎进我耳朵里。七年来,因为**过大患上的心因性失语症,
我的世界一片寂静。医生说我或许一辈子都无法再开口说话。可就在刚刚,我给他发消息,
激动地问他庆功宴之后去哪里庆祝时,我的耳朵里,突然嗡的一声,世界鲜活了。
我听见了酒杯碰撞声,听见了他朋友们轻浮的笑声。然后,就是那句:「简吟,喜欢吗?」
被他那帮兄弟簇拥着的女人,是盛华集团的千金,简吟。也是七年前,贺烬跌入谷底时,
第一个甩了他的初恋女友。身后,刺耳的议论像是苍蝇,嗡嗡地往我耳朵里钻。「**,
烬哥**下血本啊!这墙得几十个W吧?简**才刚回国,他就准备了这么大惊喜?」
「一个破哑巴感动的眼都红了,真以为是给她的?笑死。」一个穿着花衬衫的男人,
吊儿郎当地摇着酒杯,撞了下贺烬的肩膀:「烬哥,正宫娘娘都回来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个小哑巴发落了?」贺烬抄着口袋,瞥了我一眼,
那眼神像在看一件摆旧了的家具。「急什么?」他漫不经心地说,「等我跟吟吟订了婚再说。
」「行啊你,是真对这哑巴玩出感情了?」「感情?」另一个声音夸张地大笑起来,
「你们懂个屁!这叫岗前培训!毕竟是盛华的千金,烬哥不得先拿个人练练手,
把十八般武艺都解锁了,才好去伺候咱们的简大**啊!」众人爆发出更刺耳的哄笑,
那一道道黏腻的目光,像一条条毒蛇,爬满我的后背。「说真的,
上次哥几个喝多了在门口听墙角,这哑巴虽然不叫唤,但那动静,嘖嘖,
比会所里的头牌都会扭!不愧是破产老板的女儿,骨子里的浪劲儿是藏不住的!」
「还是烬哥会玩!养个哑巴在身边,什么丑事都传不出去!
她爹温启明要是知道他捧在手心的独生女现在这么****,怕不是要从坟里爬出来!」
冷气,顺着我的脚底板,一路窜上天灵盖。贺烬顺手将外套脱下,披在我轻颤的肩膀上。
他低头时,气息温热,动作一如既往地温柔,仿佛刚才那些刺骨的话,都只是我的幻觉。
「怕她伤心啊?」有人意味深长地瞟着我,「我看这小哑-巴对你死心塌地的,
万一真想不开了怎么办?」「伤心?」贺烬嗤笑一声,捏了捏我的后颈,像在逗弄一只宠物。
「她除了缠着我,还能去哪儿?」「那也是,一个欠着几千万外债的哑巴,
也就烬哥你大发慈悲肯收留了。」「当年要不是她那张脸跟简**有三分像,
烬哥当年怎么会从那群追债的手里把她捞出来?」「烬哥,下周就去简家提亲了吧?恭喜啊!
终于得偿所愿,要抱得美人归了!」我低着头,指甲死死地陷进掌心的肉里,
胸口像是被人用钝器一下下地砸着,喘不过气。这七年,多少个夜晚,
他反复摩挲着我的眉眼,夸我长得干净。所有人都说贺家三公子薄情寡义,
玩过的女人比衣服还多,唯独我天真地以为,他把仅存的耐心和温柔都给了我。闹了半天,
原来都是因为我这张脸……“和简吟有三分像”,还能“先拿她练熟,伺候好千金”。
整整七年,两千五百多个日夜的陪伴,从他被家族排挤到如今融资成功,
不过是一场明码标价的……岗前培训。彻头彻尾的,天大的笑话。我腿一软,眼前瞬间发黑。
贺烬扶住了我,眉头紧锁,似乎在怪我扫了他的兴。他忘了,今天也是我们七周年的纪念日。
乐高墙的星光洒在他肩头,我下意识地想替他整理一下衣领,手却在半空僵住。何必呢。
从今往后,他西装上的每一丝褶皱,都会有简吟来抚平。2我在手机上敲了两个字:「累了」
,然后挣开他的手,踉踉跄跄地逃回了他给我安排的、别墅最角落的那间佣人房。
门关上的瞬间,我背靠着门板滑落在地,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怎么都止不住。这七年,我不求名分,不奢望未来,只求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屋檐。
我以为我藏好的那点卑微爱意,他多少能感受到一些。原来在他和那帮朋友眼里,
那份小心翼翼的喜欢,就是「自甘**」。我颤抖着手,开始收拾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东西。
梳妆台上只有一个廉价的发卡,是贺烬某次开完会,顺手从前台拿回来给我的,
我却宝贝了这么久。除此之外,我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
抱着用一个购物袋装好的全部家当,我在泪水中沉沉睡去。我梦见我爸还在,
那年公司还没破产,他站在明亮的落地窗前,笑着刮我的鼻子,叫我「禾禾」。「砰——!」
刺耳的摔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慌忙抹掉脸上的泪,抬头看向门口,瞳孔狠狠一缩。
简吟穿着一身火红色的连衣裙,抱臂站在那儿,居高临下地睥睨着我,
嘴角的笑容像是淬了毒。「哟,好久不见啊,温禾。」我仓促地从床上站起来,
几乎是本能地想对她低头。她却突然掩着嘴笑了起来,声音又尖又利:「当初在学校里,
你不是挺能耐的吗?事事压我一头。怎么,现在变哑巴了?」她一步步朝我走来,
眼神里的轻蔑变成了刀子。「听说,你现在很会伺/候/人?连贺烬的床都爬上去了?」
我浑身发抖,一步步后退,手腕却被她死死抓住。「就算你哑了我也要告诉你,」
她凑到我耳边,吐出的气息阴冷又残忍,「你这辈子,都贱得让我恶心。」「你信不信,
我现在只要一句话,贺烬连你的命都会拿来给我赔罪。」刚好给我送药的阿姨看到这一幕,
吓得差点跪下:「简**!温**她……她身子不舒服……」「滚开!」简吟一脚踹开阿姨,
猛地抓住我的头发往后一扯。我头皮剧痛,整个人向后栽去,后腰重重地磕在了桌角上。
一股尖锐的剧痛瞬间从我小腹炸开,随即,
有什么温热的液体顺着我大腿内侧涌了出来……我的孩子!
昨天的孕检报告还没来得及给他看……我只是有了先兆流产的迹象……我瘫软在地,
绝望地捂住肚子,黏腻的温热液体在身下迅速蔓延。「啊——」
一个破碎的音节从我喉咙里挤出,七年来第一次发出声音,却是如此痛苦的哀鸣。
贺烬闻声匆匆赶来,看到我身下那摊刺目的红,神色一变。
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攥住他的裤脚,用尽全力,
从喉咙里挤出沙哑又模糊的字句:「……孩……子……救……」贺烬眉头紧锁:「怎么回事?
」简吟却突然娇笑一声,指着地上的血:「阿烬你看!温禾为了给你助兴,玩得多花啊。
这颜色,真像抹在地上的朱砂。她可真是用心良苦,知道你喜欢这种调调!」
贺烬蹙着的眉头松开了,他看我的眼神,只剩下一片冰冷的厌恶。我拼命摇头,
泪水混着冷汗往下掉,腹部的绞痛快要将我撕裂。送药的阿姨哭着爬过来:「贺先生!
温**她……她可能要小产了!您快叫救护车救救她吧!再晚一点,一尸两命啊!」「够了。
」贺烬的耐心彻底耗尽,他一脚踢开我的手,「简吟说的没错,这种玩笑开过头了,
就显得廉价又恶心。」「阿烬……」简吟轻笑着挽住他的胳膊,「我看她这么喜欢红色,
不如……来人,去酒窖里拿最烈的威士忌过来。既然她这么脏,不如帮她好好洗一洗,
消消毒。」3贺烬一眼都没再看我,搂着简吟转身就走。两个身材壮硕的保镖走了进来,
一左一右把我架起来,我腿间的血还在往下淌。他们面无表情地捏开我的下巴,
冰冷的酒液混着玻璃碴的碎响,直接往我嘴里灌。辛辣的液体灼烧着我的食道,
我疼得眼前阵阵发黑,腹部的绞痛也愈发剧烈。保镖们的声音毫无温度:「简**吩咐了,
这瓶酒不喝完,不许停。否则,我们俩都得滚蛋!」喉咙里只能发出痛苦的呜咽,
我哭喊着求饶,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喝快点,我们也好交差!」一个保镖揪住我的头发,
强迫我仰头。他们将那瓶烈酒尽数灌进我的身体里,每一次吞咽,都像是在吞刀子。
我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血混着酒液,浸透了我的裙摆。一双精美的红色高跟鞋停在我面前。
简吟的脸在我模糊的视线上方晃动,她的声音带着胜利者的**:「温禾,你这种**,
连怀上的种都是脏的,我就发发善心,替你清理门户了。」她蹲下身,凑到我耳边,
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见。「你知不知道,七年前,你爸的公司是我爸做局搞垮的?
他从天台跳下来的时候,就跟你现在一样,也是这么一滩烂泥……真是可怜啊。」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炸开,像是被人用重锤狠狠砸了一下。
我听见远处传来医疗阿姨撕心裂肺的呼喊:「快来人!这里真的出人命了!」
我甚至还听见了贺烬隐约的一声「温禾」,不知道是我的幻听,
还是迟来的、毫无意义的讽刺。当我再次睁开眼,消毒水的味道刺得我鼻子发酸。
医生惋惜地告诉我,孩子没了,还说因为失血过多和酒精**,
我以后……可能再也没有做母亲的资格了。也好。一个不被期待的孩子,来到这个世上,
除了受苦,还能有什么呢?至于我,也该滚了。我在医院躺了三天,贺烬一次也没出现。
唯一来看过我的那个医疗阿姨,偷偷告诉我,贺烬正忙着筹备和简吟的订婚仪式,
陪着简吟满世界地挑选戒指和礼服,根本没回过别墅。我静静地听着,
指尖无意识地在床单上划着。这天,两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推门进来,态度还算客气,
但眼神里的轻蔑毫不掩饰:「温**,简**在顶楼设了宴,请您务必过去一趟。」
我本不想去。可听到他们说「简**专门定制了铂金餐具」时,我的指尖猛地蜷缩起来。
贺烬对铂金有极罕见且严重的过敏反应,一旦接触,轻则全身起红疹,呼吸困难,
重则……会直接休克。我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居然……还放不下他。我真贱。
到了顶楼的旋转餐厅,满座衣着光鲜的宾客看到我,纷纷露出看好戏的神情。
「那不是温家的那个哑巴女儿吗?」「嘘!早就不是什么温家了,她爸都成一撮灰了!」
「听说她欠了好多钱,被贺三少包了七年,圈子里谁不知道啊?」「我要是她,
被简吟正主找上门,早就识趣地滚蛋了,哪还有脸出来?」我面无表情地穿过人群,
走到贺烬那一桌。他抬头看我,眉头不悦地拧在一起:「你怎么来了?
身体不好就在医院待着,乱跑什么?」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他咳了一声,
语气里的不耐烦像针一样扎人:「以后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简吟说你是因为她回来了,
所以故意装病想引起我的注意。温禾,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玩这种游戏。」装病?
我差点要笑出声来。原来直到现在,他还以为我那天是在演戏。原来他不知道,
我失去了一个孩子,也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简吟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我死死攥着袖口,强忍着涌上喉咙的腥甜,在手机上慢慢打出一行字。「我来是想提醒你,
今晚的餐具是铂金的,别用。」他看到那行字,眼神似乎闪动了一下,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像是打发一只烦人的苍蝇:「嗯,知道了。」我嘴唇动了动,
又在手机上打了几个字:「我先走了。」刚走到露台边,简吟就踩着高跟鞋拦住了我。
她双臂环胸,下巴扬得像只斗胜的孔雀:「你看,就算你给他暖了七年的床又怎么样?
他心里,从始至终就只装得下我一个人。」我懒得理她,转身想走。
她眼中闪过一丝被无视的恼怒,突然伸手狠狠拽住我的手腕!我猝不及防,被她用力一扯,
在她夸张的尖叫声中,和她一起摔进了旁边的泳池里。4冰冷的水瞬间灌入我的口鼻,
身体刚刚恢复一点,此刻根本使不上力气。就在我意识模糊,以为自己就要这么死掉的时候,
一道人影飞快地跳了下来。是贺烬!我心里燃起一丝可笑的希望。可下一秒,
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径直游向了正在水中扑腾的简吟,一把将她拦腰抱起。
他抱着他失而复得的宝贝,转过头,用能杀死人的目光死死瞪着还在水里下沉的我,
怒吼出声:「温禾!你想害死简吟吗?!」他忘了,我刚经历小产。更忘了,此刻,
我还沉在水里。窒息感吞没了所有知觉,我缓缓闭上眼,任由身体坠入冰冷的黑暗。
就这样吧。反正,这世上,再也没有人期待我活着了。
我最终还是被餐厅的工作人员捞了上来。再次醒来时,我正躺在贺烬私人医院的顶级病房里,
檀香的气味萦绕鼻尖。他坐在床边,脸色是从未有过的阴沉和冷漠。「幸好简吟没事。」
他的声音又冷又硬,每一个字都像冰锥砸在我心上。「温禾,你不该这么恶毒。
去给简吟道歉。」我没说话,没解释,只是麻木地垂下眼帘,
从喉咙里挤出两个沙哑的音节:「对……起……」站在病房中央的简吟,
脸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嘴角却勾起一抹得意的、残忍的弧度。「贺三少,
她的道歉这么没诚意,我可受不起。」贺烬皱了皱眉:「那你想怎么样?」
简吟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像是看一个死物:「我被推下水,受了风寒,
从小落下的偏头痛又犯了。我听说,国外刚研制出一种速效美容针,对偏头痛也有奇效,
只是还没上市,副作用不明……」她歪着头,笑得天真又恶毒,
「不如……让温**替我试试?」贺烬的脸色终于变了。那种来路不明的针剂,
就跟赌命一样。打下去,谁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看到他犹豫,简吟的眼眶立刻就红了,
声音也带上了哭腔:「阿烬,我的头好痛……你是不是也不要我了?
你是不是要眼睁睁看着我疼死?」
贺烬的目光在我惨白的脸上和简吟楚楚可怜的脸上来回徘徊,最终,
他缓缓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温禾,去吧。」
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就当是……还我这七年收留你的恩情。你放心,
我会找最好的医生守着,绝对不会让你死的。」我看着他,忽然笑了。七年恩情?好,
我還你。我被带到一个密闭的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