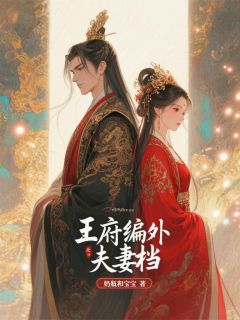
永平郡的告示栏前,人头攒动。一张崭新的朱砂官府告示贴在最显眼的位置,墨迹淋漓,
力透纸背:“为敦睦民风,倡行伦常,永平郡王府特设‘敦睦录’编外户籍记录官十位,
兼评‘郡中模范夫妻’,岁赐纹银百两,米二十石,并赐‘敦睦之家’牌匾。
凡本郡良籍夫妇,婚契三载以上,无口舌争讼之扰,有邻里称颂之和者,
皆可至郡衙户房报名应选。当选者,需按月呈交夫妇日常和睦相处之详录,
以资教化……”人群嗡嗡议论着那诱人的百两岁赐和二十石米粮。
苏晚瘦削的身影挤在人群中,目光死死锁着那“岁赐纹银百两”几个字,指尖冰凉。
百两银子!有了这笔钱,加上她日夜操劳攒下的微薄积蓄,或许就能填上那个巨大的窟窿,
保住父亲临终前紧紧攥着她手叮嘱“万万不能丢”的苏家小酒坊!官府新划的官道,
正巧要从她家那间传了三代、飘着醇厚酒香的小院穿过。报名?
她一个被夫家休弃、带着个半大丫头的妇人,连“夫妇”这一条都沾不上边!
苏晚心头刚燃起的一点火星,瞬间被冰冷的现实浇灭。“啧,这银子可不好拿,
”旁边一个摇着蒲扇的老汉咂嘴,“按月交那劳什子‘和睦详录’?
夫妻关起门来是拌嘴还是打架,谁乐意写出来给官老爷们看?还得写得花团锦簇,
这不是活受罪嘛!”活受罪?苏晚黯淡的眸子骤然亮了一下。只要能保住酒坊,
什么罪她不能受?就在此时,一个穿着半旧靛蓝布袍的高大身影,如同融入阴影的墨,
悄无声息地靠近了告示栏的另一角。男人面容轮廓深刻,眉骨处一道浅疤隐入鬓角,
眼神沉静得像深潭古井,看似随意地扫过告示,
目光却在“编外户籍记录官”和“岁赐”上停顿了微不可察的一瞬。
他周身有种难以言喻的紧绷感,仿佛一张拉满的弓,随时警惕着四周。
几个穿着短打、眼神精悍的汉子在不远处巷口逡巡张望,目光几次掠过他的背影。
男人眉头几不可察地一蹙,迅速收回目光,转身欲走,脚步却微微一顿。
他敏锐地捕捉到旁边那个身形单薄、面色苍白的年轻妇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决绝光芒。
郡衙户房那间散发着陈年墨汁和灰尘味道的偏室里,主簿捻着稀疏的山羊胡,
三角眼在苏晚和那个自称“沈砚”的男人之间来回扫视。“婚书?”主簿拖长了调子。
苏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沈砚却神色自若地从怀中掏出一份微微发黄、但格式规整的婚契文书,轻轻放在案上。
纸张边缘磨损,印泥颜色古旧,竟像是有些年头了。苏晚飞快地瞥了一眼,心头惊疑不定。
“哦?永宁府青石镇人士?婚配……五载有余?”主簿仔细查验着婚书上的官印和保长签押,
竟似无懈可击。他狐疑地打量眼前这对“夫妻”:女子荆钗布裙,难掩清秀,
眉眼间却有股子韧劲;男子沉默寡言,身姿挺拔如松,虽穿着寻常布衣,
那通身的气度却不像普通乡民。两人站在一起,既无新婚的黏腻,也无怨偶的怨怼,
只余一种奇异的……疏离的平静。“既是夫妇,为何女方户籍仍在原籍?”主簿敲了敲桌子。
沈砚的声音低沉平稳,听不出情绪:“内子家中尚有幼妹需人照料,兼之经营一处祖传酒坊,
故此前并未随迁。此次听闻郡王府仁政,为求‘敦睦’之名以光耀门楣,方一同前来应选。
”他微微侧身,目光落在苏晚身上,那眼神平静无波,却奇异地让苏晚慌乱的心定了定。
“酒坊?”主簿挑眉,看向苏晚。苏晚连忙垂首,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谦恭:“回大人话,
是家传的一点小营生,名唤‘苏记醴泉’。”主簿沉吟片刻,
又问了几个诸如“夫妻如何相识”、“平日如何相处”的例行问题。沈砚应答简洁,
苏晚小心补充,竟也圆了过去。最后,主簿的目光落在案头那份厚厚的《敦睦录规约》上。
“规矩都清楚?每月初五,交详录。不得记怨怼争吵,不得录闺帷秘事,
须得详述夫妇和睦、互敬互爱之日常。郡王府会不定期派员暗查,若言行与记录不符,
或邻里有怨言……”主簿哼了一声,“莫说岁赐没有,这‘欺瞒官府’的罪过,
也是吃不起的!”“明白。”沈砚应道,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草民明白。
”苏晚跟着应声,手心已全是冷汗。主簿慢条斯理地蘸了墨,
在名册上添上“沈砚、苏晚夫妇”几个字,又盖上一个鲜红的印章。“成了。住处报上来,
自有人去勘验。下月初五,交第一份详录。”走出郡衙那扇沉重的朱漆大门,
午后的阳光刺得苏晚眯了眯眼。百两岁赐的承诺像一块滚烫的烙铁,悬在心头,
也压得她喘不过气。“苏记醴泉在何处?”身侧,沈砚的声音响起,打断了她的恍惚。
苏晚报了个地址,犹豫了一下,低声道:“方才……多谢沈……沈公子解围。
那婚书……”沈砚脚步未停,目光掠过街角那几个已不见踪影的短打汉子,淡淡道:“假的。
旧物,略作修改。各取所需罢了。”他顿了顿,补充道,“契约期内,
在人前唤我‘夫君’或‘沈砚’皆可。人后随意。住所我会尽快解决,不会打扰你与家人。
岁赐所得,归你。我只需这个身份。”他的话语直白得近乎冷酷,
却也奇异地让苏晚松了口气。假的就好。一场交易,互不相欠。几日后,
沈砚搬进了苏家酒坊后院一间闲置的旧厢房。地方不大,收拾得异常干净,
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别无他物,冷清得像间客栈。他每日早出晚归,行踪不定,
极少与苏晚和她的妹妹小满碰面,安静得仿佛不存在。转眼快到月末,
初五交《敦睦录》的日子迫在眉睫。这日傍晚,苏晚刚封好最后一批酒坛,
就见沈砚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灶房门口,手里拿着几张雪浪笺和一支笔。“该‘交作业’了。
”他言简意赅,将纸笔放在院中的石桌上。苏晚的心顿时提了起来。演戏,她不怕苦累,
但对着眼前这个冷得像块石头的“契约夫君”,演那卿卿我我的戏码,实在无从下手。
沈砚似乎看穿了她的窘迫,率先坐下,铺开纸笺,蘸了墨:“你口述,我记。
先定几个‘桥段’。”他语气平淡,像在部署任务,“本月下旬,秋凉渐起。
可记:妻感夫君操劳,夜织寒衣,灯下穿针,夫感其辛,亲奉热茶。”苏晚愣了一下,
忙点头:“好……好。”她想象着那画面,努力挤出一丝温柔表情,
“嗯……妻见夫指尖微凉,劝其添衣?”沈砚笔下不停:“可。添一笔:夫言‘无妨’,
然妻执意取衣披之,夫莞尔受之。”“莞尔?”苏晚差点呛住,
难以置信地看着沈砚那张没什么表情的俊脸。他会“莞尔”?沈砚抬眼,
目光平静无波:“记录而已。郡王府的人不会真来看我笑不笑。”苏晚哑然。也对,
字面功夫。两人就这般一个编一个记,硬生生凑出了“妻为夫洗手作羹汤,
夫赞其味美”、“花前月下,共论农桑”等几段“和谐”日常。编得口干舌燥,腹中空空。
苏晚从灶上温着的锅里捞出几只卤得油亮酱红的鸡爪,端到石桌上:“歇会儿,垫垫肚子。
”沈砚没客气,拿起一只。苏晚也饿了,顾不得形象,两人对坐石桌,就着昏黄的暮色,
啃起了鸡爪,动作一个比一个利落,全无方才记录的半分“斯文”。“明日交上去,
就写‘妻与夫分食珍馐,其乐融融’,对吧?”苏晚啃完一只,吮着指尖的卤汁问。
沈砚正被一小块脆骨噎住,眉头微蹙,闻言点了下头,
端起旁边的粗陶碗灌了口凉水才顺下去。苏晚看他那样子,
下意识地把手边自己那碗没动过的水推了过去:“再加一句,‘妻见夫噎住,
温柔递茶解之’,如何?”沈砚接过碗的手顿了一下,抬眼看向苏晚。昏黄的光线下,
她唇角还沾着一点油亮的酱色,眼神却清澈认真。他喉结微动,沉默地点了头,
在纸上添了那句。“契约夫妻”的日子在鸡飞狗跳与精妙配合中滑过。
苏晚的小酒坊终于酿出了一批新方子的“金桂凝露”,清冽甘甜带着桂花香,成本不低。
能否打响招牌回本,就看这第一波试卖了。她愁得在灶房剁肉馅准备包饺子,
菜刀剁在砧板上,“哐哐哐”震天响,仿佛要把所有忧虑都剁碎了。正剁得起劲,
隔壁书房里,
一阵悠长刺耳、带着金属摩擦特有韵律的“嚓——嚓——嚓——”声也响了起来,
一声接一声,绵延不绝,与她的剁馅声此起彼伏。苏晚的刀停了。她听出来了,
这是沈砚在磨他那把从不离身的、开了刃的短匕。
这声音……是他们约定的“冷战密码”之一。她因为酒坊的事烦躁,没控制住情绪,
剁馅声里带出了火气。他这是在回应:知道了,我在消气(磨剑),你也消停点。
一股莫名的、带着点暖意的尴尬涌上心头。苏晚深吸一口气,放轻了手上力道。果然,
书房的磨剑声也随之低缓下来,渐渐停了。几天后,试卖的日子到了。
“苏记醴泉”的小小铺面前,苏晚正紧张地招呼着稀稀拉拉的几个街坊熟客。忽然,
七八个身形矫健、穿着各异但眼神都透着精悍之气的汉子涌了过来,
二话不说就开始搬酒坛子。“哎!你们……”苏晚吓了一跳。“老板娘,各来一坛!
”为首一个络腮胡大汉嗓门洪亮,“听说你家新酒不错,哥几个尝尝鲜!”他丢下几块碎银,
动作麻利。苏晚又惊又疑,这架势不像买酒,倒像……砸场子?她忐忑地收钱记账,
眼角余光瞥见铺面外不远处的巷口,沈砚抱臂倚墙站着,身影半隐在阴影里,没什么表情,
目光却锐利地扫视着铺面周围。那几个搬酒的汉子,搬完酒也不走,竟自发地站在铺子两侧,
隐隐维持起秩序,驱散了几个想趁机起哄的半大孩子。苏晚心头猛地一跳,忽然明白了。
契约里有一条:“夫需酌情支持妻之产业”。他竟如此“灵活运用”,
拉来了他那些神秘的前同僚!酒卖得出乎意料的顺利。苏晚忙着收钱记账,手都有些抖。
混乱中,一只粗糙的大手伸过来,想浑水摸鱼摸向钱匣子。苏晚吓得往后一缩。“啪!
”一声脆响。那手还没碰到钱匣,就被另一只骨节分明、更快更稳的手攥住了手腕。
是巷口的沈砚,不知何时已到了近前。他脸上没什么怒容,只淡淡地看着那人,
眼神却冷得像冰。那想偷钱的混混脸色一白,手腕剧痛,哀嚎着被沈砚看似随意地一推搡,
踉跄着跌进人群,眨眼溜得没影。秩序瞬间恢复。沈砚没再看苏晚,又退回巷口阴影处,
仿佛刚才只是拂去一片落叶。苏晚看着他的背影,
再看看铺子里那些沉默搬酒、维持秩序的“客人”,一股暖流夹杂着酸涩,悄悄漫过心田。
麻烦也接踵而至。那日之后没过几天,
两个穿着锦袍、腰佩长刀、气势迫人的男子找到了苏家小院。彼时沈砚正在后院劈柴,
苏晚在灶房熬煮酒曲。“沈大人!”为首一人抱拳,声音洪亮,
带着不容置疑的恭敬(或者说强迫),“属下等寻访多时!京中……”话未说完,
沈砚已放下斧头,转过身,脸上是苏晚从未见过的冷硬与疏离:“此处没有沈大人。
二位认错人了。”“大人!”另一人急道,“事态紧急,主上……”沈砚抬手打断,
语气斩钉截铁:“内子体弱,近日染恙,需静养。家中不便待客。二位请回。”他声音不高,
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威压,堵死了对方所有的话头。两个锦袍男子面面相觑,
目光扫过这简陋的小院,又看看沈砚身上沾着木屑的粗布衣裳,最终不甘地抱拳,悻悻离去。
打发走人,沈砚回到院中,见苏晚正扒着灶房门框,一脸担忧地探头张望。“无事。
”沈砚语气恢复平淡,走到院角那架苏老爹留下的旧竹摇椅旁,拍了拍上面的灰,
对苏晚道:“躺下。”“啊?”苏晚不明所以。“装病。”沈砚言简意赅,
“以防他们再派人来探。”他顺手从窗台上苏晚晒的蜜饯罐子里抓了一把塞给她,“吃。
”苏晚:“……”她哭笑不得地抱着蜜饯,躺上摇椅。春日午后的阳光暖融融地洒在身上,
嘴里是酸甜的杏脯。沈砚则搬了个小马扎坐在摇椅旁,拿起一本不知从哪找来的破旧地方志,
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像极了守着病中妻子的丈夫。摇椅轻轻晃动,蜜饯的甜意在舌尖化开。
苏晚眯着眼,看着身旁男人专注(装模作样)读书的侧影,
阳光给他冷硬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一种荒谬又踏实的暖意,悄悄包裹了她。
每月初五交详录,成了雷打不动的“任务”。这日,
苏晚将沈砚誊抄好的、墨迹簇新的《敦睦录》仔细卷好,又用红绳系上,准备送去户房。
临出门,她瞥见自己书桌上摊着几张写废的笺纸,顺手抓起来想揉掉,一起塞进了袖袋。
到了户房,当值的小吏是个生面孔,正忙着整理归档一堆新旧卷宗。苏晚交了卷,
小吏头也不抬地接过,随手往旁边一堆待归档的卷册上一放,便挥手让她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