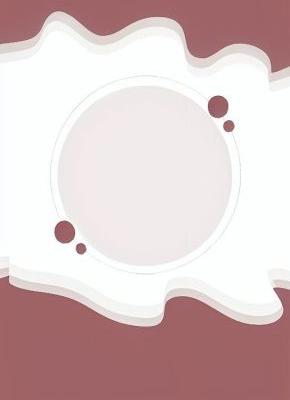
初三暑假,我揣着打工路费站在校门口,班主任骑着破自行车追来。
她喘着气把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塞给我:“高友真,你考上县一中了!”“老师,
我爹妈都没了……”我捏着五十六块三毛钱。“学费我先垫!”她掏空口袋凑出三百块,
“记住,读书是咱山里娃唯一的梯子。”二十年后,我推着轮椅上的她在校园散步。
新来的教授们好奇张望,她拍拍我手背:“现在你是别人的梯子了。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当年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开春的寒气还裹着毛刺,
扎得人脸颊生疼。高友真站在黄土夯实的村口公路上,觉得那疼一直钻进了骨头缝里。
脚下是娘生前纳的千层底黑布鞋,边儿已经磨得发了白,鞋尖沾着路上半干的泥浆。
蓝布裤子的膝盖处,补丁摞着补丁,洗得泛了白,像两团模糊的云。
他肩上挎着一个洗得辨不出原色的帆布包,瘪瘪的,里头只有两件换洗的褂子,
和一个小手绢包,手绢里躺着五十六块三毛钱。那是家里最后一点钱,
爹临终前从炕席底下摸出来,塞给他的。风从北边的豁口子灌进来,卷起沙土,
打在路边枯了一冬的蒿草秆子上,唰唰的响。远处,绵延的土山灰黄一片,看不见丁点绿意。
近处,村子里几缕炊烟有气无力地飘着,还没到晌午,大多数人家都舍不得烧柴。
村小学那面褪色的红旗在旗杆半腰耷拉着,没精打采。高友真把手揣进袖筒,又拿出来,
捏了捏裤兜里那个小手绢包。硬硬的纸币边角硌着手心。去县城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
晌午过点儿从乡上发车,经过村口。他得在这儿等着。脚边是干结的车辙印,一道深,
一道浅。他盯着那些印子,脑子里空空的。爹咳了大半年,最后那几天,
喉咙里像拉着破风箱,呼哧呼哧,眼窝深陷下去,抓住他的手,说不出话,只是看着他。
娘走得早,是秋收时累倒的,再没起来。现在爹也没了。堂叔帮着料理的后事,
最后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瘦削的肩:“真娃,不是叔不念情分,自家也揭不开锅……你大了,
出去寻个活路吧。”隔壁春生他爹在省城建筑队,说能带他去,管吃住,
一个月……兴许能有几十块。先干着。他不知道建筑队要干什么活,只知道要离开这里了。
离开这片看了十四年的山,这条走了无数遍的上学路,还有……学校。风好像更紧了,
灌进他单薄的衣裳里。他缩了缩脖子,目光无意间抬起来,望向村口那条岔路。
那是通往乡中学的路,有七八里,全是上坡下坎的黄土路。
他每个星期天下午背着干粮走回去,星期五下午再走回来。就在这时,岔路口那边,
一个身影歪歪扭扭地出现了。是一辆旧得看不出颜色的自行车,骑得很快,
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着,像随时要散架。车上的人身子前倾,用力蹬着,头发被风吹得乱飞。
那身影有点眼熟。高友真眯起眼睛。心里突地一跳。自行车越来越近,
叮铃哐啷的响声也清晰起来。他终于看清了,是陈老师!他的班主任,陈秀梅老师。
她身上那件半旧的藏蓝色外套敞开着,露出里面红色的毛衣,脸涨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
几缕头发被汗水黏在鬓角。她骑到近前,猛地刹住车,车轮在土路上蹭出两道印子。
她一条腿支在地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张着嘴喘气,话都说不连贯:“高……高友真!
等……等等!”高友真愣住了,呆呆地看着她。陈老师跳下车,车子哐当一声歪倒在路边。
她也顾不上扶,几步冲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她的手很热,抓得很紧,还有些抖。
她另一只手在身上的挎包里急切地翻找,掏出一个皱巴巴的黄色信封。“给……给你!
”她把信封塞进高友真手里,手指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录取……录取通知书!县一中!
你考上了!全校就三个!”高友真低下头,看着手里那个信封。牛皮纸的,
右上角印着“县第一中学”几个红字,已经被揉得有些模糊了。信封口没有封死,
能看见里面一张薄薄的纸。他脑子嗡嗡的,一时反应不过来。考高中是上学期的事,
他参加了考试,考完就忘了。后来爹病重,他心思早不在那上头了。“老师,
我……”他喉咙发干,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我不念了。”陈秀梅的喘息还没平复,
听到这句话,眼睛一下子瞪大了:“你说啥?”“我不念了。”高友真重复了一遍,
垂下眼睛,看着自己露出脚趾的布鞋尖,“我爹……没了。我得去找活儿干。
”陈秀梅抓着他胳膊的手又紧了紧,好像怕他下一秒就会跑掉。她看着他低垂的脑袋,
乱蓬蓬的头发,洗得发白的衣领,还有那双破布鞋。她刚才一路猛骑,
心里那团火急火燎的东西,此刻被少年这句话浇得一阵刺痛。她早就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这孩子上学期期末就总恍惚,成绩却还是拔尖。她料到他家里可能出了大变故,
只是没想到……“不行!”陈秀梅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你必须念!
高友真,你听我说,你考上县一中了!那是好学校,将来能考大学!”高友真摇摇头,
没吭声。他把手从陈秀梅手里抽出来,伸进裤兜,掏出那个小手绢包,慢慢打开。
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小沓毛票,最大的面额是两张十块的,
更多的是皱巴巴的一块、五毛,还有几个硬币。“我就这些钱了,
”他把手绢托到陈秀梅面前,声音很低,“五十六块三毛。去省城的车票不知道够不够。
”那几张零碎的票子,躺在洗得发白、边缘有些破损的手绢里,
被早春冷硬的风吹得微微抖动。陈秀梅的目光落在那些钱上,又猛地抬起来,
盯住高友真的脸。少年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一种过早来临的、沉重的平静,
可那双眼睛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点熄灭下去,像寒夜里最后一点微弱的炭火,
眼看就要被风吹灭。陈秀梅的心像被那只摊开的手、那些零票狠狠攥了一把,酸胀得厉害。
她忽然转过身,扶起倒在地上的自行车。
那辆老旧的“二八”横梁上挂着一个磨得起毛的黑色人造革包。她手忙脚乱地打开搭扣,
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往外掏:两本卷了边的练习册,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试卷,
一个掉了漆的军绿色水壶,半包用作业纸裹着的饼干屑……她的手在包里急切地摸索着,
指尖触到内袋一个薄薄的、同样有些旧的小布包。她掏出来,那是一个手缝的小钱包,
深蓝色的底子上绣着已经褪色的白色小碎花。她一把扯开束口的绳子,
把里面的钱全部倒在车座垫上。有几张一块、两块的纸币,
更多的是一摞摞用橡皮筋扎好的毛票——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一毛的。
那是她这个月的工资剩下的,准备带回家贴补家用,给老人抓药,给孩子交书本费。
她数也不数,一把抓起来,又把自行车把上挂着的那个更旧的小布包也扯下来,
把里面几个钢镚倒在手心。然后,她转过身,把这一把零的整的、皱巴巴的票子,
连同那几个沉甸甸的硬币,不由分说地,全部塞进高友真那只还托着手绢的手里。“拿着!
”她的声音因为激动和刚才的奔跑而有些嘶哑,却异常清晰,
一个字一个字砸在清冷的空气里,“学费,老师先给你垫上!”高友真只觉得手上一沉,
冰凉坚硬的硬币和柔软的纸币混在一起,压在手绢那少得可怜的五十六块三毛上。
他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想缩手:“老师,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你给我拿着!
”陈秀梅用力按住他的手,她的手心很热,甚至有些烫,“高友真,你听着!”她喘了口气,
目光灼灼,像两簇不肯熄灭的火苗,直直看进他眼睛深处,“这点钱,不多。
但够你去县一中报个名,够你撑过头一个月!老师知道你难,家里没了顶梁柱,天塌了一样。
可越是这种时候,你越得咬住牙,把书念下去!”风卷起地上的尘土,打着旋儿。
远处传来几声沉闷的狗吠。
陈秀梅的声音在风里显得异常坚定:“你记住老师今天的话:读书,是咱们山里娃,
唯一一架能爬出这穷山沟、能去看看外面天地的梯子!这梯子陡,难爬,可能还晃悠,
但它就在那儿!你得抓住它,一步一步往上走,别回头,别往下看!”她说着,松开了手,
但目光依旧紧紧锁着他:“县一中那边,我会去跟学校说你的情况,申请减免,申请补助!
你在学校,就一门心思学习!别的,先别想!天无绝人之路,听见没有?”高友真低着头,
看着自己两只手里满满当当的钱。老师的钱,和他那五十六块三毛混在一起,旧的新的,
整的零的,带着老师手心的温度,沉甸甸地压在他掌心里,压得他手腕发酸,
压得他眼眶也猛地酸胀起来。喉头像堵着一大团粗糙的砂石,哽得生疼。他死死咬着下嘴唇,
咬得尝到了淡淡的铁锈味,才把那阵汹涌的、陌生的酸热狠狠逼了回去。不能哭。
爹娘没了他都没当着人面哭过。他慢慢抬起头,迎上陈秀梅殷切而炽烈的目光。
老师额前的头发被汗水黏住,脸颊因为刚才的疾驰和激动而泛着红,
藏蓝色外套的袖口已经磨得发白起毛。她身后是那辆歪靠在路边、漆皮斑驳的旧自行车,
再后面,是灰黄寂寥的远山和天空。他忽然想起语文课本上,好像有一句诗。他记不全,
只模糊有个印象。大概意思是,什么东西虽然微小,却足够照亮一段黑夜里的路。
他嘴唇翕动了几下,终于,极其缓慢地,把手里的钱,连同那个小手绢,
一起紧紧地攥在了掌心。骨头硌着硬币,有些疼。他点了点头,很重地点了一下。“老师,
”他的声音依旧沙哑,却好像有了一点力气,“我……我去上学。”陈秀梅一直紧绷的肩膀,
几不可察地松了一下。她长长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白色的雾气在冷空气中迅速消散。
她抬手,用力抹了一把额头的汗,又胡乱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这就对了!
”她的语气轻松了些,伸手帮他把帆布包的带子往上提了提,拍了拍他瘦削的肩膀,
“把通知书收好。回家……算了,直接去乡上等车吧,今天就去县城,早点安顿下来。
到了学校,找教导处的李主任,就说是我让你去的。”高友真把那皱巴巴的信封,
小心翼翼地塞进帆布包的内层,贴着那几本旧课本放好。然后,
他把那一把钱仔细地用手绢重新包好,也放进包里,按了按。陈秀梅扶起自行车,
掉转车头:“我还得赶回学校上课。你快去吧,路上小心。”高友真站在原地,
看着陈老师骑上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沿着来路,奋力蹬去。
她的背影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着,藏蓝色外套被风吹得鼓起来,很快变小,拐过路口,
不见了。只有那车轮轧过土路的细微声响,似乎还在风里残留了一瞬。他转过身,
背对着村庄,面向公路延伸的方向。攥紧了帆布包的带子。五十六块三毛,
加上老师给的那些,他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但足够买一张去县城的车票,或许,
还能剩下一些。他把帆布包甩到肩上,迈开了步子。布鞋踩在干硬的土路上,
发出轻微的沙沙声。风还在吹,很冷,刮在脸上像小刀子。
但他觉得掌心那紧紧攥着过什么的感觉,还在隐隐发烫。他沿着公路,一步一步,
朝着乡车站的方向走去。没有再回头。县一中的大门比乡中学的气派得多,砖砌的柱子,
顶上挂着校牌。高友真站在门口,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手心全是汗。门卫室的老头探出头,
上下打量他几眼,目光在他打补丁的裤子和布鞋上停了停,才瓮声瓮气地问:“找谁?
干嘛的?”“我……我来报到。考上的。”高友真连忙从包里掏出那个皱巴巴的信封。
老头接过去,眯着眼看了,又瞥瞥他:“高友真?就你一个人?家里大人呢?
”“家里……有事。”高友真垂下眼。老头没再多问,指了个方向:“那边,红色那栋楼,
一楼教导处。”教导处里弥漫着粉笔灰和旧木头的气味。李主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听了高友真磕磕巴巴的说明,又看了看陈秀梅老师写在录取通知书背面的一行小字和签名,
眉头皱了皱,叹了口气。“陈老师电话里跟我说过了。你的情况,学校知道了。
”李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沓表格,“按规定,学费可以申请部分减免,
但住宿费、书本费、伙食费……这些都得自己想办法。学校有勤工俭学的岗位,但不多,
竞争也激烈。你……”“我能干活。”高友真立刻抬头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什么活都行。我会好好学习。”李主任看着他瘦小却挺得笔直的身板,
和那双过于早熟而沉静的眼睛,终于点了点头:“先去总务处办住宿,安顿下来。
勤工俭学的事,我帮你问问。课本先去教材科领,跟老师说清楚情况。”宿舍是八人间,
拥挤,但比家里四面透风的土墙房结实。他的床位靠门,上铺。
用老师垫的钱和被减免后剩下的钱,他交了最低限度的费用,领了被褥和饭票。被褥是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