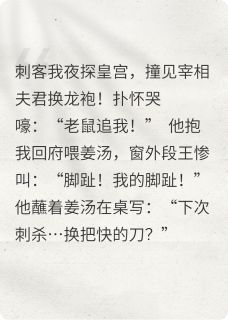
别人穿成王妃是宅斗,我穿成八岁王妃——是连夜给皇帝当刺客!黑心段王拿捏我土匪身份,
逼我毒杀皇帝;可没人告诉我,我那病弱宰相夫君,脱了官服就是龙袍加身的皇帝本尊!
第六次刺杀,他当众搂我入怀:“此乃朕的皇后!”段王气疯跳脚:“她是刺客!
”太后反手一个寿桃砸他脸上:“闭嘴!这是哀家御膳房认证的好儿媳!
”——现在问题来了:夫君兼刺杀目标,天天用满汉全席贿赂我,这皇帝…还杀吗?
1段王把药碗怼到我唇边,腥臭味冲得我反胃:“喝!缩成八岁替你那死鬼爹当王妃!
三日内皇帝不死——”他猛踹铁笼,姐妹阿蛮在笼里痛呼,“老子就剐了她们!
”十八岁的我吞下药,喉咙像吞了炭火。操!等姐妹脱困,老娘把你金牙一颗颗撬下来!
骨头缩紧的疼劲儿过去,我低头看鸡爪似的小手。盖头被挑起——嚯!
这宰相慕容清脸白得像糊墙的腻子。刚掀完盖头就咳得撕心裂肺,帕子上全是血点子。
老妈子急吼吼递药:“相爷保重!陛下也真是,
天天留您议政到三更…”我心里冷笑:病痨鬼!咳成这样还得给皇帝卖命?挺好,
夜里肯定睡死!“夫…夫君?”我掐出奶音,自己膈应得慌。他垂眼瞥我,
眼神像看路边的石头:“委屈你了。”声音哑得像破锣。他忽然伸手拂过我左袖!
我汗毛倒竖——毒镖就藏在那儿!他却只捻了捻袖口绣花:“沾灰了。
”指尖擦过毒镖冷硬的棱角,激得我一抖。“夫人早些安置,”他咳着转身,腰背挺得笔直,
“陛下…还等着臣议政。”慕容清这病痨真够拼!白天咳得惊天动地,天一黑就往宫里冲,
美其名曰“陛下急召”。老娘乐得清闲——夜夜溜出去宰贪官!刚钻出狗洞,
就听见巡逻侍卫嘀咕:“陛下真是…总留相爷到深夜,
相爷那身子骨…”我嗤笑:皇帝老儿真不是东西!我像壁虎一样贴墙根挪到皇帝寝宫台阶下。
刚喘口气,描金殿门“吱呀”开了。明黄龙袍。伸懒腰的身影。慕容清?!操!
我嫁的“病痨”宰相就是皇帝?段王这老狗坑死我了!脑子“轰”地炸了。
眼看他转头扫过来,死亡的恐惧瞬间攫住我。“哇——!”我爆发出凄厉的童音哭嚎,
八岁的小身板炮弹般猛冲过去,狠狠撞在他大腿上。骨头硌得我胸口剧痛,管不了了。
我死死箍住他的腰,鼻涕眼泪全糊在他冰凉的龙袍上,浑身抖成筛糠:“呜呜夫君救命!
有老鼠。好大好黑。追我!呜呜呜吓死小七了!”被我撞上的一瞬,他身体骤然绷紧。
硬得像块铁板。但这僵硬只持续了一瞬,一条手臂就下意识环住了我后背,
甚至轻轻拍了两下。更惊悚的是,我的脸紧贴他小腹上方——隔着一层龙袍,底下那颗心跳,
咚!咚!咚!沉稳有力,快得惊人,哪他妈像个咳血的病秧子?!“嗷——!我的脚!
死老鼠滚开!”花丛后传来段王压抑的痛嚎。活该!报应!头顶一声轻咳。后颈一凉,
他捏着我那块软肉,像拎猫崽似的把我从他怀里“提溜”出来。月光下,
他脸色还是病态的苍白。但那双眼睛黑沉沉地盯着我,深不见底。
冰凉的指尖捏得我后颈皮发麻。“宫禁森严,”他声音不高,带着点刚醒的沙哑,
却字字砸耳,“夫人如何在此?”来了!我立刻进入角色,小嘴一瘪,肩膀一耸一耸,
君送…送参汤…皇宫好大好黑…还有老鼠…呜呜…”我抬起泪汪汪的眼(努力挤出点水光),
带着“后怕”和“懵懂”:“陛下…陛下呢?没…没留您议政吗?”致命问题抛出!
他没立刻回答。慢条斯理地从袖中掏出一方白帕。俯身,
动作“轻柔”地用帕子擦我糊满眼泪鼻涕的小花脸。帕子带着他身上那股清冷的药草香。
指腹隔着薄薄的丝帕,擦过脸颊、鼻尖…最后,
不轻不重地按在了我左眼下那颗小小的泪痣上,停住。我的心跳骤停!他是不是认出来了?!
他抬眼,目光沉静,嘴角却勾起一丝极淡的、难以捉摸的弧度:“迷路?参汤?”他重复着,
尾音微妙上扬,“陛下龙体不适,歇下了。”回答了,却跟没答一样。
他的指尖还按着我的泪痣,目光却像要穿透我这层八岁的皮囊。
“倒是夫人你…”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丝玩味的审视,“方才跑起来…脚下生风,
那速度…可真不像被老鼠撵的。”泪痣被他按得发烫!我猛地缩脖子,
像受惊的兔子躲开他冰冷的手指,声音尖细变调:“老…老鼠!它追得可凶了!
不跑快就被咬掉脚趾啦!呜呜…陛下真歇啦?那…那您也快回府歇着?”2他拎我进寝宫。
烛火通明,龙涎香冲得我头晕。我盯着他后背——杀!姐妹就能活!袖中匕首滑出,
我挪到龙床边。刀尖离他脊背一寸。他突然翻身坐起:“折腾半宿,饿否?
”我吓得匕首“当啷”掉地!匕首掉地上的声音太响了,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操!露馅了!
他倒好,跟没事人一样坐起来,拍了拍手。门一开,太监宫女跟流水似的涌进来,
眨眼功夫就把那张大桌子堆满了。烤乳猪皮脆得反光,蟹黄包冒着热气,水晶肉片透亮,
还有一堆我叫不上名的硬菜。香味儿猛往鼻子里钻,我肚子不争气地“咕噜”一声巨响,
震得我自己都脸红。妈的,丢人!“坐。”他自己先坐下,夹了个小包子吃,慢悠悠的。
我站着没动,手指头揪着裙子边,眼睛管不住地往那盘酱红色的大肘子上瞟。真他娘香啊!
“怕下毒?”他撕了一大块肘子肉塞嘴里,嚼着,眼睛盯着我看,像看猴戏。怕个屁!
毒死也比饿死强!“哇!好香啊!”我掐着嗓子装小孩叫唤,扑到桌子边的高凳上。
手脚并用爬上去,伸手就抓了最大那只鸡腿!张嘴狠狠咬!鸡皮脆,肉嫩,油汁儿烫嘴,
香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了!去他娘的刺杀!去他娘的皇帝!老娘先吃饱再说!我埋头猛啃,
吃得满手满嘴油。“好吃吗?”他声音带笑。我吃得正爽,想都没想,
甩着油乎乎的脑袋:“香!真他…”“真好吃!”差点说漏嘴。
手里啃光的鸡腿骨“嗖”地飞出去,穿过窗户缝。窗外立刻响起段王杀猪似的惨叫:“啊!
我的眼!哪个王八蛋扔的骨头?!操!”我啃鸡腿的动作僵住了。操,劲儿使大了!突然,
一块带着药味儿的白手帕擦上我下巴,蹭掉一滴油。我抬头。他不知道啥时候凑过来了,
弯着腰,离我耳朵很近。他呼出的热气喷在我脖子上,痒痒的。“骨头飞得挺准?
”他声音压得低低的,听得我心里发毛。我装傻:“它自己飞的!怪…怪那骨头太滑!
陛下呢?您吃这么多好东西…不用伺候陛下啊?”赶紧转移话题!他不紧不慢地盛了碗热汤,
推到我面前。碗底,正正压着我刚才甩出去的那根光溜溜的鸡腿骨!我捧着碗,手都僵了。
热汤气儿糊了眼。操!他看见了!他绝对看见了!他手指头敲敲桌面,
发出“哒、哒”的声音。“夫人要是爱吃…”他突然抓住我坐的凳子腿,
连人带凳猛地拽到他跟前!我整个人被拖过去,差点从凳子上栽下来。
他身上的龙涎香和药味一下子把我罩住了,距离近得吓人。“…为夫天天让他们给你做?
”他低头看着我的油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砸在我耳朵里。
3段王那独眼老狗半夜翻窗,把毒粉拍我枕边:“再失手…老子把你姐妹的耳朵下酒!
”我攥着毒粉蹲在御书房书架后。安神香熏得人昏沉。不行…撑住…再睁眼,
头顶是蟠龙金帐!身下是滑溜溜的龙纹锦被!“醒了?”带笑的声音响起。
夫君披着寝衣靠坐床头,手里奏折哗啦一响,“夫人这梦游的功夫…比轻功更妙。
”我“噌”地坐起来,裹紧被子缩到床角,后背死死抵着冰凉的柱子:“我…我怎么在这儿?
!”他放下手里的折子,慢悠悠站起来。他太高了,站在床边像个影子罩下来。我缩得更紧,
八岁的身体在他面前跟个小鸡崽似的。“这话,”他声音不高,带着点刚睡醒的沙哑,
“该我问你吧?”他弯下腰,那张没什么血色的脸离我很近。手指头伸过来,不是碰我,
是撩了撩我肩膀上乱糟糟的头发丝儿,“夫人半夜摸进御书房…是找我,还是找‘陛下’?
”他说“陛下”那俩字儿,有点怪。“找您,当然是找您!”我赶紧装乖,
声音掐得又软又急,“陛下总留您议政到那么晚,小七担心您身子。”一边说,
藏在被子里的手偷偷往枕头底下摸——空的!我塞那儿的毒粉没了。冷汗“唰”地冒出来!
“找这个?”他声音在头顶响起。我一抬头,魂儿差点飞了。他手里捏着那个眼熟的油纸包,
我的毒粉!更他妈要命的是,他居然把那玩意儿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像闻香囊似的。然后,
他眉毛一挑,看着我,嘴角勾起个特别欠揍的笑:“夫人新弄的‘香’?味儿…可真冲。
”那语气,明晃晃的嘲笑!操!他知道!他就是在耍我玩!我臊得满脸通红,只想立刻消失。
手忙脚乱想从床角爬出来溜走。刚挪动一下,他手臂突然一伸。不是抱,
是像拎个小包袱似的,大手直接卡在我胳肢窝下面。稍一用力,
就把裹着被子的我从床角“提溜”了出来。八岁的身体轻飘飘的,被他轻而易举地悬空拎着,
离了床铺。那一瞬间的感觉,贼他妈憋屈。他胳膊很有劲儿,
隔着薄被都能感觉到他手指的力道,稳稳地箍着我的肋骨下方。我的脚离了地,
在半空中晃荡了两下。他身上的药味和龙涎香味儿一下子把我裹住了,热烘烘的。
我像个被捏住后颈皮的猫崽,完全被他掌控着。十八岁的灵魂在咆哮:操!放老娘下来!
八岁的身体只能僵着,动都不敢动。他拎着我,把我轻轻“放”在床沿坐着,
脚总算挨着地了。但他没立刻松手,那只大手还虚虚地扶在我背后,像是怕我摔了。
距离太近,他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眼睛就垂着看我,带着点审视。“慌什么?”他声音低低的,
手指在我背后隔着被子轻轻点了点,“为夫又不会吃了你。”这话听着像哄小孩,
可我他妈只觉得后脖子发凉。脚一沾地,我立刻像被火烧了**的兔子,连滚带爬地窜下床,
头也不回地冲出寝殿。背后好像还听见他低低的笑声,更气了。一路狂奔到御花园锦鲤池边,
扶着棵老树喘粗气。脸还烫得厉害,一半是气的,一半是刚才被他拎起来的憋屈。
“噗通——”“哎哟**!”巨大的落水声加熟悉的骂街。我扭头一看,乐得差点蹦起来。
段王那老狗正在池子里狗刨呢!一身黑绸湿透了贴在干巴身上,脑袋上顶着一坨水草,
活像戴了顶绿帽子。一条肥锦鲤大概被他吓着了,
“啪”地一尾巴甩在他那只没受伤的眼睛上。他那只绑着绷带的独眼气得直冒火,
一边扑腾一边骂:“哪个缺德带冒烟的泼的油?想摔死老子?晦气!真他娘的晦气。
”看着他这副落汤鸡加绿毛龟的衰样,刚才的憋屈瞬间烟消云散。
我拍着树干哈哈大笑:“活该,报应!淹死你个老狗!”手腕猛地被一只滚烫的大手攥住。
笑声卡在喉咙里,我惊恐地回头。夫君不知啥时候站我身后了。还穿着那身睡觉的白衣服,
外面随便披了件黑袍子,头发有点乱。他脸上没啥表情,但眼神沉得吓人。他攥着我的手腕,
掌心烫得离谱。他先扫了眼我惊呆的脸,然后目光慢悠悠地移开。
落到了池子里正往上爬的、一身狼狈的段王身上。接着,他低下头,嘴几乎贴到我耳朵边,
呼出的热气喷在我耳垂上。“夫人刚才…笑得挺欢?”他故意顿了一下,
目光又瞟向落汤狗段王,慢吞吞地问,“…见着熟人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脸上还得装出被吓到的样子,缩着脖子:“没…没有!就是…就是看见只癞蛤蟆掉水里了,
好笑…”声音越说越小。“午膳时辰到了。”“随为夫回宫用膳。”4被他带回一个偏殿,
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没上次寝宫那么夸张,但也挺精致。我心不在焉,
满脑子都是刚才被他抓包的尴尬和段王那衰样。加上确实饿了,抓起筷子就吃。吃着吃着,
感觉不对劲了。头越来越沉,像灌了铅。眼前的菜盘子开始晃,耳朵里嗡嗡响。
筷子“啪嗒”掉桌上,我甩甩头,想清醒点。“夫人?”他的声音好像隔着层水传过来,
听不真切。“我…我没事…”我想站起来,结果腿一软,整个人就往旁边栽!
没有预想中摔地上的疼。一条有力的胳膊及时捞住了我,把我整个儿圈住了。
八岁的小身板在他怀里轻飘飘的。他身上的药味和龙涎香变得特别浓,熏得我头晕眼花。
“好烫。”一只冰凉的手贴上了我的额头,那感觉舒服得我想蹭蹭,
但下一秒就彻底没了意识。感觉像是在黑暗里漂了好久,浑身骨头缝都疼。
一会儿冷得像掉冰窟窿,一会儿又热得像被架在火上烤。难受得要死,忍不住哼哼唧唧。
嘴里发苦,时不时有温热的、带着药味的液体被小心地喂进来。有时苦得我直皱眉想吐,
就有人轻轻拍我的背,动作有点生硬,但挺耐心。好像还听到有人说话。
有时是太医战战兢兢的声音:“…风寒入体,来势汹汹…”有时是他在旁边问:“药喝了?
烧退了点?”声音听着比平时低,好像还有点…着急?最他妈丢人的是,我好像还说了胡话!
迷迷糊糊的时候,
冒:“鸡腿…别跑…”“老狗…淹死你…”“阿蛮…小月…别死…”“…匕首…藏好…”操!
我都说了些啥?十八岁的灵魂在昏迷的躯壳里急得跳脚,生怕把老底全秃噜了。
但身体不受控制,一会儿喊冷要被子,一会儿又踢腾着嫌热。
感觉有人不停地给我换冷帕子盖额头,掖被角。动作算不上多温柔,但没撒手不管。
那感觉…有点怪。好像这个知道我要杀他、还总耍我的男人,对我这具八岁的壳子,
还挺…上心?不知道昏了多久,终于彻底清醒过来。睁开眼,又懵了。不是偏殿,
也不是龙床。这地方更宽敞,摆设看着更贵气,空气里有股淡淡的、好闻的花香。
我躺在一张超级软和的大床上,盖着轻飘飘的锦被。“醒了?”熟悉的声音。扭头一看,
夫君就坐在床边不远处的椅子上,手里拿着本书。脸色还是白,但精神看着还行。
他放下书走过来。“这…这是哪儿?”我嗓子哑得厉害,像破锣。“坤宁宫。”他答得简单,
倒了杯温水递过来。坤宁宫?皇后住的地方?我差点被水呛着!他等我喝完水,
又变戏法似的,从袖子里摸出个东西。金光闪闪!上面镶着宝石,还垂着流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