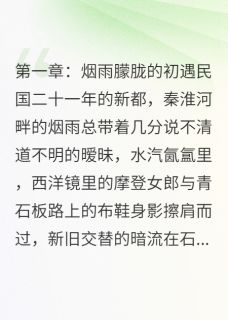
第一章:烟雨朦胧的初遇民国二十一年的新都,
秦淮河畔的烟雨总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水汽氤氲里,
西洋镜里的摩登女郎与青石板路上的布鞋身影擦肩而过,
新旧交替的暗流在石板缝里悄悄涌动。沈梵踩着沾满晨露的石阶上山时,
浅灰西装的袖口已被雾气洇出淡淡水痕。秦风紧随其后,黑色短靴踏过湿滑的苔藓,
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古寺的断壁残垣在烟雨中若隐若现,飞檐翘角的轮廓被雨水洗得发白,
像一幅被时光晕染的水墨画。秦风:“少帅,这是最新勘测的图纸,
秦风将一卷牛皮纸图纸递上前,目光扫过墙根处一抹突兀的鹅黄。沈梵接过图纸的手顿了顿。
晨光正透过云层的缝隙漏下来,在断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一个穿着素色布裙的姑娘正踮着脚,手里拿着小小的竹筒,往砖缝里那株刚冒头的野草浇水,
她的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发梢沾着细碎的水珠,阳光穿过发隙时,
在地上织出一片晃动的光斑。他指尖的铅笔在图纸上停住,
笔尖悬在“大雄宝殿”的标注上方,心头莫名地漾起一丝涟漪,这古寺他已考察过三次,
从未留意过墙缝里还能长出这样有韧性的生命。温心:“这寺墙的砖缝里,
藏着百年的雨水呢。”姑娘忽然转过身,声音清浅得像山涧的溪流,她手里还握着竹筒,
看见沈梵望着图纸出神,眼睫轻轻颤动了一下,又补充道:“祖父说,修旧如旧,
得顺着它原本的性子来。”沈梵抬眼时,正撞见她清澈的目光,
那双眼眸像浸在溪水里的黑曜石,映着断墙的轮廓,也映着他此刻微怔的神情,
他注意到她指尖沾着的墨痕,不是寻常胭脂水粉的艳色,而是松烟墨特有的沉静光泽。
沈梵:“你懂建筑修复,他挑眉,目光落在她沾着泥土的布鞋上,这姑娘看着不过十六七岁,
素净得像古寺后院的青苔,却能说出这般贴合肌理的话。温心摇摇头,将竹筒放进竹篮里。
篮底露出半截古籍,封皮是磨损的蓝布面:“不懂建筑,只是常听祖父说裱画的道理。
古画修复讲究‘补纸如补肌’,想来这砖墙也是一样的,她指着墙角那处开裂的斗拱,
“您看那处榫卯,原是用糯米浆粘合的,若是换了水泥,反而伤了它的筋骨。
”沈梵的目光倏地锐利起来。这处斗拱的特殊构造,连设计院的老工匠都未曾留意,
她一个看似普通的姑娘竟能一语道破,他展开图纸,指着其中一处标注:“那依姑娘之见,
这处横梁该如何处理?”温心:“横梁内侧有三处虫蛀的空洞,
温心:“祖父曾在横梁背面发现过明代的修补痕迹,用的是樟木嵌补法,您看这木纹走向,
她纤细的手指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弧线,就像人的血脉,得顺着它的肌理走。
”秦风在一旁暗自咋舌,沈少帅留学归来后主持过十余处建筑修复,
从未有人敢在他面前指点图纸,更何况是个不知名的姑娘,可沈梵却听得认真,
甚至微微俯身,让她看得更清楚些。沈梵:“你祖父是,温心:“温知言,
曾在寺里做过裱画匠,她提起祖父时,眼底浮起一层温柔的光晕,他教我辨识木柱的年轮,
说每一道圈都是时光刻下的印章,她走到左侧那根歪斜的楠木柱前,手掌轻轻贴在柱身上,
这根柱子有一百三十二圈年轮,道光年间的那场暴雨让它歪了半寸,却也让它扎得更深。
”沈梵看着她专注的侧脸,忽然觉得这古寺的晨雾都变得生动起来,
他讲起巴黎圣母院的玫瑰窗,
说阳光透过彩玻璃时会在地面投下流动的光斑;温心则说起秦淮河畔的画舫,
讲那些在月光下泛着银光的飞檐翘角。他教她看图纸上的比例尺,
她便拉着他去后院辨认草药,指着那株开着细碎白花的植物说:“这是续断,专治跌打损伤,
祖父常说,万物都有自愈的本事。”秦风远远站在山门处,看着少帅蹲在药圃前,
听那姑娘讲得眉飞色舞,手里的铅笔无意识地在图纸背面画着什么,晨雾渐渐散去,
古寺的轮廓在阳光下清晰起来,断墙上的爬山虎垂落下来,恰好拂过两人并肩的身影。
沈梵忽然想起临行前母亲孟清如的话,说这古寺与沈家渊源颇深,他摩挲着胸前那半块玉佩,
冰凉的玉质似乎也染上了几分暖意,
当温心指着檐角那只风化的螭吻说“它嘴里的铜铃原是鎏金的”时,他忽然觉得,
这趟古寺之行,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温心转身去竹篮里取水壶时,
瞥见他腰间露出的玉佩一角,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顿,
那纹样像极了祖父临终前指着的那幅《古寺晨钟图》上的印章,只是她还没来得及细想,
就听见沈梵问道:“温姑娘明日还来吗?我想请教些关于斗拱结构的问题。
”她低头看着鞋面的泥点,声音轻得像飘落的雨丝:“我每日都来给祖父种的草药浇水。
”沈梵将图纸卷起来的动作慢了半拍,铅笔在纸卷上留下一道浅痕,秦风注意到,
少帅嘴角那抹惯常的清冷,不知何时已化作了柔和的弧度。
第二章:药香里的重逢晨露还挂在艾草叶尖时,温心已挎着竹篮站在古寺后山的石阶下,
春桃提着小锄跟在后面,裤脚沾着露水打湿的泥点,嘴里念叨着:“**您看,
陆少爷的黄包车上还插着您喜欢的雏菊呢。”温心抬头望去,
青石板路尽头停着辆锃亮的黄包车,陆景然正倚着车把朝她笑。他穿着月白色的杭绸长衫,
手里把玩着折扇,扇面是新绘的《寒江独钓图》,笔锋带着几分刻意的洒脱,看见温心,
他立刻迎上来,自然地接过她手里的竹篮:陆景然:“昨日听秋纹说你要采何首乌,
我特意让阿武备了新锄,温心:“景然哥哥费心了,温心接过春桃递来的草帽,
指尖触到草绳编织的纹路,“祖父留下的那株何首乌该换盆了,需得配些阴坡的腐叶土。
”陆景然的折扇“唰”地展开,遮住半张脸,只露出含笑的眼睛:“你呀,
总记着这些草木的性子,他侧身让她上黄包车,长衫下摆扫过车座时,
带起一阵淡淡的古龙水味,与温心竹篮里的艾草香格格不入。
黄包车碾过石子路的声响惊动了树梢的麻雀,陆景然说起南京商会的新鲜事,
说柳玉茹女士新办的女子学堂添了西洋画课,问温心要不要去看看,
温心望着车窗外掠过的竹林,轻声道:“还是古寺的墨香更合心意。”陆景然的笑容淡了些,
他与温心自幼相识,看着她从梳总角的稚童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却总觉得隔着层薄雾,
她的世界里有古画的肌理、草药的性味,还有那些他读不懂的沉默,就像此刻,
她分明在听他说话,目光却落在远处崖壁上那丛开着紫花的石韦上。温心:“那是石韦,
治淋症的良药,祖父说这草性喜阴湿,采的时候得留三分根,她挽起布裙下摆,
踩着湿滑的苔藓就要往上爬,手腕却被陆景然攥住。陆景然:“仔细脚下,
他的语气带着惯常的温和,指尖却微微用力,让阿武来采便是,你何苦沾这一身泥。
”温心挣开他的手,指尖在裙角蹭了蹭:“药草也有灵性,旁人采的不合时辰,
她仰头看那丛石韦,阳光透过竹叶洒在她脸上,绒毛都看得分明。陆景然望着她专注的侧脸,
忽然想起母亲柳玉茹的话:“景然,温心这姑娘好是好,只是太过静了,
配不上你风风火火的性子。”他正想再说些什么,忽听身后传来皮鞋踏过枯枝的声响,
沈梵穿着同色的浅灰西装,袖口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一道浅淡的疤痕,
那是昨日勘察时被断木划伤的,秦风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个金属工具箱,
见到陆景然时微微颔首,目光却在温心沾着泥土的指尖顿了顿。陆景然:“沈少帅也来晨练,
巧得很,我陪心妹来采些草药,沈梵:“这石韦的孢子囊得正午采收才有效。”温心抬眸时,
正对上他的目光,他的眼底没有昨日的疏离,反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关切,
像是在提醒她注意时辰,她指尖蜷缩了一下,将沾着泥土的手背到身后:“沈先生也懂草药?
”沈梵:“略知一二,沈梵的目光掠过陆景然搭在车把上的手,
昨日在寺里听温姑娘说起续断的用法,特意翻了祖父留下的医书,
他从秦风手里接过一个牛皮纸包,这是欧洲带来的止血粉,比草药见效快些。
”纸包递过来时,温心闻到一股淡淡的松节油味,混着他身上的烟草香,竟不觉得刺鼻,
她正要伸手去接,陆景然已抢先一步接过:“多谢少帅好意,心妹向来只用祖父传下的法子,
他将纸包塞给阿武,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熟稔。
沈梵的目光在陆景然搭在温心肩上的手顿了顿,
指尖在工具箱的金属锁扣上轻轻敲了敲:“我来取昨日落在寺里的绘图尺,他看向温心,
“顺便想请教,您说的樟木嵌补法,可有具体的文献记载?”温心:“祖父的笔记里有提过,
温心侧身避开陆景然的手,从竹篮里取出个蓝布封皮的册子,只是字迹潦草,
怕是难登大雅之堂。”沈梵接过册子时,指尖不经意触到她的指腹,
她的指尖带着草药的凉湿,他的掌心却因握着工具箱而温热,两人都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手,
册子掉在地上,里面夹着的干枯艾草散落出来,恰好落在沈梵的皮鞋前。温心:“对不住,
陆景然:“心妹的花,还是别让旁人碰了。”沈梵弯腰捡起册子,
注意到扉页上画着株何首乌,根茎缠绕成“寿”字形状。他指尖抚过那细腻的笔触,
忽然道:“令祖父的画,颇有黄公望的笔意。”温心抬眸时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这画册她从未示人,他竟能一眼看出祖父临摹的师承。陆景然的笑容僵在脸上,
他认识温心十几年,只知她会裱画,却不知她还藏着这样的本事。温心:“少帅若不嫌弃,
改日我拓份摹本送您,温心接过册子,指尖在“寿”字根茎处轻轻点了点。
那里藏着祖父用朱砂标注的草药特性,是她与祖父之间的秘密。沈梵颔首时,
目光扫过陆景然别在温心发间的雏菊,
忽然从西装口袋里取出个小纸包:“昨日在后山发现几株野山参,
或许对令祖父留下的药圃有益,纸包打开时,露出几株带着泥土的参须,根须完整,
显然是精心采挖的。温心:“少帅费心了,温心接过纸包的动作很轻,
像是捧着什么珍贵的物件。春桃在一旁看得分明,自家**接过野山参时,耳根悄悄红了。
陆景然的折扇在掌心捏出了褶皱,他看着沈梵与温心讨论着草药的药性,
看着阳光穿过两人交叠的身影落在地上,忽然觉得这山间的风都变得滞涩起来,
阿武识趣地说:“少爷,时候不早了,商会还有事等着您处理呢。”陆景然:“那我先回了。
”陆景然拍了拍温心的肩,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怅然,采完药早些回去,
我让厨房炖了冰糖雪梨,温心点头时,目光正与沈梵相撞。
他眼里的清冷不知何时染上了暖意,像晨雾散去后的阳光,落在她沾着泥土的指尖,
竟有些发烫,秦风看着少帅将那本蓝布册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工具箱,忽然明白,
昨日图纸背面那几笔潦草的雏菊,为何画得那般用心。待陆景然的黄包车消失在竹林尽头,
沈梵忽然指着崖壁上的石韦:“现在辰时刚过,正是采收的好时候,他示意秦风取出登山绳,
我来吧,这石缝里的草,我比你们熟。”温心望着他攀援在崖壁上的身影,
西装裤被荆棘划破了一道口子也浑然不觉,阳光照在他专注的侧脸,
竟比陆景然精心打理的长衫更显生动。春桃在一旁偷笑:“**,沈少帅采草药的样子,
倒比陆少爷顺眼多了。”温心嗔怪地看了她一眼,指尖却不由自主地抚上发间的雏菊。
那花瓣上的露水早已干透,却仿佛还带着他方才目光掠过的温度。当沈梵将石韦递过来时,
她注意到他小臂的伤口又渗出血迹,慌忙从竹篮里取出草药:“这是止血的,
我帮您重新包扎吧。”山间的风带着艾草的清香掠过,将她的声音送进沈梵耳里,
他看着她低头捣药时认真的侧脸,忽然觉得,这古寺的草药香,或许比南京城的香水味,
更让人牵念。第三章:府邸深处的误会晨雾尚未散尽时,
温心已将祖父留下的药箱擦拭得锃亮,春桃蹲在地上整理药包,
鼻尖萦绕着当归与川芎的混合香气:“**,这大帅府可不是寻常地方,
听说门槛都比别家高半尺呢。”温心将最后一味三七放进药箱,
指尖抚过箱角那道浅浅的裂痕,那是祖父十年前为沈老夫人诊病时,
不小心磕在门槛上留下的。温心:“祖父说,医者眼里只有病患,没有高低,
她将药箱上的铜锁扣系好,老夫人的喘疾得用晨露炮制的枇杷叶,我们得赶在辰时前到。
”黄包车穿过朱雀大街时,温心掀起车帘一角,街对面的洋行正在卸货,
西装革履的买办与挑着担子的小贩擦肩而过,喇叭声与吆喝声搅在一起,
像幅被揉皱的西洋画。她忽然想起沈梵说过的哥特式教堂,不知那些尖顶在晨雾里,
是否也这般藏着新旧交替的褶皱。大帅府的朱漆大门前,两尊石狮的眼睛被晨露洗得发亮,
门房验过帖子,引着她们穿过三进院落,回廊下的紫藤萝开得正盛,花瓣落在青石板上,
像铺了层紫色的云霞。温心的布鞋踩在花瓣上,悄无声息,
倒比引路小厮的脚步声更合这庭院的静谧。周嬷嬷:“老夫人正在偏厅歇着,温**这边请,
引路的老妈子掀起竹帘时,温心闻到一股浓郁的檀香,混着淡淡的西药味。
沈夫人孟清如半倚在紫檀木榻上,银白的发丝用翡翠簪绾着,看见温心,
浑浊的眼睛亮了亮:“可是知言先生的孙女儿?”温心:“正是晚辈温心,她放下药箱,
取出脉枕时,注意到榻边的西洋台灯亮着,灯罩上绣着繁复的缠枝莲纹,
中西合璧得有些刻意,诊脉的间隙,老夫人忽然抓住她的手,
指腹摩挲着她腕间的银镯子:“你祖父当年为我诊病,总说我这病得靠三分养。她叹了口气,
目光落在窗外的石榴树上,“那树还是他亲手栽的,说开花时能安神。
”温心顺着她的目光望去,石榴树的枝桠刚抽出新绿。她取出银针,
指尖稳如磐石:“老夫人放宽心,今年的新叶比往年旺,病气也能跟着散,
正当她准备施针时,院外传来一阵轻快的笑语。一个穿着月白色洋装的女子提着裙摆跑进来,
珠花在发间晃动,像只振翅的蝴蝶:“姑母,您看我给您带了什么好东西?
”温心的手顿在半空,那女子径直走到榻前,亲昵地挽住老夫人的胳膊,
发间的香水味瞬间盖过了药香,她瞥见温心时,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审视:“这位是?
”孟清如:“这是温先生的孙女,来给我瞧病的,老夫人拍了拍她的手,“瑶儿,
快见过温**。”孟瑶这才懒洋洋地颔首,目光落在温心沾着药渍的布裙上,
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原来是温**,久仰,我叫孟瑶,是梵表哥的表妹。
”“表哥”二字刚出口,院外便传来皮鞋踏过青石板的声响,温心抬头时,
正看见沈梵穿过紫藤萝架走来,他脱下沾着晨露的西装外套,搭在臂弯里,
里面的白衬衫解开了两颗纽扣,露出锁骨处淡淡的疤痕——那是上次为护她擦伤的地方。
“表哥你可算回来了!”孟瑶立刻迎上去,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外套,
指尖有意无意地擦过他的手腕,“我从巴黎带了新的香水,你闻闻喜不喜欢。
”沈梵的目光越过她,落在温心身上时,脚步顿了顿,药箱敞开着,
里面的银针在晨光下闪着微光,她的指尖还捏着未用完的艾草,侧脸在檀香里显得格外素净。
他正要开口,却见温心低下头,将银针放回药盒,动作快得像是在躲避什么。沈梵:“祖母,
这位是,沈梵的目光转向孟瑶,语气听不出情绪。孟瑶:“这是温**,来给姑母诊病的,
孟瑶挽住他的胳膊,发间的珠花蹭到他的衬衫,说起来,温**看着倒像是哪家的闺秀,
怎么会做这走方郎中的营生?”温心的指尖在药箱锁扣上掐出红痕。
她看见孟瑶与沈梵站在一起的模西洋装与白衬衫,香水味与烟草香,像画报上剪下的人物,
般配得让人心头发涩,原来他身边的女子,是这般明艳照人的模样。
孟清如:“瑶儿不得无礼,老夫人在榻上轻咳两声,温**的祖父是名医,
比那些西洋大夫靠谱多了。”沈梵正要再说些什么,
却见温心已背起药箱:“老夫人的脉象已平稳许多,晚辈先回了,明日再来换药,
她的声音比往常更低,像被晨露打湿的蛛丝,轻轻一碰就要断。沈梵:“我送你,
沈梵下意识地迈步,却被孟瑶拉住:“表哥,你答应陪我去看新到的西洋画的,她转向温心,
笑容里带着几分得意,“温**怕是不认得路吧,让下人送你便是。”温心没有回头,
只是拉着春桃快步穿过回廊,紫藤萝的花瓣落在她的布裙上,像些无声的叹息,
她听见身后沈梵的声音:“瑶儿,我还有事,脚步声响了几下,又被孟瑶的笑语盖过。
走出大帅府的朱漆大门时,春桃终于忍不住:“**,那孟**分明是故意的!
您没看见她看您的眼神,温心:“嘘,我们是来诊病的,不该管旁人的闲事。
”她抬头望向街角的槐树,新叶在风里轻轻摇晃,像极了方才沈梵眼中一闪而过的复杂情绪。
而此刻的偏厅里,沈梵正将孟瑶递来的香水瓶放在案几上,
声音恢复了惯常的清冷:“以后不要在病人面前说这些,他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
我还有事,先走了。”孟瑶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将香水瓶狠狠砸在地上,
玻璃碎裂的声响里,她看见夫人孟清如正闭目养神,嘴角却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廊下的石榴树影落在地上,像幅被揉皱的画,藏着谁也说不清的心事。
温心的黄包车行到朱雀大街时,忽然下起了小雨,她掀起车帘,看见街角的洋行门口,
沈梵正站在雨里打电话,白衬衫已被雨水打湿。他的目光越过人群,似乎在寻找什么,
直到黄包车拐过街角,那道身影才消失在雨幕里。春桃递过油纸伞:“**,
您的眼眶怎么红了?”温心摇摇头,将脸埋进带着药香的衣袖里,雨水敲打着车篷,
像首没有结尾的曲子,她忽然想起沈梵说过的那句话——“梵心,
你的名字像是早就等在这里。”原来有些等待,只是她一厢情愿的错觉,
药箱里的枇杷叶沾了雨气,散发出淡淡的苦味,像极了此刻的心情。
第四章:巷尾的竹篮温心把最后一页信笺压进樟木箱时,春桃正踮着脚往窗台上摆草药。
薄荷的清香混着松烟墨的气息漫在屋里,却压不住檐角那只信鸽咕咕的叫声。春桃:“**,
沈少帅的信又送来了。”春桃戳了戳信鸽脚上的银环,“这已经是第三封了,
您真要一直搁着?”温心没抬头,指尖抚过樟木箱里祖父留下的裱画工具,
牛角马蹄刀的弧度被磨得温润,像藏着无数个在古寺灯下修复画心的夜晚,
她将那叠印着西北邮戳的信笺推到箱底,压上块绣了一半的平安符——针脚歪歪扭扭的,
是那日从大帅府回来后绣的。温心:“就说我病了,不便见客,她抽出张宣纸铺在案上,
研墨的动作却比往常重了些,墨汁在砚台里晕开,像朵化不开的乌云。
这已是沈梵第五次派人来请了,前两次说古寺修复遇到难题,后两次托词送新得的拓片,
温心都以“祖父药圃需得照料”为由推了。今早更甚,秦风竟送来株半开的绿萼梅,
花枝上还系着张字条,字迹凌厉却带着几分刻意的柔和:“寺后梅开,似温姑娘所植。
”春桃抱着那株绿萼梅进来时,花瓣上的露水正顺着瓷瓶往下滴,
在青砖地上洇出小小的水痕:“**您看,这梅枝修剪的手法,
倒跟您给寺里的腊梅剪枝时一个样。”温心的笔尖猛地一顿,浓墨在宣纸上晕成个墨团,
她想起那日在崖壁下,
沈梵为采石韦划破的西装裤;想起他掌心的温度透过止血粉的纸包传来时,
自己发烫的耳根;更想起大帅府里,孟瑶挽着他胳膊时,
两人站在一起的画面——像西洋镜里走出的人,衬得她这布裙沾着药渍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