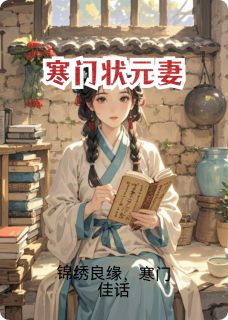
1红妆薄嫁暮春的雨丝斜斜织着,打湿了沈清沅单薄的衣料。
她立在沈家后门的青石板路上,看着那顶连红绸都泛着旧色的小轿被两个力夫抬着,
不情不愿地往巷口走,轿帘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仅有的一床粗布喜被。“晦气东西,
总算打发出去了。”管事嬷嬷尖刻的声音从门内传来,“也不瞧瞧自己什么身份,
竟想穿三姑娘剩下的那件藕荷色嫁衣,也配?”清沅攥紧了袖中的那支旧银簪,
是娘亲留给他的唯一念想。指尖深深掐进掌心,却感觉不到疼。从她记事起,
大娘的巴掌、冷饭、寒衣就是家常便饭,如今将她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穷书生做填房,
不过是觉得她留在府里碍眼,不如换几两银子给二房的表哥做束脩。
轿子晃晃悠悠走了半个时辰,停在城南最破败的巷子口。没有鼓乐,没有贺客,
只有一个穿着洗得发白青布长衫的老妪在门口等候,见了轿夫忙不迭地塞了两个铜板,
又颤巍巍地来扶她下轿。“姑娘……哦不,媳妇,快进屋吧,外面风大。”老妪声音嘶哑,
咳嗽了两声,“我家阿砚去给先生送文章了,回头就回来给你赔罪。
”清沅低着头跟着她走进低矮的土坯房,
屋内陈设简单得近乎寒酸:一张缺了腿用石头垫着的方桌,两把摇摇晃晃的椅子,
东厢房的门帘破旧不堪,隐约能看见里面铺着稻草的床榻。唯一像样的,
是西厢房里堆满的书册,整整齐齐码在靠墙的木板上,散发着淡淡的墨香。“让你受委屈了。
”老妪拉着她的手,枯瘦的手指带着病气的微凉,“阿砚他是个好孩子,
就是家里穷……我这身子骨也不争气,总拖累他。这次急着娶亲,实在是我这病越来越重,
他要去京城赶考,家里总得有个人照看。”清沅这才知道,自己要嫁的书生姓张名砚,
字景行,是个自幼丧父、靠乡邻接济才读得起书的寒门学子。他母亲张氏常年卧病,
这次催着完婚,原是想让她代为侍奉汤药。正说着,门外传来轻快的脚步声,
一个身着青衫的年轻男子推门而入。他身形挺拔,眉目清朗,虽面带倦色,眼底却亮得惊人,
看见屋里的清沅时微微一怔,随即拱手作揖,声音温润如玉:“在下张砚,
让姑娘……娘子受委屈了。”他没有丝毫轻视,也没有半分不耐,只是坦然地迎上她的目光,
那双眼睛干净得像雨后的天空。清沅的心莫名一跳,慌忙低下头去,脸颊微微发烫。
新婚之夜没有红烛高燃,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在桌案上跳动。张砚将西厢房收拾出来给她住,
自己则搬到了母亲床边的小榻。临睡前,他端来一盆热水:“路上辛苦了,泡泡脚暖暖身子。
”清沅看着他蹲在地上,将她的脚轻轻放入温水里,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对待稀世珍宝。
她长这么大,从未有人对她这般好,鼻尖一酸,眼泪险些掉下来。“以后有我在,
不会再让你受委屈。”张砚抬头看她,眼底是化不开的认真,“待我金榜题名,
定风风光光把你接进状元府。”清沅望着他俊朗的侧脸,在心里悄悄点了点头。或许,
这场看似不幸的婚事,会是她苦尽甘来的开始。2陋室温情婚后的日子清贫却安稳。
张砚每日天不亮就起身温书,清沅则早早起来烧水做饭,伺候婆婆喝药。张氏的病时好时坏,
常常整夜咳嗽,清沅便守在床边,随时准备着递水拍背,往往一夜只能睡上两个时辰。
张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夜里读书累了,总会轻手轻脚到母亲房外看看,
见清沅伏在床边打盹,便取件外衣给她披上。白日里若得了空闲,便帮着她劈柴挑水,
不让她累着。“这些粗活我来就好。”他夺过清沅手里的木柴,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
“你在家照看母亲,读些书解闷便是。”清沅知道他是怕自己辛苦,
却更心疼他既要备考又要操劳。她偷偷学着做针线活,将自己陪嫁的几件旧衣拆了,
改做成厚实的棉袜,又在张砚的长衫肘部、膝盖处都打上补丁,让衣服更耐穿些。一日,
张砚从书铺回来,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女诫》,
有些不好意思地递给她:“听闻娘子幼时也读过书?这书虽旧了些,你若无事,可拿来看看。
”清沅接过书,指尖抚过磨损的书脊,眼眶微微发热。在沈家时,大娘从不许她碰笔墨,
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如今张砚却主动让她读书。她抬头望他,见他耳根微红,
正有些局促地搓着手,忍不住弯了弯唇角。日子在柴米油盐和笔墨书香中缓缓流淌。
张砚要去京城参加春闱的日子越来越近,家里的积蓄却日渐微薄。为了给母亲抓药,
张砚常常去书铺抄书到深夜,回来时冻得手脚冰凉,清沅便把他的手揣进自己怀里暖着,
再端出温在灶上的热粥。“景行,这是我攒的月钱。”出发前夜,
清沅将一个沉甸甸的布包塞到他手里,里面是她偷偷做针线活换来的几十文钱,
“路上要保重身体,莫要省着吃食。”张砚看着布包里整齐叠放的铜钱,
又看看她眼底的青黑,喉结滚动了几下,将她紧紧拥入怀中:“沅沅,辛苦你了。待我归来,
定不负你。”他的怀抱温暖而有力,带着淡淡的墨香,清沅靠在他胸前,听着他沉稳的心跳,
轻声道:“我等你回来。”第二日天未亮,张砚便背着行囊上路了。清沅站在巷口,
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晨雾中,直到再也看不见,才抹了抹眼角的泪,转身回家。她知道,
从今天起,这个家,她要独自撑起来了。3风雨骤至张砚走后,清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白日里要伺候婆婆汤药,洗衣做饭,夜里还要借着月光做针线活换钱。张氏心疼她,
常常想帮忙,却总被清沅按回床上:“娘,您好好养病就是对我最好的帮衬。
”春日的天气反复无常,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张氏的病骤然加重。夜里发起高烧,
浑身滚烫,说胡话,咳嗽得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清沅急得团团转,
家里仅有的几文钱早就买了药,如今连请郎中的钱都没有。她跑遍了邻里,求了东家求西家,
可大家都是穷苦人家,自身难保,哪里有余钱帮衬。看着婆婆烧得通红的脸,
呼吸越来越微弱,清沅的心像被刀剜一样疼。“娘,您撑住,我这就去请郎中。
”清沅咬着牙,将家里最后一点口粮盖好,锁了门便往沈家跑。她知道此行必定难堪,
可眼下只有这一条路了。沈家的朱门紧闭,清沅跪在门前,一遍遍地求着:“大娘,
求求您发发慈悲,借我些钱给婆婆治病吧,等景行回来一定还您!”许久,侧门才开了条缝,
管事嬷嬷探出头来,满脸嫌恶:“哪来的叫花子,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们夫人说了,
你既已嫁出沈家,就不是沈家的人,死了也与沈家无关!”“嬷嬷,求您行行好,
我婆婆快不行了!”清沅膝行上前,想去拉嬷嬷的衣角,却被她一脚踹开。“滚开!
别脏了我们沈家的地!”嬷嬷招呼着两个家丁,“给我打出去,省得在这里晦气!
”棍棒落在身上,疼得清沅眼前发黑。她蜷缩在地上,死死护着头,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倒下,娘还等着救命。不知挨了多少下,
她被家丁像拖死狗一样扔出了巷口,额头磕在石阶上,渗出的血混着雨水流进眼里,
**辣地疼。她挣扎着爬起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却不敢停留。她想起张砚曾提过,
城外的报恩寺有位原恩方丈,医术高明,常常免费为穷苦人看病。咬着牙,她踉跄着往家跑。
回到家,她简单包扎了伤口,背起昏迷的婆婆就往城外走。从城南到城外报恩寺有十几里路,
她平日里走平地都吃力,如今背着一个人,更是举步维艰。泥泞的土路湿滑难行,
她摔了不知多少跤,膝盖磨破了,手心也被碎石划破,却死死咬着牙不肯放手。“娘,
再坚持一下,我们就快到了。”她喘着粗气,声音嘶哑,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往下淌。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林子里传来鸟兽的叫声,她怕得浑身发抖,却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不知走了多久,终于看见报恩寺的山门。清沅眼前一黑,抱着婆婆栽倒在山门前,
昏迷前只听见寺门“吱呀”一声开了。4菩萨心肠清沅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寺内的厢房里,身上的伤口已经被妥善包扎。窗外传来诵经声,
她挣扎着坐起身,就见一个小和尚端着药碗走进来:“施主醒了?方丈说你伤得不轻,
让你再歇会儿。”“小师父,我婆婆呢?”清沅急切地问。“老夫人在隔壁厢房,
方丈正在为她诊治,施主放心吧。”小和尚将药碗递给她,“这是方丈配的药,
施主趁热喝了。”清沅接过药碗,温热的药汁滑入喉咙,带着淡淡的苦味,
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流。她挣扎着下床,想去看看婆婆,刚走到门口,
就看见一位身着灰色僧袍、面容慈祥的老和尚正从隔壁出来。“女施主不必多礼。
”原恩方丈双手合十,目光温和,“老夫人已无大碍,只是积劳成疾,需得好生静养。
贫尼已开了药方,你且按方抓药,按时服用即可。”“多谢方丈救命之恩!
”清沅“扑通”一声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大恩大德,民妇没齿难忘!”“施主慈悲,
危难之际仍不忘孝亲,这份心已是难得。”方丈扶起她,“出家人慈悲为怀,施主不必挂怀。
只是老夫人身子虚弱,山路难行,你们今日便在此歇息,明日再下山吧。”清沅感激涕零,
留在寺中照顾婆婆。张氏醒来后,得知是儿媳背着自己走了十几里山路求医,
心疼得直掉眼泪:“是我这老婆子拖累你了……”“娘说的哪里话,儿媳照顾您是应该的。
”清沅为她掖好被角,“等景行回来,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在寺中休养了两日,
张氏的精神好了许多。清沅谢过方丈,又留下自己那支唯一的银簪作为谢礼,方丈推辞不过,
便收下了,却回赠了一包草药,嘱咐她若日后有难处,可再来寺中。母女俩相互搀扶着下山,
回到家时已是傍晚。清沅刚收拾好屋子,准备去抓药,就听见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她抬头望去,只见张砚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口,青衫上沾着尘土,眼底满是疲惫,
却在看见她的瞬间亮了起来。“沅沅,我回来了!”张砚快步上前,想抱抱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