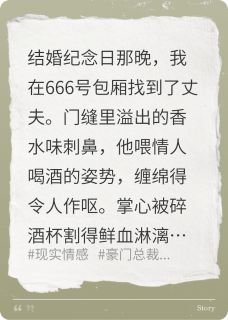
结婚纪念日那晚,我在666号包厢找到了丈夫。门缝里溢出的香水味刺鼻,
他喂情人喝酒的姿势,缠绵得令人作呕。掌心被碎酒杯割得鲜血淋漓,
剧痛中我意外觉醒了看穿情感的能力。丈夫身上的粉雾正紧紧缠绕着情人,
而我腕间象征婚姻的红绳早已断裂成灰。
婆婆冲进病房狠狠甩我一耳光:“自己拴不住男人怪谁?
”她没看见——自己颈后深蓝的雾带,正悄然缠向年轻的男保姆。
当离婚协议甩在丈夫面前时,整个豪门都在笑我不知好歹。
直到我当众播放他勾结医生替换我妈救命药的录像。
他腕上象征罪孽的黑带突然疯狂暴涨:“**,你早该跟你妈一起死!
”我微笑着亮出那晚包厢的录音:“你猜法院嗑哪对CP?
”异能界面赫然弹出:“情感链接成功收割,
道德审判系统已激活——”【第一章】结婚纪念日那天,我像个拙劣的笑话,
独自驱车驶向城市的另一端。导航屏幕上,
那个刺目的终点——皇冠酒店的VIP666包厢——像一只嘲讽的眼睛,钉在我的视线里。
三天前,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彩信照片,击碎了我摇摇欲坠的婚姻堡垒。照片模糊,
但足够清晰:我的丈夫秦昭,优雅地捏着高脚杯,喂向身侧一个年轻女孩微张的唇,
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姿态里透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缱绻。背景,正是这间镶着金色门牌的包厢。
方向盘冷得像冰,窗外流光溢彩的街景在我眼中扭曲、模糊,又重归冰冷。我想起出门时,
化妆镜里自己那张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双眼下是熬夜照顾生病母亲积累的青黑。
我特意穿了件昂贵但款式老套的连衣裙,期望能唤起他些许旧日温情?真是愚蠢至极。
侍者引路的皮鞋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空气里漂浮着劣质香水和残留酒气的混合味道,
浓得几乎让人窒息。终于,那扇厚重华丽、门牌号闪着金光的包厢门近在咫尺。门虚掩着,
一道狭长的暖黄色光线,像窥探者的眼缝,从中泄漏出来。我停住了脚步。
不需要推开那扇门了。从那道缝隙里,清楚地传出了秦昭带着宠溺的低沉笑声:“慢点喝,
小心呛着。”然后是另一个娇俏的女声,
甜腻得能拉出丝来:“人家就是想试试这酒什么味道嘛……唔,秦总喂的,
特别甜……”声音,画面,气味,在此刻汇集成尖锐的冰锥,狠狠扎进我的心脏。
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在瞬间冻结、倒流,冲向头顶,又在下一刻轰然坠向深渊。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强烈的恶心感扼住了我的喉咙。就在这时,
包厢内突然传出清脆的“哐当”一声,像是酒杯落地碎裂。“哎呀!
人家笨手笨脚的……”那女声惊呼。“小调皮,”秦昭的声音带着笑意,温柔得可怕,
“没事,再开一瓶就是……”——砰!理智的弦彻底崩断。身体先于意识做出了反应,
那扇沉重的、象征着我婚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门,被我猛地推开,门板撞在墙上,
发出巨大的哀鸣。包厢内,金碧辉煌的水晶吊灯闪烁着俗气又刺眼的光芒。
昂贵的浅金色地毯上,猩红的酒液正在肆意蔓延,像血。
一个穿着水红色吊带亮片裙的年轻女孩惊呼着后退一步,大片酒渍浸染了她胸前轻薄的衣料。
而秦昭,正拿着一块方巾,温柔地替她擦拭着手腕,动作轻缓得如同擦拭一件稀世珍宝。
听到门口的巨响,两人同时抬头,脸上虚伪的笑意尚未褪尽就僵住了。秦昭看清是我,
眼底划过一丝惊讶,随即被浓重的不耐烦和阴鸷取代。他直起身,
原本擦拭女孩手腕的手指蜷了一下,又松开,只是冷冷地看着我,那种目光,
比陌生人的更让人心寒。像是在看一件突然闯入的不速之物,一件惹人厌烦的垃圾。“宋晓?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他的声音没有一点温度,甚至带着质问。世界被按下了静音键。
水晶灯耀眼的光芒变得模糊,秦昭那张英俊却写满冷酷的脸在我视野里摇晃,
还有那个年轻女孩眼底迅速升腾起的、混合着惊惶和隐秘得意的表情。
周遭的一切声音潮水般退去,只剩下我自己心脏在肋骨下疯狂撞击的闷响,
还有血液冲击太阳穴的轰隆声。愤怒?羞辱?绝望?不,
是更深沉的东西——一种被彻底愚弄、价值被践踏到尘埃里的死寂的冰冷。“我?
我怎么找来的?”我的声音听起来那么遥远,那么陌生,干涩得像砂纸摩擦,“大概是因为,
今天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我的、好、丈、夫?”最后四个字,
我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秦昭脸上瞬间掠过一丝极其不自然的僵滞,
随即被更深的恼怒取代。他薄唇紧抿,下颌线绷得死紧,没再看我,
反而带着一种刻意的偏袒,把那个受惊小鸟似的女孩往后挡了一下,动作充满了保护的意味。
那杯泼在女孩身上的酒,此刻仿佛全都泼在了我的脸上,**辣地烫。
空气里的甜腻酒味和她的香水味混合着,简直是一场嗅觉酷刑。胃里翻涌得更厉害了。
我下意识地向后踉跄一步,手肘撞到了门旁边壁龛里一个装饰用的细长水晶高脚杯。
它摇晃了一下,摔了下来。咔嚓——!!一声刺耳的爆裂!锐利的碎片在我眼前炸开,
冰冷的液体飞溅。几乎是本能地,我下意识地伸手想去挡飞溅的碎片。
手心陡然传来一阵尖锐到无法言喻的剧痛!“嘶——”我倒抽一口冷气,猛地缩手低头。血,
鲜红的血,正汩汩地从我下意识挡开碎玻璃的手心涌出来。
几块尖锐的碎片深深嵌进了皮肉里,掌心一道狰狞的割伤皮肉翻卷,
甚至能看到一点暗色的东西。剧痛如同烧红的烙铁,瞬间烙印在我所有神经末梢。
就在这剧痛达到顶峰的零点几秒——一种奇怪、冰冷、非人般的嗡鸣声猛地在我颅腔内炸响!
眼前的世界骤然失去所有颜色,视野里的一切物体边缘都像是蒙上了一层扭曲的灰色毛玻璃!
随后,铺天盖地的晕眩和一种从骨髓深处弥漫开来的冰冷感,瞬间将我吞没。
耳边的所有声响——秦昭的低喝,女孩的惊呼,侍者的询问——都变得遥远而模糊不清,
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隔音玻璃。身体里的力量被瞬间抽干,眼前最后看到的画面,
是秦昭带着惊疑的脸猛地凑近,然后,
整个世界彻底沉入了纯粹的、无声无息、冰冷刺骨的黑暗深渊…………不知道过了多久。
意识像是沉在冰冷粘稠的泥沼里,一点一点艰难地向上挣扎。眼皮沉重得如同灌了铅。
鼻腔里充斥着浓烈的消毒水气味,无处不在,冰冷而枯燥。喉咙干得冒烟,
每一次微弱的吞咽都像砂纸摩擦。“……醒了?呵,我还以为你这一撞,
终于把自己撞清醒了!”——啪!一记带着十足力道和厌憎的耳光,狠狠扇在我的脸颊上!
清脆,响亮!脸上**辣地痛,瞬间盖过了掌心的钝痛,耳朵里嗡嗡作响。
被抽离的意识被迫重新凝聚。我猛地睁开眼,视线还有些模糊,像蒙着水雾。
一个保养得宜、穿着昂贵香奈儿套裙、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的老妇人站在床边,
居高临下地盯着我,眼神像是淬了毒的针,刻薄又阴冷。那是秦昭的母亲,我的婆婆,
林凤霞。她身后,还站着两个穿着黑色西装、面无表情的保镖模样的男人,
像两座冰冷的门神。“妈……”我下意识地想张口,嘴角牵扯着肿痛的脸颊,声音干涩嘶哑。
“闭嘴!”林凤霞厉声打断,她的目光像冰锥一样刺在我的脸上,
毫不掩饰其中的鄙夷和愤怒,“宋晓,你真是我秦家门楣上最大的耻辱!堂堂秦家的太太,
像个泼妇一样跑去捉奸?还把自己弄进医院?呵,弄得人尽皆知,
让整个圈子都看我们秦家的笑话!你自己拴不住男人,除了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还会干什么?怪谁?啊?!”她尖利的声音在单人病房里回荡,
每一个字都像鞭子抽打在我的尊严上。旁边病床上的人早已被“请”走,
这里成了她一个人的审判场。那两个黑衣人像铁塔一样堵住了门。手心剧痛依旧,
脸也**辣地疼。绝望像冰冷的蛇缠绕上来。然而,就在这巨大的屈辱和绝望之中,
那股在包厢掌心剧痛时炸开的、奇异冰冷的感觉,再次涌现!这一次,更加清晰,
仿佛某种压抑已久的东西被这记耳光彻底激活!我的视野核心骤然像投入石子的湖面,
猛地漾开了一圈无法抗拒的、非人的灰色涟漪,迅速向四周扩散覆盖!
眼前原本鲜明真实的场景陡然蒙上了一层淡灰色的滤镜!所有人的实体轮廓都在模糊,
唯有……色彩!一股股不同色调、细若游丝、闪烁着奇异光芒的“烟雾”或者说是“光带”,
竟从眼前所有活人的身体不同部位……飘了出来!我心脏猛地一抽,
恐惧和一种离奇的、巨大的荒谬感攫住了我。我死死盯住林凤霞。
只见在她头顶、肩颈的位置,正盘绕着一股凝实、散发着幽幽深蓝光泽的“雾气”带子,
像是有生命的藤蔓,缓慢地蠕动着。而更令我惊悚的是——这股深蓝色的雾带,它的一头,
紧紧缠绕着她自己的颈项,像是某种冰冷诡异的蛇环。
而另一端……竟然在空气中划出一道细长的弧线,如同被无形的磁石吸引,
执着又贪婪地……缠绕、锁闭在林凤霞身后那个年轻男保姆,手腕的袖扣位置!
那个保姆低着头,看似恭敬,但那道蓝雾的链接却像实质的锁链,将两人隐秘地捆绑在一起!
那蓝色深邃得像冰冷的深海,透着一股……沉沦粘腻的占有欲?这……这是什么?
而林凤霞对我喷着毒液的嘴巴里,并没有任何……嗯?“光带”?链接?
更诡异的是视线下移——我看清了自己的手腕。没有深蓝,没有粉红,
只有一种……黯淡、枯萎、破碎的灰烬色,在我左手腕间凝聚成一圈断裂的绳索残骸?
冷硬、死寂,仿佛早已被焚毁多年。“贱骨头!”林凤霞刻毒的谩骂将我震回现实,
“还不起来收拾你闯下的祸?昭儿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要不是他拦着,
你以为你能这么舒舒服服躺这儿?”她伸手过来,尖利的指甲似乎想再掐我一把,
“快给我……”那浓郁的深蓝色雾带随着她的动作摇曳扭动。
就在她的指尖几乎碰到我手臂的刹那,一股极其抗拒的意念在我心中汹涌爆发:不!
不要碰我!嗡……掌心那道狰狞的伤口深处,骤然传来一股细密如针扎般的锐痛!
不是医院处理的钝痛,是内在的、源于骨头的冰寒痛楚!同时!
那深蓝色雾带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强烈的斥力,“嗤啦”一下猛烈地扭曲后退!
林凤霞触碰的动作僵在半空,脸上闪过一丝极其古怪的错愕,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烫了一下,
下意识地猛地缩回了手,眉头紧紧皱起。她身后那个年轻男保姆,
更是微不可察地后退了半步,一直低头看着鞋面的脑袋抬了一下,眼神惊疑地扫过我。
冰冷蔓延的感觉越发清晰。我能感知到那股冰冷源自我受伤的掌心,像无数细小的冰晶,
沿着我的血管在向手臂侵蚀。很痛,刺骨的痛。但更强烈的,
是一种灵魂被剥离观察自己躯壳般的奇异超然。我低下头,避开林凤霞那几乎要喷火的目光,
左手悄悄攥紧了身下被消毒水气味浸透的病床床单,指甲深深陷了进去。
掌心伤口的每一次细微牵扯,都伴随着那非人的冰针之痛。
我看着林凤霞依旧不断开合的嘴唇,声音却仿佛来自很遥远的地方。
看着手腕上那圈代表婚姻契约、却早已断裂枯萎成灰烬色的“红绳”残骸。
还有林凤霞和她保姆之间,
那根深蓝黏腻、无法斩断的奇异纽带……一种混杂着极度荒谬、深入骨髓的冰冷,
以及某种荒诞绝伦的兴奋感,突然冲垮了刚才的绝望和无力感。
这世界……原来是这副鬼样子?就在这时,病房门被不轻不重地推开了。【第二章】门开处,
颀长的身影立在光暗交界的门口。秦昭来了。深灰色的昂贵手工西装一丝不苟,
衬得他身姿笔挺。头发精心梳理过,不见一丝包厢里的狼狈。
脸上也重新戴上了惯有的、那副完美且疏离的面具,唯有眼底深处,
残存着一线几乎不可察觉的阴翳,那是被我撞破好事后的怒意被强行压服的回响。“妈。
”他声音低沉平静,听不出任何波澜,
仿佛之前包厢里喂情人红酒、缱绻温存的那个人根本不是他。他淡淡扫了我一眼,
那眼神冰冷如刀锋刮过皮肤,没有丝毫温度,
更没有半分对一个躺在病床上、脸颊红肿、手掌缠着厚厚纱布的妻子的……担忧。只有审视,
以及被拖累后的厌恶。林凤霞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立刻换上一副委屈又严厉的表情:“昭儿你看看她!把你害成什么样了!
秦家的脸都被她丢光了!醒了就给我装死,我看她是心虚!”她矛头再次指向我。
秦昭没理会他母亲的控诉,
边病床上摆着的、那只装着染血碎片和药水纱布的医用托盘上——那是我伤口处理后的证据。
他眉头极轻微地蹙了一下,像是在评估着什么麻烦,随即视线才重新落回我脸上,或者说,
是落在我缠满纱布的手上。“伤怎么样?”声音平淡得像在询问一件物品的状态,
甚至没有半点关切该有的起伏。不等我回答,
他那冰冷的、不容置喙的声音紧接着压下:“公司那边我让文凯处理了,
对外会说你不慎在家摔倒。最近你就好好待在疗养院静养,别出来乱跑。
需要什么让张姐给你送。媒体那边……”他微微一顿,眼神里划过一丝更深的厌烦和警告,
“你管好自己,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最好心里有数。”疗养院静养?说的好听,
是隔离,是软禁!是让我在这个丑闻风口躲起来,别碍他的眼,
别妨碍他做秦家的好儿子好总裁!一股强烈的荒谬感混杂着冰冷的怒意冲上我的头顶。
我几乎想笑,想放声大笑。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一丝不苟、虚伪到令人作呕的脸。
就在这一刻,那股源于掌心的、针扎般的冰冷痛楚再次清晰地蔓延开来!
指尖瞬间如同浸入了万年冰窟,冻得麻木刺痛。视野里的灰色滤镜再次幽幽泛起涟漪!
我死死地盯着秦昭。在他挺拔、象征着精英与掌控力的西装之下,
靠近心脏的位置……浓郁的、甜腻得几乎令人窒息的粉红色雾带,正盘踞在他的胸前,
缓缓流动、纠缠着。那粉色透着一股低劣的人工合成的艳俗感。而那条粉色的光带,
一头深扎进他心脏的位置,另一头,则……如同贪婪的触手,
顽强地、跨越空间般地延伸出去,朝着某个遥远的方向延伸……那方向,赫然正是皇冠酒店!
那是他的情人!那条丑陋的粉色纽带,连接着他和那个吊带裙女孩!我心脏重重一跳,
一股冰冷的恶心感攫住喉头。然而,就在这浓烈到刺眼的粉色旁边,
我清晰地看到——另一条细得几乎要忽视的、黯淡得如同灰尘凝聚成的、灰白色的线状雾气,
勉强地粘连在他的左肩。那灰白的线微弱、飘渺、死气沉沉,
仿佛只需轻轻一吹就会彻底消散,毫无生气。它连接的另一端,
轻轻搭在了我的……小臂绷带边缘。是那条早已断裂的、只剩灰烬残骸般的“婚姻绳索”!
这就是我们五年的婚姻!浓艳恶心的偷情粉,与这条苟延残喘、随时可能断掉的死灰之线?
讽刺到极致!目光再移向秦昭的面部。他那双深邃的眼睛,本应是情绪外显的窗口,
此刻在我这“异变”的视野里,却空空如也!那张英俊的、正在对我宣布软禁指令的脸上,
没有属于我的情感纽带?没有一丝一毫真正关乎于我宋晓的情绪在流动?只有冰冷算计!
只有被拖累的厌烦!没有爱,没有关心,甚至没有多少真实的愤怒!只有对麻烦的厌恶!
他所有的温情,他的心,他的情愫,都系在了那条艳俗粉红的带子上!
属于我的那一点点可怜的灰烬,早已被他弃如敝履,视若空气!“……心里有数。
”他结束了宣判,最后三个字带着冰棱般的锋锐。这股冰冷的荒谬感,
终于压过了所有愤怒和羞辱,化为一种从骨髓深处涌出的清醒和决心。像最锋利的冰锥,
破开了笼罩在我眼前五年的迷雾。我慢慢抬起头,用尽力气扯动了一下嘴角。
脸上被扇过的地方还在**辣地疼,手心伤口在纱布下传来钻心的冰与火的刺痛,
但这些痛楚,此刻都成了催生决心的燃料。“秦昭,”我的声音意外的平静,
甚至带着一丝疲惫的喑哑,完全出乎林凤霞的预料。她没有听到预想中的哭闹或哀求。
我直视着他那张冰冷完美的面具,一字一顿,清晰地说道,“我们离婚吧。”声音不大,
在安静的病房里却像一块巨石投入寒潭!死寂。林凤霞倒抽一口冷气,眼睛瞬间瞪圆,
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荒谬的笑话!她那精心描绘过的眉毛高高挑起,
随后是几乎要掀翻房顶的尖刻讽刺:“离婚?宋晓!我看你不仅是摔伤了手,
怕是连脑子也一起摔坏了?!你是个什么东西?离了秦家你算个什么?敢提离婚?
昭儿没休了你就是天大的恩德!你这没用的东西,连个蛋都下不出来,还有脸提离婚?
你……”她还要继续恶毒地喷吐,秦昭却缓缓抬起了手。只是一个微小的动作,
林凤霞像被无形的绳子勒住喉咙,剩下的话硬生生噎了回去,只是胸膛剧烈起伏着,
怨毒地死盯着我。秦昭脸上那完美的面具,终于出现了一丝极其细微的裂痕。不是慌乱,
不是挽留,而是一种被人先行冒犯、超出掌控的意外和……羞辱?他盯着我,
那双深邃的眼眸里寒潭涌动,冻结一切光芒,嘴角却极其轻微地扯动了一下,
形成一个极度冷漠的、如同看待一场滑稽戏的弧度。“你说什么?
”低沉的声音带着一种淬了冰的压迫感,仿佛空气都骤然降了几度。掌心伤口深处,
那冰针般的锐痛随着我意志的决绝,似乎变得愈发清晰、锐利!
它似乎……与我的情绪、我的精神力共振了!寒意顺着小臂攀爬,在指尖凝聚。
我看着手腕上那圈黯淡灰烬色的婚姻残骸,又扫过他那根浓艳粉红的情欲纽带。“我说,
”我吸了一口气,将心中翻涌的无数冰冷讽刺强行压下,目光像穿透他虚假外壳的探针,
一字一句复述:“秦、昭、我、们、离、婚。”“呵,
”一声极轻、极冷的单音从秦昭喉咙深处滚出。他眼底最后一丝惊异被彻骨的寒意覆盖。
他向前走了一步,阴影笼罩住我半靠在病床上的身体,压迫感扑面而来。
那双眼睛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冰井,要将人的骨血都冻结。“宋晓,
”他用一种极度低沉的、如同宣判终末的声音,
缓缓道:“看来是医院把你惯得不知天高地厚了。离婚?你以为你有资格提这两个字?
”他微微俯身,带着上位者天然的压制气息,
冰冷的气息几乎喷在我的脸上:“想想你那个躺在普通病房等死的妈?
想想你们家那点摇摇欲坠的小生意?你以为签了婚前协议,你就能从我这里分走什么?
还是你觉得,闹这么一出捉奸的丑剧,外面就有哪个不知死活的野男人肯接你的盘?
”每一个字都淬着毒,准确无误地扎向我最脆弱无助的地方!我妈!
那高昂的医疗费是悬在我头上的剑!还有婚前协议里冰冷的条款!心脏猛地一抽,
一种窒息般的屈辱和愤怒几乎要冲破喉咙。但下一秒,手掌心伤口的剧痛骤然尖锐数倍!
那股非人的冰冷仿佛瞬间冻结了我的血管和怒火,
同时也带来一种异乎寻常的清醒——异能视野里,
他心脏位置那根浓艳粉红的情欲纽带剧烈地翻涌扭曲,似乎在配合着主人的暴戾。而他脸上,
依旧没有任何与我直接相关的情绪纽带显现!他的愤怒只来源于权威被挑衅!
他只想将我打入深渊!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影出现在病房门口。
是秦昭的首席秘书,李文凯。他脸上带着一种职业化的、恰到好处的急促和恭敬,
微微低头:“秦总,抱歉打扰。您母亲那边的……王医生和院方刚送来的加急复查结果,
需要您马上去特需医疗中心那边确认一下。情况……有些变化。”特需医疗中心?
那是林凤霞常年做“专项保健”的豪华套间。秦昭身形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李文凯出现的时机太“凑巧”,但这理由涉及林凤霞,他无法立刻驳回。
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那眼神如同锁定了猎物的秃鹫,充满了警告和秋后算账的意味。随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