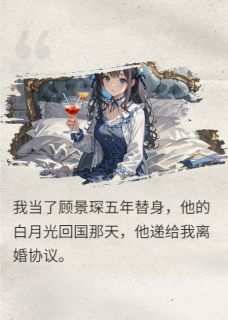
我当了顾景琛五年替身,他的白月光回国那天,他递给我离婚协议。“她身体不好,
你搬去客房睡。”我看着他为白月光戴上祖传玉镯,那是我跪了三天祠堂都没求来的。
1、顾景琛的白月光从国外回来了,我五年的替身生涯像个笑话。他递来离婚协议时,
连眼风都吝啬给我:“念薇身体弱,你今晚就搬去客房。
”我看着他小心翼翼扶那朵娇弱白莲,心像被钝刀子反复切割。更讽刺的是,
三天前我跪在顾家冰冷祠堂,只为求他母亲认可,但换来的,却是一句“你不配”。
而那枚象征传承的羊脂玉镯,此刻正套在林念薇纤细的皓腕上,温润流光,刺得我眼睛生疼。
后来,我躺在手术室冰冷床上,身下鲜血蔓延如狰狞的彼岸花,护士一遍遍问他电话,
得到的只有忙音。他正陪他的白月光,在山顶看一场据说能带来永恒幸福的流星雨。
心死成灰,不过如此。直到某天,顶级豪门沈家动用整版报纸头版,
只为寻回他们流落在外二十余年的真千金。2、离婚协议书是顾景琛亲手放在我面前的,
深灰色大理石桌面映着白纸黑字,像一纸冰冷的讣告,宣告我五年的婚姻正式死亡。
他骨节分明的手指压在纸页边缘,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
这曾是我无数次小心翼翼描摹的轮廓,此刻却只让我觉得冷。“念薇回国了。”他开口,
声音是一贯的低沉平稳,听不出半分涟漪,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她身体一直不太好,
受不得**。你,今晚就搬到客房去。”我捏着温热的牛奶杯,指尖却冷得发颤,
牛奶是我习惯每晚给他温好端上来的。五年。一千八百多个夜晚,从未间断。
杯壁的热度烫着掌心,心口却空荡荡地灌着冷风,我抬起头,目光掠过他线条冷硬的下颌,
试图在那双深邃的眼眸里找到一丝一毫的迟疑或愧疚。没有。只有一片漠然。
像结了冰的深湖。“客房?”喉咙有些发紧,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顾景琛,这里,
是我们的主卧。”也是我一点点布置起来的家,窗台的绿萝,床头柜上成对的马克杯,
墙角的懒人沙发……每一处都有我笨拙却倾注了全部心血的痕迹。
他眉心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似乎我的反问是一种不识趣的纠缠。“苏晚,”他叫我的全名,
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别让我重复第二遍。念薇需要静养。”他话音未落,
卧室虚掩的门被一只涂着精致裸粉色甲油的手轻轻推开。林念薇。
她裹着顾景琛那件宽大的黑色羊绒开衫,更显得身形纤细柔弱,楚楚可怜。
她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歉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目光扫过我手中的牛奶杯,
声音又轻又软,像羽毛搔刮着人心:“晚晚姐,对不起……都怪我身体不争气,
刚下飞机就头晕得厉害,景琛哥太紧张了,非让我先躺一会儿……”她说着,
身子还微微晃了一下,像风中孱弱的柳枝。顾景琛几乎是立刻丢开了那份离婚协议,
一个箭步上前,稳稳扶住了林念薇的腰。那份紧张与呵护,
是我五年婚姻里从未得到过的奢侈品。他的动作快得带起一阵风,吹动了协议书的边角,
也彻底吹凉了我最后一点微末的期待。“说了让你躺着别动!”他的责备里浸满了心疼,
低头看着林念薇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缱绻。林念薇顺势依偎进他怀里,
脸颊贴着他的胸膛,目光却越过他宽阔的肩膀,直直地落在我脸上。那眼神,
哪里还有半分柔弱?带着**裸的挑衅和胜利者的炫耀,唇角勾起一抹极淡、极冷的笑意,
无声地宣告着**。而顾景琛,他的全部注意力,他所有的温情,
此刻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在怀里的女人身上。我,苏晚,这个他法律上的妻子,
此刻像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旧家具,碍眼又多余。他扶着林念薇,
小心翼翼地让她坐在我曾夜夜独守的那张KINGSIZE大床边缘,
那动作珍视得如同对待稀世珍宝。我的枕头被他随意地拂到了一边,
为林念薇腾出更舒适的位置。“景琛哥……”林念薇的声音黏腻得能拉出丝,她抬起手腕,
轻轻撩了一下垂落的发丝。就在那一瞬间,一道温润柔和的流光刺痛了我的眼睛!
那枚羊脂玉镯!通体无瑕,凝脂般温润,在灯光下流转着内敛而尊贵的光华。
那是顾家祖传的宝贝,只传给当家主母。我记得太清楚了,就在三天前,
为了得到顾家一点微末的认可,我跪在顾家老宅冰冷阴森的祠堂里整整一天一夜,
膝盖肿得无法弯曲。换来的却是顾景琛母亲刻薄的冷笑和一句掷地有声的审判:“苏晚,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肖想我顾家的传家宝?”那镯子,我跪断了膝盖都没资格碰一下的宝贝,
此刻却如此随意、如此理所当然地圈在林念薇纤细的腕子上。顾景琛甚至没有看我一眼,
他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另一个人,连同我卑微祈求而不得的“认可”,也一并双手奉上。
心口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然后猛地撕开,
剧烈的疼痛伴随着强烈的窒息感瞬间淹没了我。眼前的一切,顾景琛专注的侧脸,
林念薇腕上刺目的玉镯,他们依偎的身影都变得模糊、扭曲。手中的牛奶杯再也握不住,
“哐当”一声脆响,砸落在地毯上,温热的液体溅湿了我的裤脚,留下深色的、难看的污渍。
顾景琛终于被这声响惊动,皱着眉看过来。那眼神里没有关心,
只有被打扰的不悦和一丝……厌烦?像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林念薇则低低惊呼一声,
像是被吓到了,更紧地往顾景琛怀里缩去。空气凝滞得令人窒息。地毯上蔓延的奶渍,
狼狈不堪,如同我此刻的人生。那碎裂的声响,仿佛是我心底最后一道防线崩塌的声音。
“出去。”顾景琛的声音冷得像冰,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是对我这个“闯入者”下的最后通牒,“收拾干净,立刻搬走。
”3、那杯打翻的牛奶像一个恶兆,拉开了我地狱般生活的序幕。
从主卧被驱逐到阴冷的客房,只是第一步。这间房在走廊尽头,终年晒不到多少阳光,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像是灰尘和遗忘混合的味道。
我简单的生活用品被粗暴地塞进两个纸箱,像丢垃圾一样堆在门口。
顾景琛的助理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监督:“顾总吩咐,请您动作快些,林**需要安静休息。
”我沉默地弯腰抱起沉重的箱子,纸箱粗糙的边缘硌着掌心。搬进这间囚笼般的客房,
我用了不到十分钟。关上门,背脊抵着冰凉的门板,才感觉到身体深处传来的、迟来的颤抖。
环顾这间屋子,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一个积灰的旧衣柜,唯一的窗户对着隔壁高耸的楼宇,
光线吝啬。这里,连我精心养护在窗台的那盆绿萝都没有容身之地。
它被遗忘在主卧的窗台上,和那对马克杯一起,成了林念薇新领地的点缀。顾景琛的世界,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抹去“苏晚”存在过的所有痕迹。而林念薇,
则成了这座宅邸当之无愧的新女主人。她以身体需要调养为名,口味变得极其挑剔。
早餐的粥要熬到米粒开花、温度恰好入口;午餐的汤必须用文火煨足四个时辰,
撇净每一丝油花;晚餐则要求清淡精致,少盐无糖。张妈是顾家的老人,做了几十年饭,
也被她挑剔得手足无措,私下里红着眼眶叹气。“晚晚姐,
”林念薇总是这样亲昵又疏离地叫我,声音甜得发腻,带着一种主人般的随意,
“景琛哥说你会做很棒的酒酿圆子?我这两天特别想吃点甜甜的暖胃呢,
外面的总觉得不干净,辛苦你帮我做一碗好不好?”顾景琛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
膝上摊着平板处理邮件,闻言头也不抬,仿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要求。我沉默地走进厨房,
糯米粉揉成团,搓成小小的圆子,酒酿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水汽氤氲中,
我看着锅里翻滚的小圆子,眼前却模糊一片。曾几何时,我也满怀爱意地为顾景琛做过这个,
那时他尝了一口,只淡淡说了句“还行”,如今,却要我为他的心上人洗手作羹汤。
一碗热气腾腾的酒酿圆子端到林念薇面前,她用小勺舀起一颗,秀气地吹了吹,送入口中。
下一秒,她眉头蹙起,捂着嘴,发出一声短促的干呕。“咳…咳…晚晚姐,
”她眼圈瞬间红了,楚楚可怜地看向顾景琛,“这酒酿…味道好像有点怪?
是不是…不太新鲜了?”顾景琛立刻放下平板,紧张地拍抚她的背,眼神锐利如刀地射向我,
带着毫不掩饰的斥责:“苏晚!你怎么回事?不知道念薇身体弱吗?做点东西都做不好!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这酒酿是昨天才买的。可看着他眼中全然的信任和心疼都给了林念薇,
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可笑,最终,我只是麻木地垂下眼:“抱歉,我重做。”羞辱并未停止。
几天后,顾家举办一场重要的商业晚宴。我原本以为这种场合,
我这个即将下堂的妻子不会被允许出席。然而,顾景琛却亲自敲开了客房的门。“收拾一下,
晚宴你需要出席。”他语气平淡,像是在下达一项工作任务。“为什么?”我下意识地问。
难道他不怕林念薇看到我不高兴?他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
带着一种评估物品价值的审视,随即移开,声音毫无波澜:“念薇身体还没恢复,
这种场合需要应酬,她撑不住。你,”他顿了顿,“比较合适。”原来如此。
我“比较合适”去替他真正的爱人挡掉那些觥筹交错的疲惫,去扮演一个体面的花瓶,
一个合格的挡箭牌,心像被泡在冰水里,冷得麻木。我翻出衣柜里最昂贵的一条香槟色长裙,
这还是结婚三周年时,我咬牙用攒了很久的稿费买的。对着镜子,我仔细地描画妆容,
试图掩盖眉眼间挥之不去的疲惫和苍白,镜中人影绰约,却空洞得像个没有灵魂的玩偶。
宴会在顾家别墅的花园举行。水晶灯璀璨,衣香鬓影。我挽着顾景琛的手臂入场,
能感受到四面八方投射来的、带着探究、怜悯或是幸灾乐祸的目光。
林念薇回国的消息早已传开,我这个“正室”的处境,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从来不是秘密。
顾景琛全程保持着疏离而客套的微笑,与人寒暄。他的手放在我的腰间,
动作标准得像礼仪教科书,却感受不到一丝暖意,只有冰冷的控制。
当有相熟的长辈笑着打趣:“景琛和晚晚还是这么般配,什么时候给我们顾家添个孙辈啊?
”顾景琛脸上的笑容淡了些,握着酒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他没看我,
只对着长辈淡淡回应:“王叔说笑了,我们还年轻,不急。”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不是为他否认孩子,而是为他语气里那份急于撇清的漠然。仿佛与我孕育后代,
是什么难以启齿的污点。就在这时,林念薇出现了,她穿着一身纯白色的定制小礼服,
裙摆蓬松,像个不谙世事的公主。她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柔弱和一丝病态的苍白,
在顾景琛母亲的亲自陪同下,缓缓步入会场。顾母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宠溺和骄傲,
紧紧握着林念薇的手。她们的出现,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窃窃私语声更大了些。
顾景琛几乎是立刻松开了我的手臂,毫不犹豫地大步朝林念薇走去。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真实而温柔,带着小心翼翼的呵护。他自然地接过顾母的手,
亲自扶着林念薇,低声询问着什么,眼神专注得仿佛全世界只剩她一人。我僵在原地,
手臂上还残留着他方才的力道,此刻却空空荡荡。香槟塔折射的碎光落在我身上,
却驱不散那瞬间将我吞噬的寒意和孤立。那些探究的目光变得更加**,像无数根针,
密密地扎在我**的皮肤上。“哟,这不是顾太太吗?
”一个尖细的女声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在身旁响起。是顾家一个远房亲戚,向来刻薄。
“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景琛这是……去陪那位林家**了?”她故意拉长了调子,
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周围一圈人都能听见。周围的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瞬,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带着审视、同情,更多的是看好戏的玩味。我挺直脊背,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尽全身力气维持着最后一丝体面,
强迫自己露出一个无可挑剔的、空洞的微笑:“林**身体不适,景琛去照顾一下是应该的。
”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是吗?”那女人掩嘴轻笑,眼神像毒蛇的信子,
“顾太太真是‘大度’。就是不知道,这顾家女主人的位置,还能‘大度’多久?
”周围的低笑声像细小的砂砾,磨砺着神经。我脸上的笑容几乎要挂不住。“晚晚姐,
”林念薇不知何时被顾景琛扶着走了过来,声音柔柔弱弱,带着歉意,“真是不好意思,
都怪我扫了大家的兴。景琛哥非不放心我一个人待着……”她小鸟依人地靠在顾景琛身侧,
腕上那枚羊脂玉镯在灯光下流转着温润却刺目的光晕。顾景琛一手揽着她的肩,目光扫过我,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告,仿佛在提醒我注意言行,不要“**”到他珍贵的宝贝。
他对林念薇温声道:“你最重要,别管别人。”那声音里的宠溺,像一记响亮的耳光,
狠狠扇在我脸上。“别人”……原来,我已经是“别人”了。就在这时,
一个侍者端着托盘经过,上面是几杯颜色漂亮的鸡尾酒。林念薇似乎被那颜色吸引,
好奇地伸手想去拿一杯。顾景琛立刻阻止她:“念薇,你身体刚好点,不能喝酒。
”林念薇嘟起嘴,带着点撒娇的意味:“就尝一小口嘛,那个蓝色的,像海洋之星,好漂亮。
”“不行。”顾景琛语气温柔却坚决。林念薇眼珠一转,目光落到我身上,
忽然绽开一个甜美的笑容:“那……晚晚姐,你替我喝一杯好不好?就当我敬你的,
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她的话音刚落,顾景琛的目光也落在我身上,
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示意。仿佛替他的心上人挡酒,是我此刻唯一存在的价值。
周围的目光再次聚焦,带着看戏的玩味,那杯蓝色的鸡尾酒被递到了我面前,
杯壁凝结着冰冷的水珠。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几乎无法跳动。
替身、保姆、挡箭牌……现在还要加上一个替酒的工具?屈辱感如同沸腾的岩浆,
在胸腔里翻滚冲撞。我看着那杯蓝色的液体,
又看向顾景琛冷漠的眼神和林念薇眼底那抹清晰的、恶意的挑衅。我知道,如果我拒绝,
只会换来顾景琛更冰冷的斥责和在场人更肆无忌惮的嘲笑。
为了那可笑的、早已荡然无存的“体面”,为了不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彻底崩溃……我伸出手,
指尖冰凉,接过了那杯沉重的酒杯。冰冷的触感从指尖蔓延到全身。
在顾景琛理所当然和林念薇得逞的目光注视下,在周围无数双眼睛的围观下,
我将那杯蓝色的、象征着羞辱的液体,仰头灌了下去。冰凉的酒液滑过喉咙,像刀割一样。
那味道,苦涩得难以下咽。胃里瞬间翻江倒海,一股强烈的恶心感猛地涌上喉头。
我慌忙捂住嘴,强烈的反胃感让我控制不住地弯下腰,干呕出声。
“呕……”周围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变得惊愕、探寻,
然后迅速转化为一种心照不宣的了然和更深的鄙夷。“天,
她这是……”“不会是……有了吧?
”“顾景琛不是才……”细碎的议论声如同毒蜂的嗡鸣钻进耳朵。
顾景琛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看向我的眼神不再是冷漠,
而是充满了震惊、怀疑,以及一种被冒犯的、极致的厌恶!仿佛我此刻的失态,是故意为之,
是为了在众人面前给他难堪,是为了破坏他和林念薇!他猛地一步上前,
粗暴地抓住我的手臂,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
他完全不顾我的干呕和瞬间惨白的脸色,也完全无视了周围所有的目光,
像拖拽一件垃圾一样,强硬地将我拽离了宴会中心璀璨的灯光,
一路拖向花园最偏僻、最阴暗的角落。“苏晚!”到了无人处,他狠狠将我甩开,
力道之大让我踉跄着撞在冰冷的廊柱上,后背一阵剧痛。
他高大的身躯带着骇人的压迫感逼近,阴影完全笼罩了我。他的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每一个字都淬着冰,带着滔天的怒火和被愚弄的屈辱,“你真是好手段!在这种时候,
玩这种恶心的把戏?你想干什么?嗯?让所有人都以为你怀了我的孩子?让念薇难堪?
让我下不来台?!”他眼底燃烧的怒火和毫不掩饰的鄙夷,像两把烧红的烙铁,
狠狠烫在我的心上,胃里还在翻搅,喉咙口的恶心感挥之不去,
但更痛的是他那字字诛心的话。“我没有……”我虚弱地反驳,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
小腹隐隐传来一阵坠痛,让我额角渗出冷汗。“没有?!”顾景琛冷笑一声,
那笑声里充满了极度的不信任和嘲讽,“苏晚,收起你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五年来,
我还不了解你?为了留在顾家,你还有什么做不出来?下药爬床的事情都干过,
现在装怀孕博同情?我告诉你,做梦!
”下药爬床……那被他刻意遗忘、扭曲了五年的新婚夜真相,此刻被他如此轻蔑地撕开,
当成攻击我最恶毒的武器,心脏像是被一只巨手狠狠撕裂,痛得我几乎无法呼吸,
眼前阵阵发黑。“你……”我张着嘴,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只有眼泪不受控制地汹涌而出,
混合着屈辱和灭顶的绝望,小腹的坠痛感越来越清晰,一股温热的暖流不受控制地涌出,
顺着腿根滑落。顾景琛还在盛怒之中,他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异样,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
他厌恶地别开眼,仿佛多看我一眼都嫌脏,语气冰冷决绝,下达了最后的判决:“苏晚,
你让我觉得恶心!明天,立刻、马上,给我滚出顾家!这里,一秒钟都不想再看到你!
”4、顾景琛那句裹挟着雷霆之怒的“滚出去”,狠狠扎进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
小腹的坠痛骤然加剧,仿佛有冰冷的钝器在里面疯狂搅动,
一股更汹涌的热流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瞬间浸透了薄薄的礼服内衬,
粘腻而冰冷地贴在皮肤上。剧痛让我眼前发黑,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我再也支撑不住,
顺着冰冷的廊柱滑坐在地,蜷缩起来,牙齿因为剧痛和寒冷而咯咯作响。
那杯蓝色的酒液在胃里翻腾,混合着灭顶的绝望,让我控制不住地干呕,却什么也吐不出来,
只有胆汁的苦涩灼烧着喉咙。“苏晚,”他的声音依旧冰冷,带着浓重的不耐,
“别在这里装死!要演苦情戏也换个地方!立刻起来,给我滚!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我身下深色地毯上晕开的、那抹不祥的暗红,或者说,他看见了,
却只以为是我拙劣表演的又一“道具”,故意弄脏自己来博取同情。
剧痛像潮水般一波波冲击着我的意识,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撕裂般的痛楚。我努力想抬起头,
想告诉他不是演戏,想求救,但喉咙像是被扼住,只能发出破碎的气音。视线里,
他那双曾经让我迷恋的、此刻却冰冷如寒潭的眼睛,越来越模糊。
“景琛哥……”林念薇柔弱又带着点惊慌的声音适时地传来。她不知何时跟了过来,
站在几步远的地方,捂着胸口,一副被吓到的模样。“晚晚姐她……她怎么了?
看起来好可怕……是不是……是不是因为我让她喝了酒?
都是我不好……”她自责地看向顾景琛,眼圈泛红。顾景琛立刻被她吸引,
脸上瞬间切换成安抚和心疼。他不再看我,大步走向林念薇,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
温柔地披在她肩上,将她护在怀里。“不关你的事,念薇。”他低声哄着,
语气是截然不同的温度,“是她自己不知分寸,在这种场合失态。别怕,我让人送她走。
”他说着,拿出手机,冷漠地拨通助理的电话:“安排两个人,立刻到花园东北角廊柱这里,
把苏晚‘请’出去。她身体不适,送她回客房休息,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她再出来一步。
”他刻意加重了“请”和“休息”的字眼,冰冷的命令像是对待一件需要清理的垃圾。
助理的动作很快,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面无表情地出现在我面前,
像两座没有感情的铁塔。他们一左一右架起我的胳膊,
毫不怜惜地将几乎虚脱的我从地上提了起来,我的双腿软得像面条,根本站不住,
脚尖无力地拖在地上。“顾……”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看向那个拥着林念薇、背对着我的男人。我想喊他的名字,想告诉他,
我们的孩子……可能没了……但剧痛再次席卷而来,眼前彻底陷入黑暗。
昏迷前最后的感知,是保镖粗暴的拖拽,
是林念薇依偎在顾景琛怀里投来的、那一道隐藏在柔弱下的、冰冷而快意的目光。
……意识在无边的黑暗和剧痛的撕扯中沉沉浮浮,不知过了多久,
刺鼻的消毒水气味强行钻入鼻腔,耳边传来模糊而焦急的对话声。“……病人大出血!
妊娠约8周,疑似不全流产!快,联系家属签字手术!”“家属?她丈夫呢?
电话一直打不通!”“紧急情况,先送手术室!准备清宫!通知值班领导签字!
”身体像是被抛进了冰冷的深渊,又被粗暴地拉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