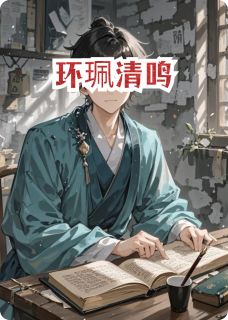
我穿成红楼贾环那天,正被赵姨娘掐着胳膊骂没出息。后来我六元及第,离京赴任扬州。
盐商宴上初见薛宝钗,她眼底有惊艳,却仍守着闺秀本分。我助林如海整顿盐务,
回京述职时已是天子新贵。荣国府夜宴,宝钗袖中滑落我当年题诗的扇子。
她垂眸:“环三爷如今位高权重,还识得旧物么?
”我接过扇子轻抚题诗处:“扬州初见,我便知金玉良缘是假,木石前盟难成。”窗外,
潇湘馆的琴声停了。---冰冷、尖利的指甲,像淬了毒的钩子,狠狠嵌进我胳膊的皮肉里。
“没出息的东西!烂泥扶不上墙!我赵彩霞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废物点心来!
”唾沫星子混着一股廉价脂粉的浓烈甜腥气,劈头盖脸地喷过来。我猛地睁开眼,
视线对上近在咫尺的一张脸。这张脸,敷着厚厚的粉,
却掩不住眼角的细纹和因刻薄而紧绷的嘴角。珠钗歪斜,
几缕油腻的鬓发散乱地贴在汗湿的额角。赵姨娘。脑子里嗡的一声,
无数不属于我的记忆碎片——屈辱的、阴暗的、带着浓重霉味的记忆——如同决堤的洪水,
轰然冲垮了我的意识堤岸。贾环!
那个在《红楼梦》里猥琐、嫉妒、永远活在宝玉阴影下的庶子贾环!
胳膊上的剧痛和耳边的咒骂无比真实。我成了他。成了这个在贾府夹缝里挣扎求生,
连亲生母亲都视作耻辱的贾环。“娘……”喉咙干涩发紧,我本能地发出一个音节,
声音虚弱得像蚊蚋。“别叫我娘!”赵姨娘的手指掐得更深,指甲几乎要陷进肉里,
她眼里的怨毒几乎凝成实质,“看看你!看看宝玉!人家是凤凰蛋,
是老太太、太太心尖尖上的肉!你呢?你就是那茅坑里的臭石头!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
我……”她越说越激动,另一只手扬起来,作势要打。就在那巴掌即将落下的一瞬,
我猛地侧头避过,同时用尽全身力气,将自己的胳膊从那铁钳般的指爪中挣脱出来。
动作太大,牵扯着身下这张硬得硌人的窄床吱嘎作响。我喘着粗气,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
目光迅速扫过这间逼仄、昏暗的屋子。墙角堆着几卷落满灰尘的旧书,
一张掉了漆的桌子歪斜着,唯一的一扇小窗糊着发黄的窗纸,透进些微惨淡的光。
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劣质脂粉的混合气息。这里是贾环的屋子,
在贾府东北角最偏僻的角落,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赵姨娘被我突然的挣脱弄得一愣,
随即那刻薄扭曲的脸上涌起更大的怒火:“反了你了!小畜生,还敢躲?
看我不……”“母亲息怒。”我打断她,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
努力模仿着记忆里贾环唯唯诺诺的腔调,但眼神却不再闪躲,
而是直直地看向她那双燃烧着怨毒火焰的眼睛。我知道,在这个吃人的地方,示弱是常态,
但毫无底线的懦弱只会招来变本加厉的践踏。我需要一点改变,哪怕只是一点姿态。
我的目光扫过墙角那几卷蒙尘的书,“儿子……儿子昨夜温书,睡得迟了些。
”这个借口苍白无力,甚至有些可笑。“温书?”赵姨娘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滑稽的笑话,
尖厉地嗤笑一声,唾沫星子几乎溅到我脸上,“就你?也配说温书?别污了圣贤的名头!
你那猪脑子,识得几个大字?装模作样给谁看?有这闲工夫,不如去太太跟前好好巴结巴结,
学学怎么讨口饭吃!”刻毒的话语像鞭子抽在心上。我垂下眼睑,
掩住眼底翻涌的冷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算计。“母亲教训得是。”我低声应道,
手指在粗糙的薄被下暗暗攥紧。贾府,这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深潭,
底下是吃人的规矩和森严的等级。一个庶子,
尤其是一个被所有人轻视、被亲生母亲鄙弃的庶子,想要活下去,想要改变什么,
唯一可能的出路,只有那一条——科举。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在这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科举是庶民乃至庶子唯一能撬动命运的杠杆。而我的脑子里,
装着远超这个时代的庞大知识库。八股?经义?策论?
那些令无数读书人皓首穷经、视为畏途的东西,在我眼中,
不过是需要背诵、理解和熟练运用的工具罢了。“哼!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赵姨娘见我服软,又狠狠剜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再骂也无趣,终于扭着腰肢,
带着那股浓郁的廉价脂粉气摔门而去。破旧的木门发出不堪重负的**,重重合上,
隔绝了那令人窒息的声音。狭小的空间里重新陷入昏暗和寂静,
只留下胳膊上几道深红的指痕和挥之不去的脂粉甜腥气。我缓缓坐起身,靠在冰冷的墙壁上,
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的霉味似乎都带着腐朽的、属于贾环过往的绝望气息。科举。
只有科举。这个念头像黑暗中燃起的一点星火,虽微弱,却无比清晰坚定地照亮了前路。
我掀开身上那床散发着陈腐气味的薄被,赤脚踩在冰冷粗糙的地面上,一步步走到墙角。
那几卷书,是前身贾环不知从哪里淘换来的旧书,
或许是他短暂萌生又被现实无情碾碎的某个渺茫念头留下的唯一痕迹。我蹲下身,
拂去厚厚的灰尘。《论语》、《大学》、《孟子》……书页泛黄卷边,
散发着经年累月的霉味。我小心翼翼地拿起最上面那本《论语》,翻开。
那些竖排的繁体字映入眼帘,有些陌生,却又在记忆深处奇异地熟悉起来。
前世累积的庞大阅读量和分析能力开始高速运转,那些佶屈聱牙的句子、微言大义的解释,
如同被拆解的精密零件,在脑海中迅速归位、重组、理解。没有先生,没有笔墨纸砚,
甚至没有一盏像样的油灯。只有这陋室,这残卷,还有一颗被逼到绝境后,
骤然清醒、燃烧着冰冷火焰的心。窗棂透进的光线越来越暗,最后只剩一片模糊的灰影。
我蜷缩在墙角,借着最后一点天光,手指在冰冷的书页上无声地划过,一个字,又一个字,
贪婪地汲取着。黑暗彻底笼罩了斗室,我闭上眼睛,那些字句却在脑海中越发清晰,
如同烙印。路,开始了。---晨光熹微,带着深秋特有的清寒,
透过窗棂上那层发黄变脆的旧纸,吝啬地洒进这间狭小阴暗的屋子。
空气里弥漫着隔夜的冷寂和挥之不去的淡淡霉味。我早已起身,
身上裹着那件洗得发白、浆得发硬的旧棉袍,坐在那张摇晃不稳的桌子前。
桌面上铺开一张粗糙发黄的毛边纸,旁边是半块磨得只剩指头大小的劣墨,
一支秃了毛的旧笔,还有一小碟清水权当砚台。窗外,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喧嚣,
那是荣国府的主子们起身洗漱、丫鬟仆妇们穿梭奔忙的声音,是另一个世界的晨曲,
与这角落的孤寂格格不入。我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得喉咙有些发紧。凝神,提笔。
笔尖蘸了蘸清水调开的稀薄墨汁,悬在纸的上方。指尖因寒冷而微微颤抖,但落笔的瞬间,
手腕却异常稳定。横、竖、撇、捺……没有名家法帖可供临摹,没有名师指点结构章法。
有的,只是记忆中那些印刷体的方正骨架,以及此刻心中对“规矩”二字最深刻的理解。
每一笔都力求工整,每一划都刻板到近乎僵硬。这不是书法,这是生存的烙印。贾环的字,
就该是这般笨拙、拘谨、毫无灵性可言,却又挑不出大错的模样。“吱呀——”一声轻响,
破旧的木门被推开一条缝,探进一张怯生生的小脸。是彩霞,
赵姨娘身边唯一一个还肯对贾环稍假辞色的丫鬟,眉眼清秀,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同情。
“环三爷,”她声音压得极低,带着清晨的寒气,“该去给老太太、太太请安了。
”她手里捧着一个粗陶小碗,碗里是半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薄粥,上面飘着几片蔫黄的菜叶。
我停下笔,将那张写满规矩字体的毛边纸小心地压在桌角一本旧书下,这才转过身。
脸上早已换上贾环惯有的那种畏缩、呆滞的神情,眼神也刻意放空了些。“嗯,知道了。
”我应了一声,声音有些沙哑,接过那碗冰冷的粥。粥几乎没什么温度,
粗糙的米粒混着菜叶的涩味滑过喉咙。彩霞默默站在一旁,看着我把粥喝完,
眼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放下碗,我跟着彩霞走出这间冰冷的囚笼。穿过一道道回廊,
绕过花木扶疏的庭院,越靠近荣庆堂,空气里那股富贵繁华的气息便越发浓郁。雕梁画栋,
锦幔珠帘,捧着铜盆、香炉、手巾把子的丫鬟们垂首敛目,脚步轻捷地穿梭着,
行动间带起细微的香风。荣庆堂正房内,暖意融融。
上好的银霜炭在巨大的铜胎珐琅火盆里无声燃烧,散发出干燥温暖的气息。
檀香和脂粉的甜香混合着,弥漫在空气中。贾母歪在正中的大炕上,身上盖着织金锦被,
几个衣着鲜亮的大丫头正围着她,或捶腿,或捧茶。
王夫人、邢夫人、王熙凤、李纨等一干媳妇并宝玉、黛玉、三春姐妹等小辈,
都已按次序肃立在下首。我跟着彩霞,悄无声息地溜到人群最末、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
垂手站定。目光低垂,盯着自己洗得发白的袍子下摆和那双旧布鞋的鞋尖。像一滴浑浊的油,
努力融入这片锦绣的海洋,却又格格不入。宝玉正凑在贾母跟前,不知说了句什么俏皮话,
逗得贾母搂着他心肝儿肉地笑,满屋子都是轻松快活的气氛。王夫人坐在贾母下首的椅子上,
手里捻着一串油亮的佛珠,脸上带着端庄温和的笑意,目光偶尔扫过宝玉,
那笑意便更深几分。然而,当她的视线不经意地掠过角落时,那温和便瞬间凝滞了一下,
如同平静的湖面落下一粒微尘,随即又恢复如常,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
但那瞬间的冷淡和漠然,却像一根细小的冰针,精准地刺入我的感知。我屏着呼吸,
将头垂得更低,肩膀微微缩起,努力把自己缩成一个毫无存在感的影子。贾环,就该是这样。
沉默,畏缩,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阴郁气息,让人看一眼都觉得败兴。
请安的过程冗长而沉闷。贾母心情好,拉着宝玉说了好一会儿话,又问了黛玉和三春几句。
王熙凤妙语连珠,不时引得满堂哄笑。我始终站在那个角落里,像一截沉默的木桩。
没有人看我,没有人问我,仿佛我根本不存在。直到贾母显出倦意,挥了挥手,
众人这才如蒙大赦,行礼告退。走出荣庆堂那温暖得令人窒息的空间,深秋的寒气扑面而来,
反而让我精神微微一振。正待随着人流默默走开,
一个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环儿。”我脚步一顿,
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瞬,随即缓缓转过身,
脸上迅速堆起那种带着讨好和怯懦的假笑:“父亲。”贾政穿着一身家常的石青色直裰,
负手站在廊下。他面容方正,蓄着短须,
眉宇间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清正和一丝挥之不去的官场沉郁。他看着我,
眼神里没有面对宝玉时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复杂,也没有面对赵姨娘时那种难以掩饰的厌烦,
只有一种纯粹的、审视物品般的平淡。仿佛在打量一件早已确认是劣等货色的物件,
连失望都懒得再生出。“嗯。”他淡淡应了一声,目光扫过我洗得发白的衣袍,
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近日书读得如何了?”声音平平,听不出丝毫关切,
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般的询问。心脏在胸腔里猛地一跳,随即又被强行按捺下去。
我飞快地抬眼瞥了一下贾政的表情,又迅速垂下,做出努力回忆的样子,
声音带着刻意的结巴和不确定:“回、回父亲,
儿子……儿子近日在读……读《孟子·告子下》篇。
”我特意选了一个相对基础、不易出错的篇章。贾政的眉头似乎皱得更紧了些,
眼神里掠过一丝不耐烦。显然,他对这个庶子读书的进度和效果毫无期待。“哦?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他随口接了一句,语气是带着考校意味的漫不经心。
我知道他在等我接下去背诵。若背得流利,或许会引来一丝诧异,
但更可能招致怀疑——一个素来愚钝的庶子,怎会突然开窍?若背得磕绊,
才符合他们的预期。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脸上露出几分紧张和努力思索的神情,
声音断断续续,带着刻意的停顿和些许混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空乏其身……呃……行拂乱其所为……”我故意漏掉了“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这一句关键,让整个背诵显得虎头蛇尾,不成章法。果然,
贾政眼中的不耐几乎要溢出来。他挥了挥手,像驱赶一只恼人的苍蝇:“罢了罢了!
连篇蒙童的章句都记不囫囵,何谈其他?回去好生用功!莫要整日里……”他顿了顿,
似乎觉得后面的话说出来都嫌浪费,只重重哼了一声,“去吧!”那一声“去吧”,
带着毫不掩饰的厌弃。我如蒙大赦,连忙躬身行礼:“是,父亲教训的是,儿子记住了。
”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惶恐和唯唯诺诺。直到贾政转身走远,我才慢慢直起身,
指尖在袖中早已掐得发白。回到那间冰冷的小屋,关上门。
方才在荣庆堂的暖意和贾政冰冷的审视带来的双重压抑感,才稍稍散去。我走到桌边,
掀开压着的旧书,露出下面那张写满字的毛边纸。上面工整刻板的字体,
此刻看起来充满了讽刺。光靠藏拙和模仿前身的愚钝是远远不够的。科举之路,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需要的不是藏拙,是锋芒!是必须刺破云霄、让所有人无法忽视的光芒!
但这份光芒,必须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一个能让贾府接受、至少暂时不会带来灭顶之灾的范围内。我拿起那支秃笔,
重新蘸了蘸清水墨汁,在另一张毛边纸的背面,悬腕、凝神。笔尖落下,
不再是之前刻意模仿的笨拙刻板。点如坠石,横如千里阵云,
竖如万岁枯藤……前世记忆中那些曾临摹过的碑帖精髓,
那些属于另一个时空的笔锋流转、筋骨气度,如同沉睡的火山,在这一刻被压抑的野心点燃,
汹涌地灌注于笔端!笔走龙蛇,力透纸背。一个个结构严谨、神采内蕴的字体跃然纸上,
与正面的“贾环体”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这才是我的字!属于一个穿越者灵魂的印记!
写罢,看着那截然不同的字迹,我缓缓放下笔,眼中最后一丝伪装褪去,
只剩下冰冷燃烧的决绝。藏拙,是为了生存。而此刻笔下的锋芒,
是为了未来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条路,注定步步惊心。我拿起写满锋芒的纸张,
凑近桌上的油灯。豆大的火苗跳跃着,贪婪地舔舐上纸角。橘红色的火焰迅速蔓延,
将那力透纸背的锋芒,连同那个不能见光的秘密,一同吞噬。火光映亮了我半边脸,
另一半隐在浓重的阴影里。灰烬如同黑色的蝴蝶,在冰冷的空气中盘旋、坠落。
---日子在贾府这座巨大的、金碧辉煌的牢笼里无声滑过。晨昏定省,
我永远是那个站在最角落、垂着头、沉默得像一块背景板的庶子贾环。
赵姨娘的尖声咒骂依旧如影随形,是这牢笼里最刺耳的配乐。我学会了在她骂得最凶时,
眼神放空,思绪却早已沉入《四书章句集注》的义理分析,或是默诵《朱子语类》的精要。
她唾沫横飞的刻毒话语,成了我磨砺心性的另类“背景音”。那几卷蒙尘的旧书,
早已被我翻得卷了边,
书页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只有我自己能看懂的、用指甲掐出的微小印记——那是浓缩的笔记,
是提纲挈领的关键词。没有灯油,我便借着黎明前最微弱的天光,
或是傍晚西沉落日最后的余晖,贪婪地汲取着书上的每一个字。手指冻得发僵,
呵出的气在眼前凝成白雾,唯有心口那点不甘的火苗,
支撑着笔尖在冰冷的毛边纸上刻下一个个工整却毫无灵魂的“贾环体”字迹,
如同修筑一道掩人耳目的工事。真正的锋芒,深藏于脑海。每一次策论的构思,
每一段经义的推演,都在无人知晓的思维风暴中激烈碰撞。模拟的答卷,只存在于意识深处,
写罢即焚,不留半点痕迹。偶尔,在通往书房的僻静回廊,或是藏书阁落满灰尘的角落,
会与宝玉不期而遇。他身边总是簇拥着袭人、麝月等一群大丫头,或捧着新得的奇巧玩意儿,
或谈论着刚读的传奇话本。他穿着鲜艳的袍子,面如傅粉,唇若涂朱,
眉梢眼角天然一段风流,眼神清澈却又带着一种不谙世事的慵懒。有时,他会看到我,
那双漂亮的眼睛里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随即又归于一种近乎天真的漠然。
他或许会微微颔首,算是打过招呼,那动作优雅得无可挑剔,
却也疏离得如同隔着一道无形的琉璃墙。更多的时候,他只是被簇拥着从我身边走过,
带着一阵香风,留下几句关于“禄蠹”、“经济文章最是俗气”的议论,那声音清越动听,
却像细小的冰粒,砸在人心上。我停住脚步,侧身让道,垂首,敛目,做出恭敬的姿态。
在他和那群衣着光鲜的丫鬟们走过之后,才抬起头,看着他们消失在雕梁画栋深处的背影。
阳光穿过廊檐,在青石板上投下长长的、彼此分离的影子。我眼中没有愤怒,没有嫉妒,
只有一片深潭般的平静,映着这富贵风流,也映着这繁华背后的森严壁垒。“环哥儿?
”一个略显苍老却温和的声音自身后响起。我转身,
看见贾代儒老先生正从藏书阁的侧门走出来。他须发皆白,穿着半旧的深蓝色直裰,
背微微佝偻着,手里还拿着两卷书。他是贾府西席,也是族学里唯一的正经先生,
平日里教授族中子弟读书,只是学生大多顽劣,老先生也颇有些心灰意冷。“代儒先生。
”我连忙躬身行礼,态度恭敬。这位老先生学问或许不算顶尖,但为人方正古板,
是贾府里少数几个还肯真正讲点学问的人。
贾代儒浑浊的目光在我洗得发白的旧袍子上停留了一瞬,又落在我脸上,
带着一丝探究:“方才……是宝玉过去了吧?”他显然看到了方才那一幕。“是。
”我垂眼应道。老先生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种阅尽世情的无奈:“宝玉天资聪颖,
只是……心思不在此道啊。”他顿了顿,目光重新聚焦在我身上,“环哥儿,
你近日……可还在读书?”“回先生,学生愚钝,不敢荒废,只是……只是苦于无人指点,
许多地方懵懂不解。”我抬起头,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困惑和求知的渴望,
声音里透着一丝自卑的颤抖。贾代儒捋了捋花白的胡须,
眼中流露出一点微弱的、类似看到朽木尚存一丝纹理的兴趣:“哦?何处不解?说来听听。
”他大概也只是随口一问,并未抱太大期望。我心中微动,机会!
一个可以光明正大接触书籍、甚至可能得到些许指引的机会!
我立刻说出一个《大学》里关于“格物致知”的经典疑难,这个问题看似基础,
实则牵扯甚广,能问出这个,既显得我确实在认真读书,又不至于暴露太多锋芒。
贾代儒果然有些意外,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嗯?你竟看到此处了?”他沉吟片刻,
便站在回廊下,就着这个问题,简明扼要地讲解了几句朱子的注释。他的讲解中规中矩,
并无太多新意,但对于一个长期闭门造车的“愚钝”庶子来说,已是久旱甘霖。我凝神听着,
不时提出一两个看似幼稚、实则引导他深入的问题。贾代儒讲得兴起,
竟不知不觉多说了小半个时辰。末了,他看着我的眼神,少了几分疏离,
多了几分难得的温和赞许:“嗯……虽则愚钝,倒也有几分向学之心。总比那些……罢了。
”他摆摆手,似乎不想提那些顽劣的学生,“若有不解,可去族学寻我。
藏书阁东侧那排架子,有些浅显的集注,你……可以看看。”他指了指藏书阁的方向。
“多谢先生教诲!”我深深一揖,声音带着压抑的激动。这扇窄门,终于撬开了一道缝隙!
从那天起,藏书阁东侧那排落满灰尘的架子,成了我隐秘的宝藏。
那里大多是些基础的集注、浅显的史论,对真正的科举进阶用处有限,
却是我此刻唯一能光明正大接触的书籍来源。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
同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向贾代儒请教一些经过精心筛选、不会暴露我真实水平的问题。
老先生对我这“笨拙却勤恳”的庶子,态度也日益和缓,偶尔还会主动问起我的“功课”。
日子依旧在表面的沉寂和暗地里的疯狂汲取中流逝。转眼,便是三年一度的童生试之期。
考篮是彩霞偷偷帮我准备的,一个半旧的藤篮,里面装着几支最普通的毛笔,半块墨,
一方粗糙的砚台,还有几个硬邦邦的冷面饽饽。赵姨娘对此嗤之以鼻,
骂骂咧咧地断定我去了也是丢人现眼。贾政那边,更是连问都未曾问过一句。府里其他人,
或是不知,或是知晓了也只当是庶子又一次不自量力的笑话。考试那日,天还未亮透。
我独自一人,踏着深秋的寒霜,走出贾府那扇沉重的角门。没有送行,没有叮嘱,
只有守门小厮打着哈欠投来的、带着一丝嘲弄的懒散目光。贡院门前已是人山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