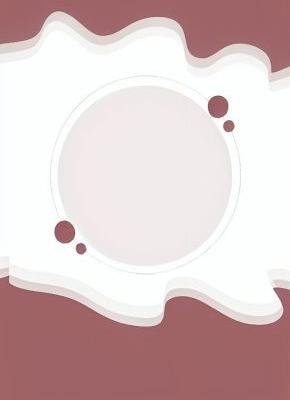
“不够。”
冰冷的两个字,像手术刀的刀尖,精准地扎在岑鸢(CénYuān)的神经上。
试镜厅内,空气凝滞。几十双眼睛聚焦在她身上,有同情,有幸灾乐祸,更多的是看戏的期待。
岑鸢半跪在冰凉的地板上,戏服单薄,手腕被道具手铐磨得发红。她扮演的是《深渊回廊》中被变态医生囚禁的女记者,此刻应该是她精神崩溃、哭喊求饶的重头戏。
她已经演了三遍。
第一遍,她声嘶力竭,泪水横流。
导演李诚皱眉:“太表面。”
第二遍,她眼神空洞,状若痴傻。
李诚摇头:“太刻意。”
第三遍,她压抑着啜泣,身体神经质地抽搐,眼神里混杂着恐惧与乞求。这是她能拿出的最好状态,她甚至在开拍前饿了自己一天,只为追求生理上的虚弱感。
可那个男人,只说了两个字:“不够。”
他坐在导演李诚旁边,身份是剧组的医学顾问。一个叫裴烬的医生。
他从头到尾没看过监视器,视线一直落在岑鸢身上,像在观察一个有趣的实验样本。他穿着一件质地精良的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的手腕干净、有力。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比试镜厅的空调还冷。
“李导,”裴烬终于开口,声音平稳,没有一丝波澜,“恐惧不是表演。它是一种生理应激反应。瞳孔放大,心率飙升超过150,血液会优先供应四肢核心肌群,导致末梢冰冷、指尖发白。她刚才的表演,心率大概在120,呼吸急促但有节律,这是典型的表演性激动,不是濒死感的恐惧。”
他像在宣读一份病理报告。
全场死寂。演员们面面相觑,一个医学顾问,在给准影后讲戏?
李诚导演却一脸信服,搓着手对裴烬说:“裴医生,那您看……怎么引导一下?”
裴烬站起身。
他很高,身形清瘦但挺拔,白衬衫衬得他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洁净感。他一步步走向岑鸢,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规律的声响。
每一步,都像踩在岑鸢的心跳上。
他在她面前蹲下,视线与她半跪的姿态齐平。一股淡淡的消毒水气味,混着他身上冷冽的木质香,钻进岑鸢的鼻腔。
“岑**,”他开口,声音很近,带着一种奇特的、耳语般的穿透力,“你怕疼吗?”
岑鸢一怔,下意识点头。
“很好。”他伸出手,不是碰她,而是从旁边的道具盘里,拿起了一把手术刀。
是真的手术刀。刀刃在灯光下反射出森白的光。
“啊!”一个胆小的女演员忍不住低呼出声。
裴烬置若罔闻。他用两根修长的手指捏着刀柄,将刀尖对准岑鸢的眼睛,距离不到五厘米。
冰冷的杀意,瞬间包裹了岑鸢。
这不是演戏。
她能清晰地看到刀尖上自己的倒影,那个因恐惧而扭曲的、渺小的自己。她甚至能感觉到刀刃带起的微风,拂过她的睫毛。
她的呼吸停滞了。大脑一片空白。
“看着它。”裴烬的声音像恶魔的低语,“想象一下,刀尖刺入你的角膜,穿过晶状体,搅碎你的视神经。不会很疼,因为神经末梢会被瞬间切断。你会先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下来,那是你的房水和玻璃体液。然后,世界会变成一片红色,再然后,彻底变黑。”
岑鸢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这不是演技,这是本能。
“不……不要……”她的声音嘶哑,带着哭腔,每个字都从喉咙深处挤出来。
“为什么不要?”裴烬的语气甚至带上了一丝好奇,像个在解剖青蛙的孩子,“失去视觉,可以让你更专注于听觉和触觉。或者,我们可以换个位置。”
他的手腕微微一动,手术刀的刀尖向下滑,停在她的喉咙前。
“这里是颈动脉。一刀下去,三秒钟内,你的大脑会因为缺氧而失去意识。你会看到一些很有趣的跑马灯,然后,一切归于平静。这是一种很……有效率的死法。”
“疯子……”岑鸢瞪大了眼睛,泪水终于决堤而出,不是因为悲伤,而是纯粹的、原始的恐惧。她想后退,可双腿发软,动弹不得。她能感觉自己的心跳声,像战鼓一样在耳边狂擂。
“对,就是这个眼神。”裴烬的嘴角,似乎勾起了一个几乎无法察效的弧度,“憎恨,恐惧,又带着一丝哀求。瞳孔放大,面部肌肉失控,牙关在打颤……生理指标基本达标了。”
他收回手术刀,随手扔回道具盘,发出一声清脆的“当啷”声。
那声音,像一个解脱的信号。
岑鸢紧绷的神经骤然断裂,全身的力气被瞬间抽空。她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
倒下前,她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裴烬对导演说的。
“李导,现在,她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