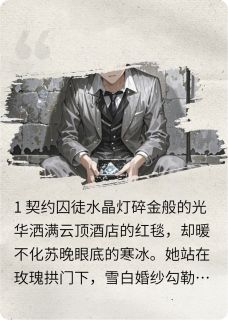
1契约囚徒水晶灯碎金般的光华洒满云顶酒店的红毯,却暖不化苏晚眼底的寒冰。
她站在玫瑰拱门下,雪白婚纱勾勒出清冷轮廓,锁骨下的钻石胸针像一枚冰冷的封印。
这该是她的婚礼,她却只像个精致的囚徒,目光越过满堂衣香鬓影,
最终定格在红毯尽头那个格格不入的身影上。凌默来了。劣质的黑色西装紧绷在他身上,
肩线歪斜,袖口磨损。那双灰扑扑的球鞋踩在光洁如镜的大理石上,刺眼得如同一个错误。
他像是误入奢靡幻境的困兽,每一步都走得僵硬沉默,微垂着头,额前碎发遮住眉眼,
只留下线条紧绷的下颌。宾客席中压抑的嗤笑和指指点点,如同毒针,密密麻麻扎向他。
“苏家真是病急乱投医,冲喜冲来个霉星?”“瞧那鞋!苏晚这朵花,插在牛粪上都嫌糟蹋!
”议论声不大,却字字剜心。凌默的脚步微不可察地一顿,指尖蜷缩又松开,
脊背却挺得更直,像一根被压弯却不肯折断的芦苇。他终于走到苏晚面前。
司仪公式化的问话尚未结束,苏晚冰冷的声音已斩断所有温情:“愿意。”她看也没看他,
径直在一份文件上签下名字,推向凌默。“签了。
”凌默的目光落在文件抬头的加粗黑体字上——《婚姻契约书》。
条款冰冷如刀:名义夫妻、互不干涉、无条件配合、每月“薪酬”、随时终止。
他是被明码标价的工具。他拿起笔,劣质塑料笔杆湿黏。就在笔尖悬停的瞬间,
一股浓烈的酒气伴着夸张的笑声袭来。“妹夫!大喜日子签什么字?喝一个!
”苏晚的堂弟苏浩,端着满满一杯烈酒挤来,脸上恶意昭彰。他手臂猛地一扬——哗啦!
冰冷的琥珀色酒液混着冰块,劈头盖脸浇在凌默头上、脸上!
酒水顺着发梢、廉价西装的领口狼狈流淌,在胸前洇开深色的屈辱印记。冰块砸在他额角,
碎裂声清脆刺耳。“哎呀!手滑了!”苏浩故作惊讶,声音里的得意几乎溢出来,
“对不住啊!衣服都湿了,脱下来我帮你洗洗?”他伸出手,作势要去拉扯凌默湿透的衣襟,
动作充满侮辱。哄笑声轰然炸响,比之前更肆无忌惮。无数道目光像聚光灯,
将他钉在羞耻的舞台中央。凌默僵立原地,酒水顺着睫毛滴落。那些目光里的鄙夷、嘲弄,
如同实质的鞭子抽打着他。攥着笔的手指骨节捏得惨白,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带来尖锐的刺痛。一股冰冷暴戾的气息在他胸腔疯狂翻涌,几乎要撕裂那层麻木的壳。
垂在身侧的另一只手,肌肉骤然绷紧,指关节发出危险的“咔”声。“苏浩!
”苏晚清冷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响起,“适可而止。”她终于侧目,扫过凌默的狼狈,
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没有心疼,没有愤怒,只有深潭般的平静和一丝疲惫的漠然。
仿佛眼前闹剧,与她无关。苏浩在苏晚毫无温度的目光下讪讪收手,哼了一声走开,
临走仍不忘丢给凌默一个恶毒的嘲笑。凌默缓缓抬手,用手背抹去脸上的酒渍。
冰凉的液体**着皮肤,奇异地浇熄了那几乎焚毁理智的怒火。
眼底深处那抹猩红风暴沉寂下去,重归死寂的墨黑。他不再看任何人,低下头,
沾着酒水的笔尖有些打滑。他依旧一笔一划,在契约书上签下名字——凌默。字迹歪斜,
却带着认命般的沉重力道。“仪式结束。请新人……”司仪干巴巴地试图挽救。“不用了。
”苏晚打断,声音冷冽。她抽走一份契约书递给助理,“Amy,收好。
”她这才第一次正眼看向凌默,目光平静无波,如同审视一件货物。“凌默,”她开口,
声音清晰地穿透残留的喧嚣,“契约已签。记住你的身份和约定。安分守己,互不干涉。
苏家给你栖身之所,你做好你该做的。”她的视线扫过他湿透皱巴的西装,
眉头几不可察地一蹙,带着本能的嫌弃,“……别惹麻烦。”说完,她转身离去。
雪白裙摆拂过地面,像一朵移动的冰莲,将身后的喧嚣与屈辱隔绝。
谄媚的宾客瞬间将她簇拥。凌默独自站在原地,头发滴水,
湿透的廉价西装紧贴着他瘦削却挺直的脊梁。水晶灯的光芒在他脚下投下孤寂扭曲的暗影。
空气中混杂着香槟的甜腻、香水的馥郁和他身上廉价酒精的酸涩,令人窒息。
岳母王美兰扭着腰肢走来,厚厚的粉底盖不住刻薄。
她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嫌弃地虚点凌默胸口:“还杵着丢人?瞧你这鬼样子!
滚回你的佣人房去!等着抬你?晦气!”她拔高声音,“记住!你连苏家的狗都不如!
马桶地板脏活累活都是你的!废物!”凌默缓缓抬起头。湿漉漉的碎发下,
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终于完全显露。里面没有愤怒,没有屈辱,只有一片死寂的空洞。
这空洞的眼神竟让王美兰心头莫名一悸,后续的咒骂卡在喉咙。他没有言语,
甚至没再看她第二眼,沉默转身。湿透的西装下摆沉重晃动,在地上拖出蜿蜒的水痕,
像无声的泪,又像不祥的印记。他背离繁华与嘲弄,走向通往地下员工区域的幽暗走廊。
那里,只有狭窄、潮湿、弥漫着霉味与清洁剂气息的佣人房在等待。
就在他即将踏入阴影的前一刻,宴会厅巨大的LED屏幕上,
娱乐新闻主持人甜美的声音突兀响起:“……最新消息,凌氏集团太子爷凌轩结束海外考察,
已于今日返回国内……”屏幕上,一张英俊矜贵、意气风发的脸孔在闪光灯下熠熠生辉。
凌默的脚步,在通道入口的阴影边缘,猛地顿住。他没有回头。
但那只刚刚签下屈辱契约、被烈酒浇透的右手,在身侧无人可见的角度,死死攥成了拳!
指甲深深陷入掌心旧伤,一股温热的、带着铁锈味的液体瞬间濡湿冰冷的掌心。
极致的隐忍下,一股深沉如渊、暴戾如狱的冰冷气息,如同被惊醒的凶兽,
在他死寂的眼底一闪而逝,快如幻觉。2屈辱烙印幽深的走廊如同巨口,
吞噬了他沉默的身影。只有通道口冰冷的地面上,几点暗红色的血珠,
在灯光的折射下诡异地亮了一瞬,随即被一只匆忙走过的侍应生皮鞋底,
碾碎成一片模糊的污迹。那血痕,是他签下的另一个名字,无声,却滚烫。
通道口的灯光彻底消失在身后,沉重的防火门隔绝了宴会厅的喧嚣,
仿佛关上了两个世界的闸门。空气瞬间变得滞重、阴冷,
混合着劣质清洁剂、陈年霉味和食物残渣的酸腐气息,狠狠灌入凌默的鼻腔。
这里是与楼上水晶宫般璀璨截然相反的地下——苏家光鲜亮丽背后的下水道。走廊狭长,
灯光昏暗惨白,勉强照亮两侧紧闭的铁灰色房门,门上贴着褪色的编号牌。
空气管道在头顶发出沉闷的嗡鸣,像一只垂死的巨兽在苟延残喘。
凌默湿透的西装紧贴着皮肤,带来刺骨的冰凉,
每一步都伴随着黏腻的脚步声和布料摩擦的窸窣声,在这死寂的空间里格外清晰。最终,
他在走廊尽头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前停下。门上没有编号,
只有一块模糊不清的、写着“杂物”字样的旧木牌。王美兰那尖刻的“佣人房”称呼,
都算抬举了它。他掏出之前管家随手丢给他的、带着油污的钥匙,
冰冷的金属触感硌着掌心未愈的伤口,带来一阵锐痛。“咔哒”一声轻响,门开了。
一股更浓烈的、令人作呕的霉味混杂着尘土气息扑面而来。房间极小,几乎无法转身。
一张布满污渍、摇摇欲坠的单人铁架床塞在角落,上面胡乱扔着一床薄得透光的旧棉絮。
墙壁斑驳,大片大片的霉斑如同丑陋的疮疤蔓延,墙角结着厚厚的蛛网。没有窗户,
唯一的光源是天花板上一个蒙尘的、瓦数低得可怜的灯泡,投下昏黄摇曳的光晕,
将房间的破败与肮脏照得无所遁形。地面是冰冷的水泥,
角落堆放着几个落满灰尘的空油漆桶和几卷废弃的电线。这就是苏家给他的“栖身之所”。
凌默反手关上门,隔绝了外面走廊微弱的光线,
也将自己彻底投入这片令人窒息的黑暗与腐朽之中。他没有开灯,
任由那昏黄的灯泡将他的影子拉长、扭曲在霉变的墙壁上,像一个沉默的鬼魅。
他背靠着冰冷的铁门,缓缓滑坐下去。湿透的西装裤紧贴着冰冷的水泥地,
寒气瞬间侵入骨髓。头顶的酒水仍在滴落,顺着发梢滑过额角,
流过那道被冰块砸出的、已经有些麻木的细小伤痕,最终汇聚在下颌,
滴落在同样冰冷的地面上,发出微不可闻的“嗒…嗒…”声,在这死寂的房间里,
却如同丧钟的回响。他摊开一直紧握成拳的右手。掌心一片狼藉。
被指甲深深刺破的伤口在昏暗光线下显得格外狰狞,暗红的血混着未干的廉价酒液,
黏腻地糊在掌心纹路里。那股熟悉的铁锈味再次弥漫开来,带着屈辱的温度。
他盯着那片污浊,眼神空洞,仿佛那不是自己的手。时间仿佛凝固。只有水滴落的声音,
和头顶管道偶尔传来的、如同叹息般的嗡鸣。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几分钟,
也许是几个小时。门外走廊传来模糊的脚步声和压低的笑语,是忙碌的酒店员工。
那些声音很近,却又仿佛来自另一个遥远的星球,与他毫无关系。
他就像被世界遗弃在垃圾堆里的碎片。突然,极其轻微的“叩叩”声响起,敲在铁门上,
带着一丝犹豫。凌默猛地抬眼,那双死寂的墨瞳在昏暗中锐利如刀,瞬间锁定了声音的来源。
他身体紧绷,如同黑暗中蛰伏的兽类,右手下意识地再次攥紧,
伤口被挤压带来的刺痛让他更加清醒。谁?苏浩?王美兰派来的爪牙?
还是哪个想再踩他一脚的“上等人”?
门外的人似乎被门内陡然升起的、无形的冰冷压迫感慑住,停顿了几秒。然后,
一个年轻女孩刻意压得极低、带着紧张和一丝不易察觉怜悯的声音响起:“凌…凌先生?
是…是我,Amy。苏**让我…让我给您送点东西。”Amy?苏晚那个干练的女助理?
凌默紧绷的肌肉没有放松,眼神中的警惕也未散去。苏晚?她不是已经当众划清界限,
让他“安分守己,别惹麻烦”了吗?现在又派人来做什么?是怜悯?还是新的警告?门外,
Amy似乎能感觉到门内无声的抗拒和寒意,声音更低了,
语速加快:“东西…东西我放在门口了。您…您自己拿一下。
苏**说…让您…擦擦身上的酒,
还有…伤口…最好处理一下…”她的声音带着一种完成任务般的匆忙,
显然不愿在此地多留一秒,更不愿与门内这个“麻烦”有过多接触。说完,
一阵轻微的衣物摩擦声和快速远去的脚步声响起,很快消失在走廊尽头。门外重归死寂。
凌默依旧靠着门,一动不动。又过了许久,直到确认外面再无动静,他才缓缓站起身。
动作牵扯着湿冷的衣物和掌心的伤口,带来一阵钝痛。他伸手,极其缓慢地拧开了门锁。
门开了一条缝。昏黄的走廊灯光斜射进来,
照亮门口水泥地上放着的一个不起眼的牛皮纸文件袋,
以及——一个印着酒店LOGO的白色塑料袋。凌默的目光先落在那文件袋上。他认得,
和刚才签的《婚姻契约书》一模一样。是给他的那份“卖身契”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