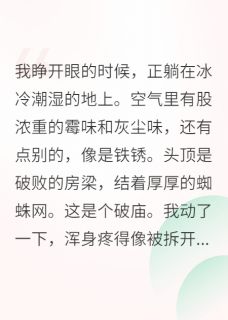
我睁开眼的时候,正躺在冰冷潮湿的地上。空气里有股浓重的霉味和灰尘味,还有点别的,
像是铁锈。头顶是破败的房梁,结着厚厚的蜘蛛网。这是个破庙。我动了一下,
浑身疼得像被拆开又胡乱装了回去。“醒了?”一个声音,冷冰冰的,从我头顶砸下来。
我费力地转动眼珠。一个男人。穿着黑色的袍子,料子看着很好,但沾了些暗色的污渍。
他很高,背对着从破窗户漏进来的那点惨淡月光,脸完全隐在阴影里,
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可那双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吓人。像狼。他手里拿着个东西,
像个小小的玉牌,泛着幽幽的绿光,正对着我的眉心。那光让我脑子一阵尖锐的刺痛,
像有根烧红的针扎进来。“忍着点。”他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很快就过去了。”那绿光猛地大盛!一股庞大到无法形容的冰冷意志,像决堤的洪水,
粗暴地冲进我的脑袋!我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无数不属于我的记忆碎片、疯狂的嘶吼、冰冷的杀意、还有深不见底的黑暗,
蛮横地撕扯着我的意识。要裂开了!我的灵魂被挤压到角落里,像一张被揉皱的废纸。
那个冰冷的意志要占据这里,彻底抹掉我。不!一个念头死死地撑着,
像狂风暴雨里最后一根草绳。我不能死!我还有事没做!
模糊的画面闪过——一个温暖的笑脸,一声清脆的“阿念”……是我最好的朋友,小满。
我不能就这么没了!这个念头成了我唯一的支点。我用尽所有的力气,在意识被彻底吞噬前,
狠狠地“咬”了回去!不是用牙,是用一种我自己都不明白的本能。就像濒死的野兽,
用最后一点力气反扑。“唔!”一声闷哼。来自那个男人。他手里的玉牌光芒猛地一黯,
剧烈地闪烁起来,像是接触不良的灯泡。那股碾压我的冰冷意志,突然停滞了。紧接着,
像是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猛地反弹回去!“噗——”男人身体晃了晃,猛地喷出一口血。
暗红的血点溅在我脸上,温热,带着腥气。他踉跄着后退了一步,
扶住了旁边歪倒的供桌才没倒下。那枚刚才还绿得妖异的玉牌,“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裂成了几瓣,光芒彻底熄灭。破庙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我的,还有他的。我瘫在地上,
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了,全身的骨头都在哀鸣。但我的脑子,奇迹般地还属于我自己。
我活下来了?那个男人低着头,看着地上碎裂的玉牌,很久没动。破庙里安静得可怕,
只有风穿过破洞的呜咽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抬起头。月光正好移过来一点,
照亮了他半边脸。那是一张极其英俊,但也极其冷厉的脸,线条像刀削出来的一样。此刻,
他嘴角还残留着血迹,脸色白得吓人。可他那双狼一样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
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冰冷。那里面……充满了震惊,难以置信,
还有……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我被他看得毛骨悚然。他要干什么?恼羞成怒,
直接掐死我?我闭上眼,等着最后的结局。预想中的剧痛没有来。脚步声响起,很慢,很沉。
他走到了我面前,蹲了下来。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我能闻到他身上浓重的血腥味,
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冷冽气息。一只手伸了过来。我吓得猛地一缩。
那只手却顿在了半空。他看着我惊恐的样子,眉头皱得死紧,
像是遇到了天底下最棘手的难题。然后,他做了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动作。他伸出的手,
没有掐我的脖子,而是……极其僵硬地、小心翼翼地,落在了我的头顶。很轻地,拍了两下。
像在拍一个……易碎的瓷器?动作生涩得可笑。他开口,声音嘶哑得厉害,
带着一种极其古怪的、试图放柔却依旧显得生硬的语调:“别怕。
”“……”我整个人都懵了,像被雷劈中。他是不是夺舍失败,脑子被我撞坏了?“饿不饿?
”他又问,语气还是那么别扭。我完全跟不上这转折,只能凭着本能,傻傻地点了下头。
肚子适时地发出“咕噜”一声巨响。在死寂的破庙里格外清晰。
男人的眉头似乎舒展了一点点,虽然那张脸还是冷得能冻死人。他站起身,
高大的身影几乎挡住了所有光线。“等着。”丢下这两个字,他转身就走出了破庙,
黑袍很快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留下我一个人躺在地上,对着漏风的屋顶,满脑子都是浆糊。
这什么情况?反派大佬夺舍失败,决定改行当保姆?我躺了不知多久,
身体稍微恢复了一点知觉。试着动了动胳膊腿,还好,没断。就是浑身疼,饿得前胸贴后背。
外面传来脚步声。我立刻又僵住。那个男人回来了。
他手里拎着……一只拔了毛、处理好的野鸡?还有一小捆干柴。他看也没看我,
径直走到破庙中间的空地上,动作熟练地生起了火。火光跳跃起来,驱散了寒意,
也照亮了他冷硬的侧脸。他拿出一个……很精巧的银色小刀?开始处理那只鸡。
那刀在他手里翻飞,快得几乎看不清。我缩在角落里,偷偷看着他。他专注地烤着鸡,
火光映在他脸上,那层冰壳似乎融化了一点点。烤鸡的香味飘了出来。我的肚子叫得更响了。
他撕下一条烤得金黄流油的鸡腿,递到我面前。“吃。”言简意赅。我看着那鸡腿,
又看看他没什么表情的脸。巨大的恐惧还没完全散去,但饥饿感更强大。我咽了口唾沫,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接了过来。烫手。我一边吹气,一边小口地啃。真香啊。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烤鸡。他坐在火堆对面,手里拿着另一只鸡腿,慢慢地吃着,
动作带着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优雅,和他一身煞气格格不入。他吃得不多,
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我吃。那眼神……怎么说呢?像是在研究什么稀世珍宝,带着审视,
还有一丝……困惑?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只能埋头猛吃。吃完鸡腿,
他又递过来一个……水囊?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喝了一口。是清水,有点凉。吃饱喝足,
身上暖和了,力气也恢复了一些。但恐惧感又回来了。我抱着膝盖,缩成一团,偷偷看他。
他坐在火堆旁,闭着眼,像是在调息。脸色还是不太好。“那个……”我鼓起勇气,
声音小得像蚊子哼,“你……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那样对我?”他睁开眼。
火光在他眼底跳动。他没有立刻回答,似乎在斟酌词句。“阎烬。”他吐出两个字。
名字都透着一股煞气。“至于为什么……”他顿了一下,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带着一种穿透力,“你的身体,很特别。”特别?我低头看看自己沾满灰土的手。哪里特别?
特别能扛饿?“特别适合……”他似乎在找一个不那么吓人的词,“容纳力量。”容纳力量?
容纳他的力量,然后把我挤出去吗?我打了个寒颤。“现在不适合了。”他移开目光,
看向跳动的火焰,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失败了。”“所以……”我试探着问,
“你打算放过我了?”他转回头看我,眉头又皱起来:“放过?”那语气,
好像我说了什么蠢话。“你,跟我走。”不是商量,是命令。我心里一咯噔。完了,
他还是没打算放过我。“去……去哪?”我的声音有点抖。“离开这里。”他站起身,
高大的身影带来压迫感,“找个地方住下。”住下?跟他?
这个刚刚还想抹掉我灵魂的危险分子?“我不去!”我脱口而出,往后缩了缩,“我要回家!
”“家?”他重复了一遍,眼神有点冷,“你还有家?”我一愣。是啊,我哪还有家?
我是个孤儿,从小在慈幼院长大,磕磕绊绊活到十八岁,
好不容易在城里一家小绣坊找了个活计,能养活自己了。昨天是发工钱的日子,
我揣着攒了几个月的钱,想给一直照顾我的慈幼院嬷嬷买点药。路过城外这片林子时,
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醒来,就在这破庙里,差点被人夺了舍。
我的钱袋……肯定丢了。绣坊的工作……无故失踪,肯定也没了。嬷嬷的药钱……也没了。
我好像,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一股巨大的委屈和绝望涌上来,鼻子发酸。
我用力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阎烬看着我,那冰冷的眼神似乎……波动了一下?
他走过来,再次蹲在我面前。这次,他伸出手,动作依然僵硬,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力道,
把我拉了起来。“以后,”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像是在宣布什么重大决定,“我管你。
”我被他拽着,踉踉跄跄地走出了破庙。外面天已经蒙蒙亮。荒郊野岭,看不到人烟。
阎烬拉着我,走得很快。他步子大,我几乎是小跑着才能跟上。“我们去哪?
”我气喘吁吁地问。“进城。”他头也不回。进了城,天光大亮。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阎烬一身煞气,加上袍子上的暗色污渍(我怀疑是血),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自动避开三米远。我被他拽着,像个破布娃娃,只想把脸藏起来。他拉着我,目不斜视,
径直走进城里最气派的一条街。然后,停在了一家……成衣铺子门口?“进去。
”他把我往前一推。我懵懵懂懂地走进去。铺子里琳琅满目,都是上好的绫罗绸缎,
伙计打扮得比我还体面。我这一身破旧衣裳,沾满泥土,站在光洁的地板上,格格不入,
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伙计皱着眉走过来,刚要开口赶人。阎烬一步跨进来,站在我身边。
他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冷冷地扫了那伙计一眼。伙计的脸瞬间白了,话卡在喉咙里,
腿肚子都在抖。“挑。”阎烬低头对我说,语气还是硬邦邦的,“喜欢的,都要。
”我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我……我没钱……”我小声说。“我有。”他言简意赅。
我看着他冷硬的脸,又看看吓得快晕过去的伙计,再看看那些漂亮得不像话的衣裳。
一种极其不真实的感觉笼罩着我。这个昨天还想杀我的男人,现在要给我买衣服?
我小心翼翼地指了指角落里一套看起来最朴素的鹅黄色细棉布衣裙。“那……那个吧。
”阎烬眉头立刻拧紧了:“太素。”他目光扫过货架,抬手指了指:“这个,这个,
还有那个……颜色鲜亮的,都包起来。”他指的都是铺子里最贵、最扎眼的料子,大红大绿,
金线银线闪闪发光。我眼前一黑。穿这些走出去,我怕是会变成城里最大的笑话。
伙计如蒙大赦,赶紧去打包。最后,阎烬付钱(他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钱袋,
倒出来的银锭差点闪瞎我的眼),拎着好几个大包袱,
带着穿着崭新大红撒金襦裙、浑身不自在的我,走出了成衣铺。
我感觉自己像个移动的红灯笼。他接着又带我去了脂粉铺子。“这个,这个,还有那个。
”他依旧是那套,指着最贵的、包装最花哨的买。我麻木了。
然后是鞋铺、首饰铺子……不到半天,我身上挂满了东西。
新衣服、新鞋子、新簪子、新镯子、新胭脂水粉……从头到脚,焕然一新。
就是这搭配……大红配大绿,金簪配银镯,活脱脱一个行走的暴发户。路人看我的眼神,
充满了同情和……忍俊不禁?阎烬似乎很满意,看着我,点了点头:“嗯,像样了。
”我欲哭无泪。这比穿破衣服还难受!最后,他带我走进一家客栈。
城里最好的“悦来客栈”。“掌柜,一间上房。”他把一块沉甸甸的银子拍在柜台上。
掌柜的眼睛都直了,点头哈腰:“好嘞!天字一号房!贵客楼上请!”天字一号房果然奢华。
雕花大床,锦缎被褥,红木家具,窗明几净。阎烬把手里的大包小包往桌上一放。
“以后住这。”我站在铺着厚厚地毯的房间中央,感觉像在做梦。一个荒诞离奇的梦。
“你……你住哪?”我小声问。他看了我一眼:“隔壁。”我稍微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住一间。“收拾一下。”他说,“缺什么,跟伙计说。”说完,他转身就走,
还带上了房门。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走到梳妆台前,看着巨大的铜镜。镜子里的人,
穿着刺眼的大红裙子,戴着金灿灿的簪子和镯子,脸上因为刚才走路而泛红。陌生得可怕。
这真的是我吗?那个在绣坊熬夜赶工、手指被针扎破也不敢吭声的范无咎?
那个差点在破庙里魂飞魄散的孤女?我猛地抬手,想把头上那根沉甸甸的金凤簪拔下来。
手却停在了半空。阎烬那张冷硬的脸,和他生硬地拍我头的样子,在我脑海里交替出现。
他到底想干什么?赎罪?还是……养肥了再宰?接下来的日子,更加魔幻。
我住着最好的客栈上房,吃着伙计送来的精致饭菜(阎烬点的,全是肉,
他好像觉得我只爱吃肉)。阎烬大部分时间待在隔壁,偶尔过来。每次来,都像领导视察。
他往椅子上一坐,也不说话,就用他那双狼一样的眼睛,上下打量我。看得我头皮发麻。
然后,他会突然蹦出一句:“头发乱了。”或者:“瘦了,多吃。”再或者:“外面冷,
加衣。”语气永远硬邦邦,带着命令的口吻。我像个提线木偶,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有时候,他也会丢给我一些东西。一本字帖(我认识的字不多)。“练。”或者,
一本棋谱(我看不懂)。“看。”甚至,一把小巧的匕首(寒光闪闪)。“防身。
”我拿着匕首,手都在抖。防谁?防他吗?我越来越搞不懂他。
他好像真的在履行那句“我管你”。管吃管住管穿戴,还管“学习”和“安全”。
只是这管教方式,霸道得让人窒息。这天下午,我实在憋得慌。客栈再好,也像金丝笼子。
我想出去透透气。趁阎烬在隔壁没动静,我悄悄溜出了客栈。走在热闹的街上,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
走到了我以前干活的那家小绣坊附近。看着熟悉的门脸,我心里有点发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