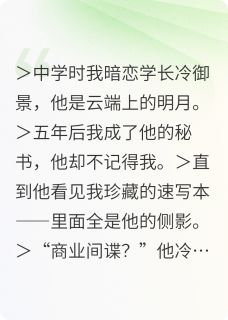
她睡着了。也许是哭累了,也许是姜汤的暖意和疲惫终于战胜了紧绷的神经。
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细小泪珠,随着呼吸轻轻颤动。眉头微微蹙着,即使在睡梦中,
似乎也锁着化不开的愁绪和不安。脸颊因为之前的哭泣和热度泛着不正常的潮红。
冷御景放轻脚步,如同踩在薄冰上,悄无声息地走到床边。他高大的身影投下的阴影,
温柔地笼罩住床上蜷缩的女孩。他缓缓蹲下身,视线与她平齐,
贪婪地、近乎痴迷地凝视着她沉睡的容颜。褪去了清醒时的防备和倔强,
此刻的她显得那样脆弱,那样毫无保留。眼下的青影,红肿的眼皮,微蹙的眉心,
每一处细节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从未如此近距离地、如此专注地看过她。中学时,
她是角落里模糊的影子;成为秘书后,她是需要他保持距离的下属。直到此刻,
他才真正看清这张脸——褪去了少女的稚嫩,线条更加清晰柔美,
却依旧带着一种易碎的、让人心尖发颤的纯净。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那本被她死死抱在怀里的速写本上。粗糙的封面,丑陋的胶带,
无声地控诉着他的暴行。一种灭顶的悔恨和难以言喻的心疼瞬间攫住了他,几乎让他窒息。
他伸出手,指尖带着一种极致的、近乎朝圣般的轻颤,小心翼翼地靠近,
想要替她拂开黏在额角的一缕湿发。
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她皮肤的瞬间——睡梦中的季宁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身体猛地瑟缩了一下,
出一声模糊的、带着浓浓惊惧和委屈的呓语:“…别撕…冷御景…求你别撕…”那声音很轻,
带着浓重的哭腔,像梦魇中的哀求。冷御景伸出的手如同被滚烫的烙铁灼伤,猛地僵在半空!
指尖距离她的额角,只有不到一寸的距离。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头顶,
冻结了他全身的血液。他僵在那里,维持着那个可笑的姿势,
看着她在睡梦中因那瞬间的惊惧而更紧地抱住了怀里的本子,眉头锁得更深。
那句无意识的梦呓,像一把淬毒的匕首,精准地刺穿了他所有试图靠近的勇气。
将他刚刚升起的那一丝微弱的希望和靠近的渴望,彻底碾得粉碎。原来,
他带给她的恐惧和伤害,早已深入骨髓,连梦境都无法摆脱。
他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收回了僵在半空的手,紧握成拳,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带来尖锐的刺痛,却远不及心口那万分之一。他站起身,
高大的身影在柔和的壁灯下显得有些佝偻。他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床上蜷缩的女孩,
和她怀里那个如同伤痕累累象征的本子,眼神里翻涌着痛苦、懊悔和无能为力的绝望。最终,
他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房间,轻轻带上了房门。厚重的门板隔绝了内外两个世界。
冷御景背靠着冰冷的门板,仰起头,闭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气。走廊冰冷的空气涌入肺腑,
却无法冷却心口那片灼烧的荒芜。他独自站在空旷死寂的黑暗里,
像一座被遗弃在暴风雨中的孤岛。悔恨如同冰冷的潮水,一遍遍冲刷着他,
留下尖锐的砂砾和刺骨的寒意。他弄丢的,弄坏的,何止是一本速写本?他该如何修补,
这被他亲手撕得粉碎的过往?沉重的门在身后无声合拢,
隔绝了门内那微弱却令人心碎的呼吸声。冷御景背靠着冰冷的实木门板,
走廊里死寂的空气像凝固的寒冰,包裹着他。
季宁睡梦中那句带着惊惧的呓语——“…别撕…冷御景…求你别撕…”——如同淬毒的冰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