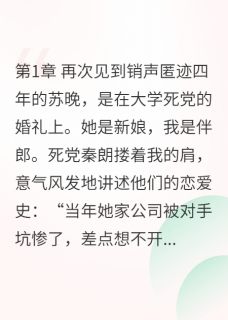
第1章再次见到销声匿迹四年的苏晚,是在大学死党的婚礼上。她是新娘,我是伴郎。
死党秦朗搂着我的肩,意气风发地讲述他们的恋爱史:“当年她家公司被对手坑惨了,
差点想不开跳江,是我连夜把她捞上来的!听说当时还有个男的一直缠着她不放?啧,
我直接带她出国避风头了。”“怎么样,阿州?哥们儿这手玩得漂亮吧?
”……秦朗还在眉飞色舞,我的大脑却嗡地一声,一片空白。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夜,
我拼了命寻找的人,竟然被我最信任的兄弟藏了整整四年!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四肢百骸瞬间冰凉僵硬,控制不住地微微发颤。秦朗看我脸色煞白,赶紧把我扶进休息室,
关切地问:“砚州?你没事吧?是不是太累了?”这四年,为了找苏晚,
我跑遍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问遍了所有认识她的人,发了无数寻人启事,报了警,
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连她家里人都绝望了,以为她真的葬身江底,
只有我固执地相信她还活着,像个疯子一样不肯停下。多少个无眠的深夜,
我站在冰冷的江堤上,被绝望啃噬,无数次想纵身跃下,结束这无望的寻找。原来,
从头到尾,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袖口下,
手腕上那些深深浅浅、反复愈合的旧疤隐隐发烫。眼眶酸胀得厉害,心脏像被钝刀反复切割。
秦朗叹了口气:“又在想她了?别找了,都过去多久了,该翻篇了。你也学学我,
找个好姑娘,重新开始。”“改天我组个局,让晚晚给你介绍几个好姐妹认识。”话音刚落,
休息室的门被推开,苏晚走了进来。一身洁白的婚纱勾勒出她依旧纤细窈窕的身姿,
时光似乎并未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唯一不同的是,当目光交汇,那双曾经只盛满我的眼眸,
只是淡漠地掠过我的脸,便径直走向秦朗,细心地为他整理领结。她身后跟着伴娘团,
还是以前相熟的朋友。她们曾经姐夫姐夫的叫我,那些笑声仿佛还在耳边。此刻看到我,
她们眼神躲闪,欲言又止。就在刚才,我还能用她跳江失忆了来欺骗自己。
可她身边每一个熟悉的面孔,都在无声地宣告:她没有失忆,她记得一切。只是,
不再爱我了。仅此而已。秦朗看着苏晚,眼里是毫不掩饰的得意与满足:“老婆,
晚上让你姐妹们都别走啊,咱们好好聚聚,热闹热闹!”他朝我使了个眼色。
苏晚随意地点点头,目光焦着在秦朗身上,再未分给我一丝一毫。仿佛,
我们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我缓缓闭上眼,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揉搓,
碾碎,再丢进冰窖里冻成齑粉。痛,是那种深入骨髓、连呼吸都带着血腥味的痛。
我猛地冲进洗手间,背靠着冰冷的瓷砖滑坐在地。那股寒意透过衣料渗进皮肤,
却压不住心底翻江倒海的绞痛。喉头堵得发紧,
压抑的哽咽冲破喉咙:“苏晚……你怎么能……不要我。”第2章2走出洗手间时,
隐约听到伴娘团里有人低声问苏晚:“晚晚,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沈砚州了?
”她的声音平静无波,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凉薄:“一个死缠烂打甩不掉的麻烦罢了,
你们谁有兴趣,谁接手。”“……”婚礼开始了。秦朗大概看出我状态不对,
临时换了人顶替伴郎。苏晚郑重地伸出手,让秦朗将戒指缓缓套进她的无名指。
我站在宴会厅最昏暗的角落,看着台上秦朗意气风发地说着“我愿意”。
一股尖锐的嫉妒猛地刺穿心脏,几乎要冲垮理智,我想冲上揪着秦朗的领子质问他凭什么!
想嘶吼着问苏晚为什么假装不认识我!为什么回来了不找我!为什么所有人都瞒着我!
我想砸烂这场荒谬的婚礼。可我最终只是僵硬地站在原地。在他们交换誓言后,
第一个用力地近乎发泄般地鼓起掌。掌声突兀而响亮,引得周围人侧目。我毫不在意,
死死盯着台上的苏晚。四目再次相对,强忍的酸楚瞬间决堤,泪水无声滑落。
苏晚的瞳孔似乎极轻微地收缩了一下,随即移开目光。那双曾经温柔似水的眼眸,
此刻只剩下冻结的深潭,不起一丝波澜。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留下月牙形的血痕。我想,
我大概真的要疯了。我掏出手机,指尖颤抖着编辑了一条信息发给她:【苏晚,
我绝不祝你新婚快乐!】【我诅咒你,诅咒你此生所求皆成空,所爱皆不得!
】按下发送键的瞬间,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她求的,已经得到了。我的诅咒,
苍白又可笑。没等宴席开始,我直接离场。再待下去,我怕控制不住自己彻底崩溃。两年前,
当寻找苏晚的最后一丝线索也彻底中断时,我把自己关在车里,拧开了煤气阀。可惜,
没死成。被巡逻的保安发现,拖了出来。醒来时,母亲握着我的手泣不成声,
求我为了她好好活下去。可没有苏晚的世界,一片灰败,活着只是无尽的煎熬。
我和她青梅竹马,高中毕业在一起,工作刚稳定就计划着买房结婚。
可她的家族企业突遭暗算,巨额债务压得她喘不过气。最终,
她选择在深夜走向了冰冷的江水,从此杳无音讯。我跑遍了沿江的每一个派出所,
问遍了当晚江边每一个可能的路人。答案只有一个:没看见。现在她回来了,
却成了别人的新娘。第3章3昏昏沉沉不知睡了多久,醒来打开手机。
除了秦朗几个未接来电和母亲的语音安慰。还有一条刺目的回复。只有一个字:【滚。
】喉咙里溢出一声苦涩的嗤笑。原来我那些锥心蚀骨的牵挂和寻找,
在她眼里不过是一场令人厌烦的闹剧。目光无意间落在左手腕上。
那里系着一根磨损严重的黑色编织手绳。是四年前苏晚送我的。绳子早已失去光泽,
边缘起了毛边,我却从未摘下。那是我们订婚前夕,苏晚独自去雪域高原求来的。
她顶着高原反应,徒步走了整整三天,
才从古老的寺庙里求到这一根据说能护佑平安、系定姻缘的手绳。下山途中遭遇暴风雪,
她死死护着胸口这根绳子,被救援队找到时几乎冻僵。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把绳子系在我手腕上,眼睛亮晶晶的:“砚州,庙里的师父说心诚则灵。我求到了,
我们一定会平平安安,一辈子在一起。”如今,女孩清脆笃定的誓言犹在耳边,
眼前却早已物是人非。眼眶发热,我用尽力气扯断那根脆弱的手绳,狠狠扔进马桶。
水流旋涡瞬间将它吞没。苏晚,从此,我们桥归桥,路归路。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后,
反而有种近乎麻木的平静。我向公司提交了调职申请,手续需要一周,
离开这座城市的机票就定在了一周后。那一天,恰好是我和苏晚相恋八周年的纪念日。也好,
在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整整七天,除了出门办手续,
断绝了所有联系。电话打不通,秦朗在我离开当天找上了门,身后跟着苏晚。
他冲上来想拉我:“阿州!你搞什么失踪!吓死我了!”我面无表情地抽回手,
语气疏离:“我没事,谢谢。”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秦朗,是恨还是漠然。
或许两者都做不到,只想彻底远离。秦朗看我冷淡,也不在意,只当我是心情糟糕。
他重重松了口气:“祖宗!手机是摆设吗?知不知道我差点报警!”“我们来接你!
今天是你生日!忘了?晚上给你办了个趴,顺便认识几个新朋友,保证合你眼缘!
”“不许拒绝!听见没!”他语气坚决,带着惯有的不容置疑。秦朗向来如此,
热情、仗义、行动力强,的确容易让人亲近。所以,苏晚会爱上他,似乎也理所当然。
我看向他身后的苏晚。她目光清冷,深不见底的眸子里凝着寒冰,
仿佛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或许是无法拒绝秦朗强硬的关心,
又或许是自己心底那点可悲的不甘。时间还早,我让他们进了屋。这套公寓,
曾经是我和苏晚一起选的婚房。她失踪后,我按照她喜欢的北欧极简风装修,
家具摆设都是她当年画在图纸上的样子。秦朗环顾四周,夸张地“啧”了一声:“阿州,
你这品味够性冷淡的啊?全是黑白灰,一点暖色都没有,跟样板间似的。”“这沙发硬的,
坐久了硌得慌吧?”因为我的世界早就失去了温度和色彩。我淡淡开口:“我前女友喜欢,
就按她的意思装了。”第4章4苏晚的声音清冷地响起,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那你自己的喜好呢?事事顺着别人,不觉得累?
”秦朗立刻接话,带着炫耀:“累什么累?我家装修全听我的!晚晚就喜欢我选的暖色调,
连床单都是我挑的明黄色,她说看着就开心!”我沉默。恍惚想起四年前同居时,
苏晚偏爱极简的灰白,而我总想加点亮色。我买过一套橙色的床品,她皱着眉说刺眼,
宁愿睡沙发也不肯上床。后来我默默换回了她喜欢的冷灰色,她才重新躺回我身边。
我嘴角勾起一丝自嘲的弧度:“是吗?那她会睡沙发吗?”秦朗得意地挑眉,
看向苏晚:“她敢?”“她现在连睡衣都是我挑的卡通款。
”苏晚嘴角几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抬手拍了下秦朗的手臂,示意他闭嘴。“睡什么沙发?
一个女人要是因为床单颜色就不跟你睡,只能说明她不够爱你。”“亏你找了她这么多年,
死渣女!”沉默片刻,我轻轻点了点头。“嗯,你说得对。”“她大概…是真的不够爱我。
”话音刚落,我清晰地感觉到苏晚的目光骤然变得锐利,像冰冷的刀片,在我脸上刮过。
她语气淡漠,带着刺骨的寒意:“既然如此,沈先生就该识相点,彻底消失。”“免得碍眼,
也省得打扰别人生活。”“自我感动式的深情,只会让人觉得廉价又厌烦。
”苏晚的话像淬了毒的针。自我感动……原来我所有的痛苦和坚持,
在她眼里只是廉价的自我感动……心脏猛地一缩,眼眶瞬间红了,
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抖:“你这么懂她,是因为你们是同一类人吗?喜欢玩失踪,
喜欢让别人在绝望里苦等,耗光所有希望,最后连一句解释都吝啬,
反过来还要指责别人自我感动?我只是想要一个真相,难道我的四年就活该被轻飘飘地抹掉?
”苏晚闻言蹙眉,眼底也染上薄怒:“没人逼你等。爱恨都是你自愿的选择。既然选了,
是好是坏,都该自己受着!”“怎么,仗着你等了四年,她就该感恩戴德回头嫁你?
”字字诛心,无情又决绝。我僵在原地,心中最后一点微弱的火星瞬间被这盆冰水浇灭。
泪水毫无预兆地滚落。苏晚的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的针,狠狠扎进心口最柔软的地方。
她说得真对,爱恨自愿。没人逼我,是我自己选的路。所以今日的狼狈不堪,
活该我一人承受。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感情,早已化为齑粉,风一吹就散了。“好,
我会消失得干干净净。”秦朗察觉到气氛降至冰点,赶紧打圆场,拉着苏晚进了书房。
他压低的带着警告的声音还是清晰地传了出来:“你有病啊!明知道砚州有抑郁症,
说话还这么难听!”“别再**他了,听见没有?”苏晚嗤笑一声,
话语里是毫不掩饰的讥诮:“装可怜罢了。”我神情麻木地站在原地,久久未动。
过了一会儿,苏晚独自离开了。我忍不住问秦朗:“她去哪?”秦朗拉着我到吧台倒酒,
笑得轻松:“她一年多没回国了,公司积压的事儿多,先去处理一下。”我愕然,
难以置信地看向他:“苏晚,一年前回来过?”为什么我毫不知情?“对啊,
回来跟我商量婚事。”我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
脑子里只剩下那句“她回来过”在疯狂叫嚣。一股寒气从心底蔓延至四肢百骸。秦朗的话,
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我脸上。“行了行了,别发呆了!我老婆忙完了,换身衣服,
我们去会所,今晚不醉不归!”秦朗兴致勃勃地推我。“你先去,我收拾一下就来。
”“快点啊!”他没多想,哼着歌先走了。目送他的车离开,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妈,我决定了,回去。安排我和您提过的那位,周**见一面吧。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惊喜又哽咽的声音:“砚州!你终于想通了!
家里人都担心你一个人在外地……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积压的情绪骤然冲破堤坝,
眼泪汹涌落下。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声音平稳:“嗯,我回去。会试着相处,
不会再让你们担心了。”母亲又惊又喜:“好好好!你想什么时候见?妈来安排!”“都行。
我订了今晚的机票,今天就回。”我拖出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直奔机场。飞机起飞前,
我将所有与苏晚有关联的联系方式,一键拉黑。手机关机。舷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