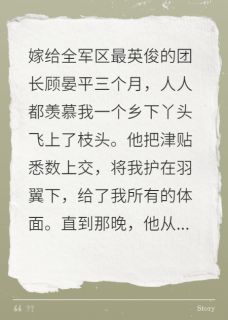
嫁给全军区最英俊的团长顾晏平三个月,人人都羡慕我一个乡下丫头飞上了枝头。
他把津贴悉数上交,将我护在羽翼下,给了我所有的体面。直到那晚,
他从演习场上负伤归来,汗湿的背肌贲张着惊人的力量,我为他擦拭伤口,他却在情动时分,
用滚烫的唇贴着我的耳朵,喊出了另一个名字——“薇薇”。我才知道,我所有的幸福,
不过是偷来的幻影。我是他白月光的替身,一个拙劣的赝品。
01“嘶……”顾晏平闷哼一声,结实的后背猛地绷紧,
肌肉线条在煤油灯下勾勒出惊人的力量感。我手一抖,沾着烈酒的棉花掉在了床单上,
晕开一小片湿痕。“别动,”他声线喑哑,反手攥住我的手腕,滚烫的呼吸喷在我的耳廓上,
带着一股浓烈的雄性荷尔蒙气息,“我自己来。”嫁给他三个月,这是他第一次离我这么近。
近到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皂角混合着汗水的味道,看到他麦色皮肤下贲张的血管。
人人都说我林晚南走了大运,一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女儿,
竟然嫁给了家世显赫、前途无量的战斗英雄顾晏平。婚后,他驻扎在西北,
我随军住进了团级家属院。他确实是个模范丈夫,津贴全部上交,从不让**重活,
对外更是把我护得滴水不漏。院里那些眼高于顶的军官太太们,即便背地里笑我土气,
当着面也得客客气气地喊我一声“顾太太”。我以为,这样的日子,
就是书里写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直到今晚,他演习负伤,高烧不退。我守在他身边,
给他擦身降温,他却在半梦半醒间,一把将我拽进了怀里。
“薇薇……”他滚烫的唇瓣贴着我的耳垂,含糊不清地呢喃着。那一瞬间,
我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薇薇,白薇薇。我见过她的照片,
就夹在顾晏平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里。照片上的姑娘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
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天上的月牙。那是他青梅竹马的恋人,
军区文工团的报幕员,也是整个大院公认的“准顾太太”。听说,她因为家庭成分问题,
被迫脱下军装,下放到了农场。而我,一个根正苗红的农家女,恰好在那时,通过媒人介绍,
嫁给了顾晏平。原来,他对我所有的好,所有的体面,
都不过是因为我这双和白薇薇有七分相似的眼睛。我不过是个暖床的替身。荒唐,可笑。
我从他滚烫的怀抱里挣脱出来,胸口闷得像压了一块巨石。就在这时,
房门被“砰砰砰”地敲响了。“嫂子,你在家吗?我是团卫生队的,顾团长发烧了,
我来给他打一针退烧针。”门外传来一个年轻战士清脆的声音。我定了定神,
哑着嗓子应了一声:“在,门没锁,你进来吧。”门被推开,一个小战士背着药箱走进来,
看见床上的顾晏平,立刻敬了个礼。“嫂子,我给团长打针,您……您能搭把手,
把他裤子往下褪一点吗?针要打在……打在**上。”小战士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这三个月,我和顾晏平虽然同床共枕,却清清白白,
连手都没正经牵过。他是个军人,严于律己,说要等我慢慢适应。
我曾为他的君子风度而感动,现在想来,不过是因为他心里装着别人,根本不屑于碰我。
可如今,当着外人的面,我却要亲手……我咬着牙,指尖掐进了掌心。“嫂子?
”小战士见我迟迟不动,小声催促道。我深吸一口气,走到床边,
看着顾晏平昏睡中依然紧蹙的眉头,心中一片冰凉。替身?好啊。我倒要看看,这场戏,
我能不能唱得比正主还好听。我伸出手,指尖触碰到他腰间那根武装带冰冷的金属扣时,
床上的人却突然睁开了眼睛。那双深邃漆黑的眸子,在昏黄的灯光下,锐利如鹰。他醒了。
02顾晏平的眼神清明得不像个高烧的病人,他盯着我,又扫了一眼旁边手足无措的小战士,
喉结滚动了一下。“你在干什么?”他的声音比刚才更加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
我捏着他皮带扣的手指像是被烫了一下,下意识就想缩回来。可一想到“薇薇”那两个字,
一股无名火就从心底窜了上来。凭什么?凭什么我就得像个受了惊的兔子?我非但没缩手,
反而指尖微微用力,直视着他的眼睛,语气平静得可怕:“小战士来给你打退烧针,
我搭把手。”我看到顾晏平的喉结又滑动了一下,耳根处泛起可疑的红晕。“不用,
”他猛地坐起身,动作太大牵动了后背的伤口,疼得他“嘶”了一声,
额上瞬间冒出细密的汗珠,“我自己来。”他一把挥开我的手,背对着我们,
动作利落地解开皮带,将裤子褪下一个危险的弧度,露出紧实挺翘的臀部。
小战士脸红得快要滴血,手忙脚乱地准备针剂,嘴里还念叨着:“团长,您忍着点,有点疼。
”我站在一旁,冷眼看着。灯光下,他宽阔的脊背上,旧伤叠着新伤,像一幅沉默的地图,
记录着他赫赫的战功。这就是我的丈夫,一个战斗英雄,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男人。
针头扎进去的时候,他的身体猛地一颤,却死死咬着牙,一声没吭。打完针,
小战士如蒙大赦,收拾好药箱就想溜。“等等。”我叫住他。
我从柜子里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塞到他怀里,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辛苦你了小同志,
晚上天黑,路上慢点。”这是顾晏平的做派,体面,周到。从前我学着他,
是真心实意地想做一个配得上他的好妻子。现在,我只想用他最熟悉的方式,
在他心上扎一根最细的刺。小战士受宠若惊地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顾晏平,
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他默默地穿好裤子,躺回床上,用后背对着我,一言不发。“顾晏平,
”我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回荡在寂静的房间里,“我们谈谈。”他身体僵了一下,
没有回头,声音从被子里闷闷地传来:“明天再说,我累了。”又是这样。
每次我试图与他沟通,他都用这句话来搪塞。以前我以为他真的是训练太累,现在我懂了,
他只是懒得应付我。“不行,就现在。”我的语气强硬起来。我走到床的另一边,与他对视。
“白薇薇是谁?”我开门见山。他的瞳孔猛地一缩,像被人踩到了尾巴的猫,
瞬间充满了警惕和……一丝被我看穿的狼狈。“你胡说什么?”他矢口否认。“我胡说?
”我冷笑一声,走到他书桌前,从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精准地抽出了那张照片,
甩在他面前。“那她是谁?顾团长,你每晚抱着我,叫的可是这个名字。”我弯下腰,
凑近他,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的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的肉里。
我看到他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那双曾经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慌乱。爽。前所未有的爽快。
就像三伏天喝了一碗冰镇酸梅汤,从头爽到脚。“我……”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却干涩无比,“晚南,这件事,不是你想的那样。”“哦?那是哪样?”我直起身子,
抱臂看着他,“你倒是说说,是我听错了,还是我想错了?还是说,
你们文工团的白薇薇同志,还有个小名叫‘晚南’?”我故意把“晚南”两个字咬得很重。
他被我堵得哑口无言,俊朗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就在我以为他会一直这么沉默下去的时候,他忽然掀开被子下了床,赤着脚走到我面前。
他比我高出一个头还多,身影将我完全笼罩。“对不起。”他低头看着我,眼神复杂,
有愧疚,有挣扎,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我和她……是过去的事了。”“过去?
”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那你书里夹着她的照片是过去?
你睡着了叫她的名字是过去?顾晏平,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吗?
”“我……”“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打断他,从手腕上褪下一个银镯子,拍在他胸口。
镯子是他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说是给我的新婚礼物。“这个,还给你。”我看着他的眼睛,
平静地说,“还有,离婚报告我会尽快写好,麻烦你签字。”说完,我转身就走,
没有一丝留恋。顾晏平在我身后,发出一声困兽般的低吼。“林晚南!
”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力道大得像是要将我的骨头捏碎。“你敢!
”03“我有什么不敢的?”我甩开他的手,转过身,迎上他布满红血丝的眼睛。
高烧和震惊让他看起来有些狼狈,但那身军人的威势却丝毫不减。“顾晏平,强扭的瓜不甜,
这个道理你比我懂。”我揉了揉被他抓疼的手腕,语气冰冷,“你心里装着别人,
却和我结了婚,这叫骗婚。按照规定,我完全有理由申请离婚。”那个年代,
“离婚”两个字,对一个女人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尤其是在纪律严明的部队大院,
足以让一个女人被唾沫星子淹死。我看到顾晏平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错愕,他大概没想到,
这个一向在他面前温顺得像只猫一样的女人,会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闹够了没有?
”他压低声音,带着一丝警告的意味,“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离婚两个字传出去,
对你我,对我们两家意味着什么?”“我当然知道。”我笑了,笑意却未达眼底,“对你,
顶多是私生活处理不当,影响一点晋升。对我,就是名声尽毁,一辈子抬不起头。
”我顿了顿,直视着他的眼睛:“可我不在乎。”与其当一辈子面目模糊的替身,
活在别人的影子里,我宁可选择一条最难走的路。至少,那条路上,我活得像我自己。
“你……”顾晏平被我的决绝噎住了,他死死地盯着我,
仿佛想从我脸上看出一丝动摇和伪装。但我没有。我的内心平静得像一口古井。
哀莫大于心死,大概就是这种感觉。“这件事,是我对不住你。”良久,他终于败下阵来,
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处理好。”“处理?你怎么处理?”我反问,
“把白薇薇从你心里挖出去?还是把我变成她?”他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顾晏平,
我们到此为止吧。”我收回目光,语气平静地陈述一个事实,“明天一早,我就搬去招待所。
离婚报告,我会尽快交上去。”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我的东西不多,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从家里带来的农技书,还有一个小木匣子,
里面装着我所有的积蓄。我动作麻利,没有一丝拖泥带水。顾晏平就那么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昏黄的灯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寂寥。
房间里只剩下衣物摩擦的窸窣声。当我把最后一件衣服叠好放进包袱里时,他终于再次开口,
声音嘶哑得厉害。“非要这样吗?”我没有回答,只是拉上了包袱的拉链。“林晚南!
”他猛地跨上一步,从身后抱住了我,灼热的胸膛紧紧贴着我的后背,“别走,算我求你。
”这是他第一次,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我说话。他的手臂像铁箍一样,将我禁锢在他的怀里。
我能感觉到他滚烫的体温,听到他因为发烧而急促的心跳。要是放在几个小时前,
我一定会心软,会沉溺在他这突如其来的亲近里。但现在,我只觉得恶心。“放开。
”我冷冷地说。“我不放!”他抱得更紧了,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呼吸灼热,“晚南,
我知道是我**,我不求你原谅,但你不能走。我们是军婚,受法律保护,
不是你想离就能离的!”他开始耍无赖了。用军婚这道枷锁来捆住我。我气得发笑,
挣扎着想要摆脱他的桎梏:“顾晏平,你还要不要脸?你用这身军装保护人民,
却用军婚来困住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谁说你不爱我?”他固执地反驳,“你要是不爱我,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这个问题,问得**的好。我为什么对他好?
因为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因为我觉得女人嫁了人,就该对丈夫好,就该操持好一个家。
这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我刻在骨子里的本分。可这份本分,在他眼里,
却成了我爱他的证据。何其可笑!“我纠正一下,”我停止了挣扎,声音平静下来,
“我不是不爱你,我是从来就没爱过你。我对你好,是因为我把你当成我的‘工作’,
我的‘任务’。现在,我不想干了,我要辞职。”我能感觉到,我背后的身体,瞬间僵硬了。
“辞职”这个词,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精准地刺进了他最骄傲的地方。他大概从未想过,
他在我心里,竟然只是一个“任务”。他的手臂,缓缓地松开了。我终于获得了自由。
我转过身,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娇柔的女声响了起来,带着哭腔。“晏平哥!
晏平哥你怎么样了?我听说你受伤了!”下一秒,房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
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梳着两条麻花辫的女人冲了进来,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
她径直扑向顾晏平,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是白薇薇。她回来了。
04白薇薇就像一只受了惊的蝴蝶,一头扎进了顾晏平的怀里,哭得梨花带雨。“晏平哥,
我好担心你!我一听到你受伤的消息,就跟农场请了假,坐了一天一夜的拖拉机赶回来的!
你怎么样了?伤得重不重?”她仰着那张与照片上别无二致的脸,满眼都是心疼和爱慕。
而顾晏平,在看到她出现的那一刻,整个人都石化了,任由她抱着,忘了推开,
也忘了我还在场。我站在一旁,像一个局外人,冷静地看着眼前这幅“久别重逢,
深情不渝”的感人画面。不得不说,他们俩站在一起,确实很般配。男的英俊挺拔,
女的娇俏可人,天造地设的一对。而我,一个粗手大脚的乡下丫头,站在这里,
简直就是多余的。“咳。”我清了清嗓子,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
白薇薇像是才发现我的存在,她松开顾晏平,转过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眼神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怯懦和探究。“这位是……?”不等顾晏平开口,
我率自我介绍:“你好,我是林晚南,顾晏平的妻子。
”我特意在“妻子”两个字上加了重音。白薇薇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顾晏平,声音都在发抖:“晏平哥,她……她说的是真的吗?你结婚了?
”顾晏平的表情狼狈到了极点,他下意识地想来拉我的手,却被我侧身躲过。“薇薇,
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我抢在他前面开口,脸上挂着“和善”的微笑,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和顾团长是经组织介绍,合法登记的夫妻,受法律保护。白同志,
你大半夜闯进我们夫妻的房间,抱着我的丈夫,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吧?”我这番话,
说得不卑不亢,掷地有声。白薇薇被我堵得哑口无言,一张小脸涨得通红,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看起来好不可怜。“我……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太担心晏平哥了……”她咬着唇,委屈地辩解。“担心他,也该有个度。
”我寸步不让,“毕竟男女有别,更何况他还是有妇之夫。白同志是从大城市来的,
应该比我这个乡下人更懂规矩吧?”我这番话,明着是讲规矩,
暗地里却是在讽刺她没有分寸。在部队大院里,最重什么?最重规矩和脸面!
白薇薇果然受不了这个,她跺了跺脚,哭着对顾晏平说:“晏平哥,她……她欺负我!
”好一招恶人先告状。我抱着臂,好整以暇地看着顾晏平,想看他怎么处理这场闹剧。
是维护我这个“正牌妻子”,还是心疼他那“白月光”?顾晏平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他看了一眼哭得楚楚可怜的白薇薇,又看了一眼一脸冷漠的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晚南,
你少说两句。”最终,他还是选择先安抚“客人”,“薇薇她刚从农场回来,什么都不知道。
”呵,男人。我心里冷笑一声。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可以随便抱别人的丈夫吗?
“行,我不说。”我点了点头,拎起脚边的包袱,“你们聊,我走。”我懒得再看这场烂戏。
“站住!”顾晏平再次喝止我,声音里带上了怒气,“林晚南,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他觉得我在“闹”。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一字一句地问:“顾晏平,到底是谁在闹?
”是我吗?是我让白薇薇大半夜闯进来的吗?是我让她抱着你不撒手的吗?
是我逼着你在心里把我们两个女人比来比去的吗?“晏平哥,都是我的错,你别跟嫂子吵架。
”白薇薇拉了拉顾晏平的袖子,善解人意地说,“我……我还是先走吧。”她说着,
就抹着眼泪往外走,那一步三回头的样子,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薇薇!
”顾晏平果然急了,他想去追,却又顾忌着我。就在这拉扯的瞬间,他因为高烧和情绪激动,
身体晃了晃,直直地朝地上倒去。“晏平哥!”“顾晏平!”我和白薇薇同时惊呼出声。
我下意识地想去扶他,但白薇薇比我更快一步。她冲过去,用自己瘦弱的肩膀,
稳稳地架住了顾晏平高大的身体。“晏平哥,你怎么样了?你别吓我!”她哭喊着,
声音里满是真实的惊慌。而顾晏平,在倒下的那一刻,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了,
他下意识地抓住离他最近的人,嘴里含糊地念着:“薇薇……别走……”05“薇薇,
别走……”这四个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我的心上。我伸出去的手,
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看着白薇薇费力地将顾晏平扶到床上,为他盖好被子,
又熟练地拧了毛巾给他敷在额头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仿佛演练了千百遍。而我,
这个正牌的“顾太太”,却像个多余的道具,杵在一旁,格格不入。“嫂子,”白薇薇忙完,
站起身,红着眼睛对我说,“对不起,刚才是我太冲动了。晏平哥他发着高烧,需要人照顾,
我……我能不能留下来照顾他?”她用的是商量的语气,眼神却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坚定。
仿佛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我看着她,忽然就笑了。“好啊。”我说。白薇薇愣住了,
显然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爽快。“你想照顾,就照顾吧。”我拎起我的包袱,走到她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