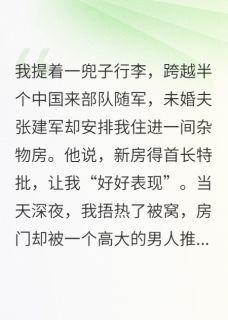
我提着一兜子行李,跨越半个中国来部队随军,未婚夫张建军却安排我住进一间杂物房。
他说,新房得首长特批,让我“好好表现”。当天深夜,我捂热了被窝,
房门却被一个高大的男人推开,他肩上扛着星,眼神像冰,
沉声问:“你就是张建军那个要结婚的对象?”我抓紧了衣领,这男人,
不就是白天在训练场上,那个所有人都怕的活阎王,顾长风首长吗?他怎么会知道我,
还深更半夜找上门来?01“同志,开开门,我是顾长风。
”冰冷、克制的男声在门外响起时,我正把最后一件的确良衬衫塞进枕头底下。我叫林晚意,
为了和未婚夫张建军结婚,我放弃了村里小学老师的铁饭碗,揣着全部家当,
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一头扎进了这戒备森严的军区大院。“建军,是你吗?
”我心里一喜,以为是刚说去开会的张建军回来了,趿拉着鞋就去开门。
门“吱呀”一声拉开,门口站着的却是一个我只敢在白天远远看过一眼的男人。顾长风。
整个大院里,最有权势、也最让人闻风丧胆的男人。他穿着一身挺括的军装,
肩章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反射出令人心悸的光。他的目光像手术刀,精准地落在我脸上,
让我刚才那点因为见到“熟人”而升起的温度,瞬间冻结。“顾、顾首长?
”我紧张得舌头都打了结。他怎么会来?还知道我的名字?
张建军把我领进这间巴掌大的杂物房时,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又是愧疚又是理所当然。
“晚意,你先委屈几天。咱们结婚得打报告,分房子得顾首长点头。他在观察我们呢,
你可得好好表现,别给我丢人。”他嘴里的“好好表现”四个字,说得意味深长。此刻,
这位能决定我命运的顾首长,就站在我门口。他的眼神沉静如水,却带着一股子压迫感,
仿佛能看穿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布睡衣。“张建军呢?”他开口,
声音比这初冬的夜风还冷。“他……他说去团里开会了。”我攥着衣角,手心全是汗。
顾长风的眉头几不可见地皱了一下,他没有再追问,而是将手上拎着的一个网兜递了过来,
里面是两个还冒着热气的白面馒头和一盒铝制饭盒。“开会前,他拜托我送过来的。怕你饿。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可我心里却“咯噔”一下。张建军临走前,我问他晚饭怎么办,
他只不耐烦地丢下一句“自己想办法,我哪有空”,怎么会突然有这份心?我接过饭盒的手,
微微发抖。饭盒温热的触感,和他手指不经意间触碰的冰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谢谢首长。”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他“嗯”了一声,目光却越过我的肩膀,
扫了一眼屋内。那眼神,让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审视的物件。这间杂物房,
除了我带来的一个木箱子,就只有一张硬板床,连张桌子都没有。“早点休息。
”他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高大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走廊尽头。我关上门,
背靠着冰冷的门板,心脏还在狂跳。打开饭盒,里面是满满的红烧肉,肥瘦相间,香气扑鼻。
在这个年代,这可是普通人家过年才能吃上的硬菜。我却没有半点食欲。
张建军的冷漠和顾长风的“热心”,像两只手,把我拽向了两个极端。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半夜,隔壁传来压抑的争吵声,
我听见一个女人尖着嗓子骂:“张建军你个没良心的!为了个乡下女人就要跟我分?
我告诉你,没门!”我浑身的血,瞬间凉了。02第二天,
我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去水房打水,正撞见几个军嫂在窃窃私语。她们看见我,
声音戛然而止,眼神里充满了探究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同情。
其中一个快人快语的李嫂子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小林啊,你就是建军的对象吧?
你可得把人看紧点。”她朝另一栋楼扬了扬下巴,“我们大院之花,宣传科的王干事,
可正跟建军打得火热呢。”我的心,一寸寸沉了下去。昨晚的争吵声,原来不是幻觉。
我端着水盆往回走,魂不守舍,没注意脚下,被一块石头绊了个趔趄,盆里的水洒了大半,
溅湿了我的裤腿。“同志,小心。”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稳稳地扶住了我的胳膊。我一抬头,
又对上了顾长风那双深邃的眼睛。他今天穿着作训服,更显得身姿挺拔。
他手上拿着一个搪瓷缸,看样子也是刚晨练回来。“谢谢首长。”我赶紧站稳,
和他拉开距离。他松开手,目光落在我湿透的裤腿上,眉头又皱了起来。“大院里人多口杂,
不该听的别往心里去。有困难,可以打报告。”他这话,是在点我吗?
他知道王干事和张建军的事?“打报告”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
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在部队里,打报告,就意味着寻求组织解决问题。“我的事,
我自己能解决。”我咬着唇,倔强地回了一句。我不想让他看扁,
更不想让他觉得我是个只会哭哭啼啼告状的女人。顾长风看着我,
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不再是纯粹的冰冷和审视。
他那道据说是在战场上留下的、从眉骨划到鬓角的疤痕,也因此显得不那么骇人了。
他没再说什么,转身接了水,离开前,却把手里一直没打开的油纸包放在了水池边上。
“今天食堂的肉包子,味道不错。”又是这样。不动声色,却把东西硬塞给了你。
我捏着那个还温热的油纸包,心里五味杂陈。回到杂物房,张建军还没回来。我掰开肉包子,
里面是扎扎实实的肉馅,香得我直流口水。可我一口都吃不下去。我决定不等了。
我不能像个傻子一样,坐在这里等着别人来宣判我的命运。我换上最体面的那件的确良衬衫,
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径直走向了宣传科的办公楼。我倒要看看,那个“大院之花”,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刚到宣传科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娇俏的笑声。“建军哥,你真好,
还特地给我带了肉包子。你那个乡下来的未婚妻,没起疑心吧?”是王干事的声音。
我浑身僵硬,推门的手,停在了半空中。03门没关严,透过门缝,
我清楚地看到张建军正殷勤地给一个穿着时髦列宁装的女人削苹果。那个女人,
想必就是王干事,王雪梅。她长得确实很漂亮,皮肤白皙,
烫着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浪卷发,看我的未婚夫时,眼睛里像有钩子。“她?
一个乡下丫头,没见过世面,我随便哄两句就信了。雪梅,你放心,
等我利用她把房子申请下来,我就跟她摊牌。”张建军的声音里,满是我从未听过的谄媚。
“那顾首长那边……”王雪梅的语气里有些担忧。“顾首长日理万机,
哪有空管我们这点小事。再说了,他那种活阎王,估计这辈子都不会懂什么叫男欢女爱。
”张建军嗤笑一声,把削好的苹果递到王雪梅嘴边。我的血气直往脑门上涌。原来,
我放弃一切奔赴的爱情,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我就是他用来申请福利房的垫脚石。
我没有冲进去撕破脸,那太难看了。我转身,一步步走回那间冰冷的杂物房,
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下午,张建军回来了。他提着一小袋水果硬糖,
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晚意,累了吧?快吃糖。我今天开会,领导还表扬我了,
说我们的结婚报告很快就能批下来。”他把我当傻子。我看着他,平静地问:“是吗?
哪个领导表扬你了?是王干事吗?”张建军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你胡说什么?
王干事是我的同事,我们是纯洁的革命同志关系!
”“纯洁到可以帮你吃掉我未来丈夫送的肉包子?”我冷笑一声,
把早上顾长风给我的那个油纸包扔在他面前。虽然里面的包子我已经处理掉了,
但这个动作足够让他心惊。他果然慌了,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林晚意,
你跟踪我?你思想怎么这么龌龊!”“龌龊?”我甩开他的手,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张建军,利用我给你当跳板拿房子,然后一脚踹开,到底是谁龌龊!
”我们的争吵声引来了邻居的围观。就在这时,走廊那头传来一声中气十足的咳嗽。
是顾长风。他还是那身军装,只是手里多了一份文件。他一出现,
所有看热闹的人都瞬间噤声,自动让开一条路。他走到我们门口,
目光在我和张建军之间扫了一圈,最后定格在张建军脸上,
声音冷得像冰碴子:“张建军同志,看来你的思想很有问题。组织上对军人的作风问题,
向来是零容忍。”张建军的脸,一下子白了。他结结巴巴地解释:“首长,您别听她胡说,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点小误会……”“误会?”顾长风扬了扬手里的文件,“那你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的结婚报告上,填的是未婚。而王雪梅同志的调职申请上,担保人也是你?
”他把文件“啪”地一下拍在门框上,动作不大,却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张建军的心上。
我愣住了。他竟然……连这个都查了?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我的?
又为什么要帮我到这个地步?04张建军彻底蔫了,像只斗败的公鸡,垂着头不敢说话。
王雪梅不知什么时候也跟了过来,躲在人群后面,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林晚意同志,
”顾长风转向我,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依旧是公事公办的口吻,
“部队是最讲究纪律和原则的地方。你受了委屈,组织会为你做主。你现在有什么要求,
可以提出来。”他把选择权交给了我。是在逼我,也是在给我机会。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深吸一口气,迎上张建军祈求的目光,
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取消结婚报告。第二,我要他,张建军,
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道歉。”我不要赔偿,不要他的前途尽毁,我只要我的清白和尊严。
张建军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当众道歉,比杀了他还难受。“林晚意,你别太过分!
”他恼羞成怒地低吼。“过分?”顾长风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如果你觉得当众道歉过分,
那我们可以聊聊欺骗组织、道德败坏的处分问题。”这句话,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建军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我……道歉。”那天的道歉,
成了整个大院的头条新闻。张建军站在操练场边上,对着我鞠躬,说了声“对不起”。
我没有看他,转身就走。这场闹剧,该结束了。事情处理完,
我面临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我该去哪儿。随军家属的身份没了,我没理由再待在部队。
可我老家的工作也辞了,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只会成为全村的笑柄。我就像一片浮萍,
无处扎根。晚上,我收拾好我那只小小的木箱子,准备天一亮就离开。门又被敲响了。
我以为是张建军不死心,没好气地喊了声:“谁啊?”“我。”是顾长风。我打开门,
他依旧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份介绍信。“后勤处的招待所,还有一个床位。
介绍信我开好了,你可以暂时住过去。”我愣愣地看着他。“为什么?
”“你是因为部队的人受了委屈,组织有责任。”他给出的理由,永远那么冠冕堂皇。
“然后呢?”我追问,“住过去之后呢?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招待所我也住不了几天。
”顾长风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思考我的问题。然后,他递给我一张报纸,
上面用红笔圈出了一则启事:军区纺织厂招工。“明天上午八点,去厂里找王厂长。就说,
是我让你去的。”他顿了顿,补充道,“他们缺一个会写字的,做出纳。我相信,
小学老师能胜任。”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他不仅给我找了住处,
连工作都替我安排好了。他就像一个沉默的巨人,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为我撑起了一片天。
我捏着那张报纸,指尖都在发烫。我抬头看着他,第一次,认真地、仔细地看着他。
他的眼睛很深,像藏着星辰大海。“顾首长,我……”我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感谢。
他却只是抬手,用他那带着薄茧的指腹,轻轻擦过我的眼角。动作快得像个错觉。“别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