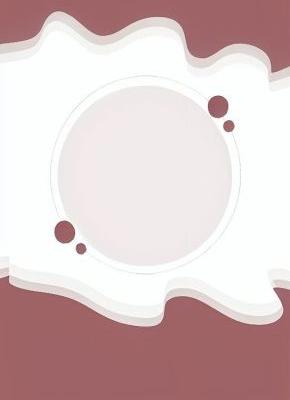
1上书房的墨痕天启二十三年的春阳,把上书房的青石板晒得发烫。玉兰花落了满地,
往日里皇子们震得梁木发颤的读书声,
如今只剩勋贵子弟们有一搭没一搭的翻书声——旧太子被废时溅在红墙上的血,
虽已被雨水冲淡,却把这处皇室学堂的规矩,也冲得松散了。裴时安坐在靠窗的位置,
腿还够不着地面,晃悠着一双青布靴。他面前的《论语》摊开在“学而时习之”那页,
狼毫笔搁在砚台边,墨汁早已干透——半个时辰前,他就把夫子布置的抄录功课写完了。
“王家二郎,”他忽然开口,声音清亮得像檐角的铜铃,刚好戳破隔壁桌的沉默,
“‘有朋自远方来’的下句,你莫不是要想到日落?”王家小公子猛地抬头,
脸红得像熟透的樱桃,攥着笔杆的指节泛白:“裴时安!我写不写得完,与你何干?
”“自然相干。”裴时安起身,踱到他桌前,指尖在砚台边轻轻一抹,沾了点浓墨,
趁对方不备,往他月白袖口上一蹭,留下个黑印子,“你看,墨都要干了,夫子要是来查,
你这手心又要添道戒尺印。哦对了,你昨日藏在书箱里的桂花糖,是不是被夫子搜走了?
”王家小公子“腾”地站起来,眼眶瞬间红了:“是你告的密!”“我可没那闲心。
”裴时安晃了晃手,踱回自己座位,从怀里摸出块麦芽糖,剥了纸含在嘴里,甜香漫开,
“是你藏糖时,糖纸露了半角,夫子眼尖着呢。再说了,你要是像我一样,
天不亮就起来温书,把功课提前做完,哪有功夫藏糖?”这是裴时安四岁进宫伴读时,
就摸出的门道。那会儿旧太子还在,上书房规矩严得能掉根针,他年纪最小,
却最会找窍门——每天寅时就爬起来,就着廊下的灯笼抄书,夫子布置的功课,
他永远是第一个交。剩下的时辰,要么在院子里捉蟋蟀,要么就“观察”同窗们的窘境。
有次谢家长子磨磨蹭蹭到午时,还没把《千字文》抄完,夫子举着戒尺就要抽他手心。
裴时安突然举手:“夫子,谢兄昨日说要帮母亲抄经,许是累着了,才耽误了功课。
不如让他先回去歇息,明日再补?”夫子点头应了,谢家长子却堵着他在廊下质问。
裴时安笑得无辜:“我这是帮你解围,你该谢我才是。再说了,你前晚偷跑去赌坊,
被我撞见时,怎么不说?”谢家长子脸白了,再也不敢找他麻烦。久而久之,
裴时安成了上书房的“小霸王”。没人敢跟他比功课,
更没人敢在他面前拖沓——谁都知道,只要慢一步,
就会被他“好心”地揭露出更多糗事。午时的梆子响了,夫子来查功课。
王家小公子果然没写完,被夫子罚站在廊下,手心还挨了三道戒尺。裴时安坐在窗边,
看着他通红的眼眶,含着麦芽糖的嘴角,又勾起了那抹漫不经心的笑。
他摸出藏在袖袋里的蟋蟀罐,罐子里的蟋蟀“瞿瞿”叫着,
像是在为他的“胜利”喝彩。窗外的玉兰花又落了几片,落在他的书页上,沾了点墨痕,
倒像是幅小小的画。2月白与青衫天启二十七年的秋,国子监的老槐树落下第一片叶子时,
裴时安提着书箱,站在了朱红大门前。门柱上“学而优则仕”的鎏金大字,
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他以上书房结业榜首的身份,选进了这金陵最顶尖的书院。
“让让。”清冷的女声突然传来,裴时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撞了一下。他回头,
看见个穿月白襦裙的少女,梳着双丫髻,发间只插了支素银簪,怀里抱着摞书,
指尖泛着淡淡的青白色,显然是抱得久了。她的眉眼很淡,像水墨画里晕开的几笔,
只是眼神太冷,扫过他时,没半分波澜,仿佛只是撞了块石头。“你走路不看路?
”裴时安挑眉,故意往路中间挪了挪,挡住她的去路,“这石板路这么宽,
你偏要往我身上撞,该不是故意的吧?”少女皱了皱眉,抱着书往旁边挪了挪,
想绕开他:“我已说了抱歉,公子若是无事,还请让让。”“我要是不让呢?
”裴时安伸手,指尖差点碰到她怀里的书脊,“你这书里写的什么?
是不是藏了什么好玩的东西,怕被人看见?”少女脚步一顿,抬眼看向他。这一次,
她的眼里终于有了点情绪——是厌烦。她没再说话,只是将书抱得更紧,
侧身从他胳膊下钻了过去,快步往前走,月白裙摆扫过地面,带起几片槐树叶。
旁边的同窗周明远凑过来,拍了拍裴时安的肩:“时安,你别惹她。她是舒家的嫡女,
舒娴心。”“舒家?兵部侍郎那家?
”裴时安想起父亲提过的旧事——舒侍郎宠妾灭妻,把正室崔氏活活气死,
“原来她就是崔氏的女儿。”“可不是嘛。”周明远压低声音,往舒娴心的方向瞥了眼,
“听说她在舒家过得不好,继母总苛待她,连月例都克扣。要不是她母亲是清河崔氏的人,
继母怕是早对她动手了。她身边那个丫鬟,叫青黛,是崔家专门培养的,医武双绝,
谁敢欺负她,青黛能直接拎着剑找上门。”裴时安哦了一声,目光追着舒娴心的背影。
她走到不远处的石桌旁,独自坐下,把书摊开,指尖划过书页,看得格外认真。
阳光落在她身上,却没暖化她周身的冷意,倒像是给她镀了层淡淡的光。他忽然觉得,
这个舒娴心,比上书房那些只会哭鼻子的同窗,有趣多了。接下来的日子,
裴时安成了舒娴心的“影子”。她在藏书楼找《礼记》,他就趁她转身时,把书抽出来,
藏在最顶层的书架上,看着她踮着脚找了半个时辰,才慢悠悠地走过去,
“恰巧”把书抽出来:“舒姑娘,你找的是这本?”她在院子里背书,
他就带着周明远等人玩投壶,喊得震天响。她皱着眉换了个地方,他就跟着换,
直到她背不下去,合上书起身离开,他才停下,看着她的背影,笑得得意。食堂里,
她排队打饭,他就抢先一步,把最后一份糖醋鱼买走,还故意在她面前吃得香:“这鱼真鲜,
舒姑娘要不要尝尝?”舒娴心从不跟他争执,只是每次被捉弄后,都会默默换个地方,
或者加快做事的速度,尽量避开他。可裴时安偏不依,她越躲,
他越追得紧——逗她皱眉、看她冷着脸,成了国子监里最有意思的事。
有次青黛实在看不下去,挡在舒娴心面前,冷眼看着裴时安:“裴公子,我家**性子淡,
不喜玩笑,还请公子自重。”裴时安看着青黛腰间的剑,挑了挑眉:“我跟舒姑娘闹着玩,
与你何干?”“我是**的丫鬟,自然要护着**。”青黛的手按在剑柄上,眼神凌厉。
“青黛。”舒娴心拉了拉青黛的衣袖,摇了摇头,“我们走。”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裴时安摸了摸下巴。他忽然觉得,这个舒娴心,不仅有趣,
还很倔——像株长在石缝里的草,看着弱,却不容易折。
3侧门的糖糕天启二十八年的深秋,一场冷雨过后,国子监的空气里添了几分寒意。
裴时安逃课去校外买糖糕,回来时路过侧门,远远就看见两个穿着舒家仆役服饰的嬷嬷,
正围着个人骂。走近了才看清,被围在中间的是舒娴心。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素色襦裙,
怀里抱着刚买的笔墨,头低着,手指攥着裙摆,指节发白。“**,您这月的月例,
夫人说要留着给二**买新衣裳,就不给您了。”左边的嬷嬷叉着腰,
语气刻薄得像冰碴子,“您也别不知足,能在国子监读书,已是夫人开恩了。要是换了别人,
早被赶去家学里跟那些庶子一起读了。”舒娴心的声音很轻,
却带着点倔强:“母亲答应过我,每月给我二两月例,供我买笔墨。”“那是以前!
”右边的嬷嬷冷笑,“现在二**要参加赏花宴,正需要钱。您一个快要嫁人的姑娘,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不如省点钱,给二**添件首饰。”“我不嫁。”舒娴心抬起头,
眼里泛着水光,却没掉眼泪,“我要留在国子监读书,将来靠自己谋生。”“哟,
还想自己谋生?”左边的嬷嬷上前一步,伸手就要扯她的胳膊,“您以为您是哪家的**?
崔家早就不管您了,您要是不听话,夫人有的是办法收拾您!”就在这时,
裴时安突然冲过去,一把打开那嬷嬷的手。他刚买的糖糕还揣在怀里,
温热的触感透过油纸传来,让他的语气也带了点暖意:“住手!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也敢在国子监门口欺负人?”嬷嬷们愣了一下,看清是裴时安,脸色顿时变了。
谁不知道裴相之子在国子监的地位,连夫子都要让他三分。她们讪讪地收了手,
嘴里嘟囔着:“我们是舒家的人,管自家**的事,与裴公子无关。”“舒家的事?
”裴时安把舒娴心护在身后,眼神冷了下来,“舒侍郎宠妾灭妻,让嫡女受委屈,
这事要是传到宫里,你们说,陛下会不会管?还有,国子监的规矩,外府仆役不得擅闯,
你们这是想违反规矩,被赶出去吗?”嬷嬷们吓得脸都白了,连忙躬身行礼:“是我们糊涂,
我们这就走,这就走!”说罢,匆匆忙忙地跑了,连头都没敢回。裴时安回头,
看见舒娴心还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他从怀里摸出糖糕,递到她面前——用油纸包着,
还冒着热气,甜香飘进鼻腔,很是诱人。“给你,甜的,吃了就不难受了。”舒娴心抬起头,
眼里带着点惊讶,还有点茫然。她看着那块糖糕,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还在时,
也曾在这样的冷天里,给她买过这样的糖糕。那时候,母亲会把糖糕剥了纸,递到她嘴边,
笑着说:“囡囡,吃了糖糕,就不冷了。”“我不吃,谢谢。”她摇了摇头,
往后退了一步,想拉开距离。“拿着吧。”裴时安把糖糕塞进她手里,
油纸的温热透过指尖传来,“我知道你月例被克扣了,这糖糕算我送你的。还有,
以后要是再有人欺负你,就告诉我,我帮你出头。”舒娴心握着糖糕,
心里忽然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她看着裴时安转身离开的背影,青色的儒衫在秋风里晃了晃,
竟不像往常那样讨厌了。那天下午,舒娴心在石桌旁看书时,青黛忽然说:“**,
裴公子好像也没那么讨厌。”舒娴心没说话,只是低头看着手里的书,嘴角却悄悄勾了勾。
风卷起书页,也卷起了那点甜香,漫在空气里,很是温柔。4夕阳与心事国子监的老槐树,
是全校最老的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枝叶繁茂得能遮住大半个院子。
从天启二十九年的春开始,这棵树下,就多了两个身影。每天傍晚,裴时安都会拿着本书,
坐在树下等舒娴心。她做完功课,就会走过来,坐在他旁边的石凳上,两人一起看夕阳,
一起聊功课,偶尔也会聊起家里的事。“我母亲是清河崔氏的嫡女,
”舒娴心望着飘落的槐树叶,声音很轻,像羽毛拂过心尖,“她以前总说,
女孩子也要读书,才能明事理。她还教我辨玉,说玉有灵性,能识人。
”她从怀里摸出块小小的玉佩,是暖白色的,上面刻着简单的缠枝纹:“这是母亲留给我的,
她说等我长大了,就把它送给我喜欢的人。”裴时安没说话,只是伸手,
帮她拂掉了落在发间的一片槐叶。夕阳的光落在她的发梢,泛着淡淡的金色,他忽然觉得,
这一刻的舒娴心,不像平时那样冷了,倒像是块被温水泡软的玉。“以后有我呢。
”他轻声说,“我会护着你,不让你再受委屈。”舒娴心的脸微微红了,低下头,
看着自己的脚尖。秋风卷起她的裙摆,也卷起了少年少女间,那点不敢说破的青涩情愫。
有次裴时安逃课去捉蟋蟀,不小心摔破了膝盖,流了不少血。他一瘸一拐地回到国子监,
刚走到老槐树下,就被舒娴心看见了。“你怎么弄的?”她快步走过来,扶着他的胳膊,
眼里满是担忧。“没事,摔了一下。”裴时安想装作没事,可膝盖一弯,还是疼得皱了眉。
舒娴心立刻让青黛拿来药箱,蹲在他面前,小心翼翼地帮他清理伤口。她的指尖很轻,
碰到伤口时,裴时安竟觉得不怎么疼了。“以后别再逃课去捉蟋蟀了。”她一边敷药,
一边轻声说,“要是摔得更重,怎么办?”“知道了。”裴时安看着她认真的侧脸,
心里暖暖的,“以后我不逃课了,陪你一起看书。”舒娴心的手顿了一下,没说话,
只是把绷带缠得更紧了些。还有次夫子布置了篇策论,题目是“论女子读书”。
舒娴心写得很认真,却被夫子质疑抄袭——夫子觉得,女子写不出这样有见地的策论。
裴时安立刻站起来,拿着自己的策论说:“夫子,舒姑娘的策论,是与我一起讨论的。您看,
我们的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表述不同。”夫子翻了翻两人的策论,
果然有很多相通之处,便不再质疑。课后,舒娴心对裴时安说:“谢谢你。”“我们之间,
不用这么客气。”裴时安笑着说,从怀里摸出块糖糕,递给她,“刚买的,还热着。
”舒娴心接过糖糕,咬了一口,甜香在嘴里漫开,心里也甜甜的。她看着裴时安的笑脸,
忽然觉得,国子监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天启三十年的秋,
老槐树叶落得最盛的时候,裴时安把自己的月例分了一半给舒娴心。“你拿着,”他说,
“买些新笔墨,再添件新衣裳。天快冷了,别冻着。”舒娴心握着那些银子,
眼眶泛红:“裴时安,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裴时安看着她,
眼神很亮:“因为我想对你好。”夕阳落在他们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老槐树下的风,
也变得温柔起来。5北疆的风沙天启三十一年的冬,来得格外早。
国子监的老槐树还没掉完叶子,就下了第一场雪。雪下得不大,却把金陵城的空气,
都冻得发僵。舒家出事的消息,就是在这样一个雪天传来的。
那天舒娴心正在跟裴时安一起整理笔记,青黛匆匆跑进来,脸色惨白:“**,不好了!
老爷他……他在兵部任职时,私通敌国,被削去官职,全家被贬往北疆了!
”舒娴心手里的笔“啪”地掉在地上,墨汁溅了一地。她看着青黛,嘴唇动了动,
却没说出话来。裴时安扶住她,轻声说:“别怕,我陪你回舒家看看。”舒家的院子里,
一片狼藉。舒侍郎坐在椅子上,脸色灰败;继母在一旁哭哭啼啼,
嘴里还骂着:“都是你这个扫把星!要不是你,我们舒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舒娴心没理她,只是默默地回房收拾行李。她把母亲留下的玉佩、旧书,
还有裴时安送她的糖糕纸,都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子里。裴时安站在门口,看着她忙碌的身影,
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出发那天,天还没亮,裴时安就赶到了城门口。雪还在下,
地上积了薄薄一层。舒娴心穿着件素色的布裙,站在马车旁,头发上落了点雪,
像撒了层碎盐。“裴时安,你怎么来了?”她看见他,眼里泛起了泪光。“我来送你。
”裴时安走到她面前,从怀里摸出个锦盒,打开——里面是枚青玉佩,
跟她母亲留给她的那枚很像,“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你拿着。等你以后回来,
再跟我要回来。”舒娴心接过玉佩,指尖触到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她把玉佩紧紧攥在手里,
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裴时安,”她看着他,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我会回来的。等我回来,我就把玉佩还给你。”“好。”裴时安点头,声音有些沙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