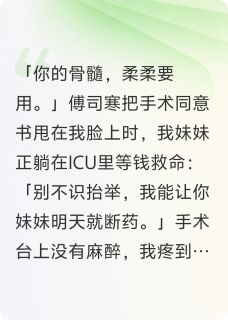
"把衣服脱了,躺上去。"
女医生冷冰冰的声音让我打了个寒颤。
我蜷缩在检查床上,金属台的冰冷透过薄薄的病号服渗入骨髓。
"有点疼,忍着点。"
穿刺针扎进我后背时,我咬破了嘴唇。
铁锈味在口腔里蔓延,我却觉得痛快——至少这疼痛是真实的,不像傅司寒那些虚情假意的"我爱你"。
"林晚?你怎么在这?"
检查室的门突然被推开,陈柔甜腻的声音刺入耳膜。
我慌乱地拉下衣服,却看到她挽着傅司寒的手臂站在门口。
"寒哥,你看她好像只被剥了皮的兔子~"陈柔咯咯笑着,往傅司寒怀里靠了靠。
傅司寒皱眉:"检查做完了吗?柔柔也要用这个检查室。"
我手指死死攥住衣角,指甲陷入掌心。
"还有两项检查。"医生低头看着病历,"病人严重贫血,建议先补充铁剂,推迟一周手术。"
"不行。"傅司寒斩钉截铁,"柔柔等不起。"
医生犹豫道:"但捐献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她死了吗?"傅司寒打断他,眼神像看一件物品一样扫过我,"不是还好好活着?"
我胸口像被重锤击中,呼吸都带着血腥味。
"寒哥~"陈柔撒娇地晃晃他的手臂,"人家不想在这个房间做检查嘛,刚被**躺过,脏死了~"
傅司寒立刻柔声安慰:"好,我们换一间。"
他们转身离开时,我听见陈柔压低的声音:
"寒哥,那个保姆的女儿会不会临阵脱逃啊?"
"她敢。"傅司寒冷笑,"她妹妹的命在我手里。"
门关上了,我的眼泪终于砸下来。
原来在傅司寒的朋友圈里,我只是个"保姆的女儿"。
我母亲确实是陈家的家庭医生,但那是顶尖医学专家才够格担任的职位。
而现在,我连母亲的尊严都没能守住。
"别动,还有最后一项检查。"
医生机械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我像个破布娃娃一样被摆弄着,完成所有术前检查。
走出检查室时,我鬼使神差地绕到了VIP病房区。
陈柔的病房门虚掩着,里面传出她夸张的笑声。
"...真的笑死我了,她还真以为寒哥爱她呢!"
我僵在原地,血液凝固。
"三年诶,就为了等我的病治好,寒哥居然忍了那么久。"陈柔的声音甜得发腻,"不过也值了,现在连骨髓都是现成的~"
护士谄媚地附和:"陈**好福气,傅先生对您真是痴心一片。"
"那当然~"陈柔得意洋洋,"那个**不过是我的替代品,现在连替代品都算不上,就是个骨髓容器~"
我扶着墙,双腿发抖。
原来我珍视的那三年,只是傅司寒等待陈柔的倒计时。
"对了,"陈柔突然压低声音,"明天手术,真的不用给她打麻药?"
"傅先生交代的。"护士的声音带着犹豫,"说您对**过敏,捐献者体内不能有任何药物残留......"
"噗——"陈柔笑出声,"这种鬼话他也编得出来?不过......"她声音冷下来,"我确实不想让那**好过,一想到她的东西要进到我身体里就恶心。"
我胃里翻江倒海,扶着墙干呕起来。
"谁在外面?"陈柔警觉地问。
我仓皇逃进楼梯间,瘫坐在台阶上,抱紧发抖的双腿。
原来明天的地狱,远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深夜,我偷偷溜进妹妹的病房。
林月依旧昏迷,瘦得脱相的小脸在月光下几乎透明。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生怕一用力就会碎掉。
"月月,姐姐明天要做个手术。"我声音哽咽,"可能几天不能来看你,你要坚强......"
输液架上挂着三袋药水,我下意识看了眼标签,突然僵住。
这不是医生之前开的进口药,而是最基础的替代药品。
我颤抖着翻看医嘱单,上面龙飞凤舞的签名赫然是傅司寒最得力的助手。
门突然被推开,值班护士走了进来。
"林**?"她惊讶地看着我,"这么晚了......"
"这些药怎么回事?"我指着输液袋,声音发抖,"为什么换成了替代品?"
护士脸色变了:"我、我不清楚......"
"告诉我!"我抓住她的手臂,"我妹妹会死的!"
护士慌乱地看了眼门外,压低声音:"是傅先生的意思...说如果您明天不配合手术,就......"
她没说完,但我懂了。
傅司寒在拿我妹妹的命当筹码。
我松开护士,跌坐在椅子上,突然笑出声。
笑声在寂静的病房里格外瘆人,护士吓得后退两步。
"林**,您、您没事吧?"
我摇摇头,擦掉笑出的眼泪:"没事,你出去吧。"
护士逃也似地离开了。
我俯身亲吻妹妹的额头,在她耳边轻声说:
"月月,姐姐发誓,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一个都别想好过。"
窗外,第一缕晨光刺破黑暗。
手术时间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