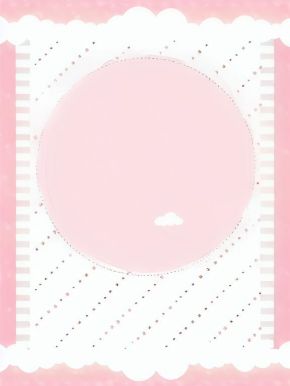
第一章雨落江南,茶肆初逢暮春的江南总裹着一层湿软的雾。
沈清辞提着裙摆踏过青石板时,檐角的雨珠正顺着黛瓦滚落,砸在她素色的裙裾上,
晕开一小片浅痕。她今日是替父亲去西街的“翰墨斋”取新印的诗集,没料想行至巷口时,
雨势忽然大了起来,豆大的雨点儿砸在油纸伞面上,发出“噼啪”的轻响。
巷尾那间“晚来居”茶肆的幌子在雨雾中晃荡,朱红的木牌被雨水浸得发亮。
沈清辞犹豫了片刻,终究还是收了伞,推门走了进去。茶肆里暖融融的,
空气中飘着龙井的清香与炭火的暖意,三三两两的茶客散坐在桌前,低声谈笑着,
偶尔有瓷杯碰撞的脆响,混着窗外的雨声,倒显出几分安逸来。她找了个临窗的角落坐下,
刚要唤小二来一壶热茶,目光却忽然被斜对面的身影勾住了。那是个身着月白长衫的少年,
正伏案坐在一张靠窗的八仙桌前,手边摊着一卷泛黄的《昭明文选》,一支狼毫笔握在指间,
笔尖悬在宣纸上,似是在斟酌字句。他的头发用一根素色的玉簪束着,几缕碎发垂在额前,
被茶肆里的暖光染成了浅金色。许是抄书久了,他微微侧着头,指尖沾着一点墨痕,
正无意识地在桌沿轻轻蹭着。沈清辞看得有些出神。她自小在江南长大,
见惯了温文尔雅的书生,却从未见过这般干净的少年——不是刻意修饰的整洁,
而是从眉眼到气质的澄澈,像是雨后初晴时,天边那抹最淡的云。正看得出神,
那少年似是察觉到了她的目光,忽然抬起头来。四目相对的瞬间,沈清辞猛地回过神,
脸颊瞬间烧了起来,慌忙低下头,假装去整理袖角。
她能感觉到那道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片刻,没有探究,倒带着几分温和的疑惑。
待她再悄悄抬眼时,少年已经重新低下头,只是握笔的手顿了顿,笔尖落在宣纸上,
晕开一个小小的墨点。“姑娘,您要的雨前龙井。”小二端着茶盏过来,打断了她的思绪。
青瓷茶杯里的茶汤碧清,浮着几片嫩绿的茶叶,热气袅袅升起,模糊了窗外的雨景。
沈清辞端起茶杯,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才觉得心跳慢了些。她偷偷抬眼,
又望向那少年——他还在抄书,字迹清隽有力,落在宣纸上,像极了巷口那株刚抽芽的柳丝,
柔韧又舒展。她忽然想起父亲常说的“字如其人”,想来这少年的品性,也该如他的字一般,
干净又正直。不知过了多久,窗外的雨渐渐小了。沈清辞看了看天色,想起父亲还在等诗集,
便起身准备离开。她走到茶肆门口时,又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那少年刚好写完一页,
正抬手揉着眉心,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脸上,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她轻轻推开门,
雨丝落在脸上,带着微凉的湿意。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什么,又折了回去,
从袖中取出一方绣着兰草的素色锦帕,走到少年桌前,轻轻放在桌角。“公子,
方才见您指尖沾了墨,”她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这帕子您先用着吧。
”少年抬起头,眼中带着几分惊讶,随即温声道了谢。沈清辞没敢再多看,
转身快步走了出去,油纸伞再次撑起时,她似乎还能感觉到,身后那道温和的目光,
正落在她的背影上。回到家时,父亲沈砚之正坐在书房里翻书。见她回来,
便放下书卷问:“怎么去了这么久?可是遇着雨了?”“嗯,在巷口的茶肆避了会儿雨。
”沈清辞将诗集递过去,指尖还残留着锦帕的触感,“爹,我今日在茶肆里,
见着一个抄书的少年,字写得极好。”沈砚之笑了笑,
接过诗集翻了两页:“江南多有才之士,若是有缘,往后或许还能再见。”沈清辞没再说话,
只是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渐渐放晴的天。檐角的雨珠还在滴落,她忽然想起少年指尖的墨痕,
还有他抬头时,眸子里盛着的、比春日阳光还要暖的光。她想,或许真的会再见。
第二章兰草为契,心事暗生自那日茶肆避雨之后,沈清辞便常常绕路去“晚来居”。
有时是午后,有时是傍晚,她总坐在上次那个临窗的角落,点一壶雨前龙井,
看少年伏案抄书。少年似乎也认出了她,每次她来,都会抬头温温地笑一下,
然后继续埋首于书卷。偶尔茶肆里人少,他会起身给她添茶,
两人也会聊上几句——大多是关于诗词,他说起《昭明文选》里的句子,
她便接上周邦彦的词,一来二去,倒也熟络了些。沈清辞渐渐知道,少年名叫陆景行,
字兰舟,是邻县来的书生,因家中贫寒,便在茶肆里抄书谋生,顺便备考秋闱。
“兰舟”二字,让她想起自己绣帕上的兰草,心中竟悄悄生出几分欢喜来——仿佛那方锦帕,
本就是为他绣的。陆景行也知道了她的名字,知道她是前御史沈砚之的女儿。
他说起第一次见她时,总说:“那日姑娘站在茶肆门口,伞沿沾着雨珠,
倒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沈清辞听了,脸颊又会发烫,只能低头搅着茶杯里的茶叶,
小声说:“陆公子取笑我了。”日子久了,两人之间渐渐有了默契。沈清辞再来茶肆时,
陆景行总会提前给她留好临窗的位置,
桌上放着一壶刚泡好的雨前龙井——他知道她只爱这一种茶。而沈清辞,
也会悄悄带些自己做的点心,比如桂花糕、绿豆酥,放在他的书旁,待他抄书累了,
便能随手拿起吃。有时陆景行抄书到深夜,茶肆老板要打烊了,他便会提着一盏青竹灯离开。
那盏灯是他自己做的,竹架纤细,灯罩是素色的棉纸,点燃后,暖黄的光透过棉纸映出来,
在青石板上投下晃动的光影。沈清辞见过一次,是在一个月色微凉的夜晚,
她送父亲的老友出门,恰好撞见陆景行提着灯从茶肆出来。“沈姑娘?”陆景行看见她,
停下脚步,“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头?”“送一位长辈。”沈清辞望着他手中的青竹灯,
“这灯是公子自己做的吗?”“嗯,夜里抄书费眼,便做了这盏灯,提着回家也方便。
”陆景行笑了笑,将灯举到她面前,“姑娘若是不嫌弃,下次夜里来茶肆,我也给你留一盏。
”沈清辞点点头,心中像被暖灯照过一般,软软的。她看着陆景行提着灯走远,
青竹灯的光在巷口转弯处消失,才转身回家。那一夜,她躺在床上,
眼前总晃着那盏暖黄的灯,还有陆景行温和的笑容。入夏之后,江南的雨少了些,
多了几分燥热。沈清辞依旧常去茶肆,只是不再只坐着看陆景行抄书,
有时会帮他整理抄好的书页,有时会和他一起讨论试题。陆景行的才华让她佩服,
他对经史子集的见解独到,说起治国之道时,眼中会闪着光,不像个贫寒书生,
倒像个胸有丘壑的谋士。“我若能中举,便去京城考进士,”一次聊到未来,
陆景行望着窗外的柳树,轻声说,“我想查清一件旧事,也想为百姓做些实事。
”沈清辞知道他说的“旧事”,是指他父亲的冤案。陆景行曾跟她说过,
他父亲原是沈砚之的下属,十年前因“贪墨”罪名被处死,可他始终不信,
觉得父亲是被人陷害的。沈清辞听了,心中一动——父亲当年被贬,也是因为“包庇下属”,
想来两件事或许有关联。“陆公子,”她犹豫了片刻,还是开口道,“我父亲书房里,
或许有当年的旧案卷宗,若是你不介意,我可以帮你找找。”陆景行猛地转头看她,
眼中满是感激:“真的吗?沈姑娘,若是能找到线索,我……”“你不用谢我,
”沈清辞打断他,声音轻轻的,“我也想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从那以后,
沈清辞便常常在父亲的书房里翻找旧案卷宗。沈砚之见她对这些旧事感兴趣,也不阻拦,
只是偶尔会提醒她:“有些事,知道了未必是好事,你要想清楚。”沈清辞点点头,
却没有停下。她知道,这不仅是为了父亲,也是为了陆景行——她想帮他完成心愿,
想看到他眼中的光,能一直亮下去。七夕那天,茶肆里挂了不少彩灯。陆景行提前收了工,
从袖中取出一枚素银书签,递给沈清辞:“今日七夕,没什么好送你的,这枚书签,
你留着玩吧。”书签上刻着几株兰草,和沈清辞绣帕上的一模一样。沈清辞接过,
指尖触到冰凉的银面,心中却暖得发烫。她抬头看向陆景行,他的脸颊在彩灯的光线下,
泛着淡淡的红晕,眼神温柔得像江南的水。“陆公子,”她轻声说,“明年七夕,
我们还在这里看灯,好不好?”陆景行点点头,声音有些沙哑:“好。”那天晚上,
陆景行提着青竹灯送沈清辞回家。两人并肩走在青石板上,灯影晃动,映着彼此的身影。
走到沈家门口时,沈清辞转身,从袖中取出一方新绣的锦帕,帕子上绣着一盏青竹灯,
递给陆景行:“这个给你,夜里抄书,别太累了。”陆景行接过,紧紧握在手中,
像是握住了什么珍宝。他望着沈清辞,想说些什么,最终却只说了一句:“清辞,
你早些休息。”沈清辞点点头,看着他提着青竹灯走远,才推门进屋。她靠在门上,
手心里还握着那枚素银书签,嘴角忍不住上扬——她知道,她的心事,
已经悄悄落在了那盏青竹灯里,落在了那方绣着兰草的锦帕上,再也收不回来了。
第三章风云突变,渡口离殇秋闱的日子渐渐近了,陆景行抄书的时间少了,
大多时候都在茶肆里埋头备考。沈清辞依旧常去,只是不再帮他整理书页,
而是默默坐在一旁,陪着他看书。有时陆景行看得累了,抬头看见她,
便会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然后继续低头复习。沈砚之看着女儿每日早出晚归,
心中虽有担忧,却也明白她的心意。他曾找陆景行谈过一次,在书房里,两人聊了很久。
沈清辞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只知道父亲回来后,对陆景行的态度好了许多,
有时还会让她带些经书给陆景行。“景行这孩子,是个可塑之才,”一次晚饭后,
沈砚之对沈清辞说,“只是他身世坎坷,往后的路,怕是不好走。”“爹,我不怕,
”沈清辞轻声说,“我想陪着他。”沈砚之叹了口气,没再说话。他知道,女儿的心思,
已经定了。秋闱前一个月,陆景行忽然接到消息,
说京城的一位故友愿意资助他去京城考进士。这对他来说,
是天大的好事——秋闱只是第一步,他的目标,始终是京城的殿试。“清辞,我要去京城了,
”陆景行找到沈清辞时,眼中满是喜悦,“等我考完进士,就回来找你。”沈清辞点点头,
心中既为他高兴,又有些不舍:“那你什么时候走?”“三日后,破晓时分,在东渡口坐船。
”陆景行握住她的手,指尖有些凉,“清辞,我走之前,想跟你说一件事。
”沈清辞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她看着陆景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我知道,
我现在一无所有,”陆景行的声音很认真,“但我向你保证,等我在京城站稳脚跟,
就回来娶你。到时候,我会提着青竹灯,带你去看遍江南的风景。”沈清辞的眼眶瞬间红了,
她用力点点头,声音有些哽咽:“我等你。”那三天,沈清辞几乎天天都和陆景行在一起。
他们去了江南的很多地方,去了西湖边的断桥,去了灵隐寺的古刹,
去了巷口的那株老柳树下。陆景行给她讲京城的故事,讲他对未来的规划,
沈清辞则给他绣了一个荷包,里面装着几片晒干的兰草叶——那是他们初遇时,
茶肆窗外的兰草。临行前夜,陆景行在“晚来居”留了一封信,
交给茶肆老板:“若是沈姑娘来,麻烦您把这封信交给她。”他还留了一个泛黄的纸包,
里面是那枚素银书签,还有一张短笺。他知道沈清辞会去渡口送他,可他还是怕,
怕自己走得太急,来不及跟她道别。沈清辞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她刚准备回房,
就听见前厅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她走过去,看见几个身穿官服的人站在客厅里,
父亲沈砚之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沈大人,奉刑部之命,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为首的官差面无表情地说,“十年前的贪墨案,有了新的线索,需要您配合调查。
”沈清辞的心猛地一沉,她冲过去,拉住官差的手:“你们凭什么抓我爹?
当年的案子早就结了!”“姑娘,休得放肆!”官差甩开她的手,“这是朝廷的命令,
谁敢阻拦,以同罪论处!”沈砚之站起身,拍了拍沈清辞的肩膀:“清辞,别担心,
爹去去就回。你在家好好待着,别出去惹事。”母亲王氏早已哭成了泪人,
她拉住沈砚之的衣袖,却被官差拉开。沈清辞看着父亲被官差带走,心中又急又怕,
她想跟出去,却被母亲死死拉住。“清辞,你不能去!”王氏哭着说,
“他们就是想抓我们沈家的人,你出去了,只会连累你自己!
”“可是爹他……”沈清辞挣扎着,“陆公子明天就要走了,我要去送他!”“什么陆公子!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他!”王氏的声音陡然提高,“你爹要是出了事,我们沈家就完了!
我不能让你再出任何差错!”王氏说完,就叫丫鬟把沈清辞锁进了房间。沈清辞拍着房门,
大声喊着“放我出去”,可回应她的,只有母亲的哭声,和门外丫鬟的劝说。夜深了,
沈清辞靠在门上,眼泪无声地滑落。她想起陆景行在渡口等她的样子,
想起他说的“等我回来娶你”,想起那盏暖黄的青竹灯。她知道,陆景行一定在渡口等着她,
可她却被困在房间里,什么也做不了。天快亮的时候,沈清辞终于找到了机会。
她用发簪撬开了门锁,悄悄溜出房间,直奔东渡口。一路上,她跑得飞快,裙摆被露水打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