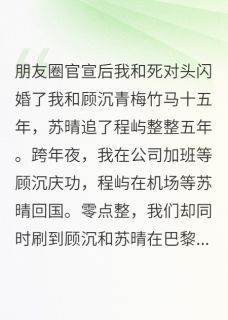
朋友圈官宣后我和死对头闪婚了我和顾沉青梅竹马十五年,苏晴追了程屿整整五年。跨年夜,
我在公司加班等顾沉庆功,程屿在机场等苏晴回国。零点整,
我们却同时刷到顾沉和苏晴在巴黎铁塔下的官宣朋友圈。“合作愉快?”我拨通程屿的电话。
“正有此意。”电话那头的声音冷静得可怕。我们火速领证,联手狙击顾沉公司的核心项目。
庆功宴上,顾沉红着眼把我按在洗手间:“你故意气我是不是?
”程屿一拳砸在他脸上:“顾总,请离我太太远点。”---手机屏幕幽幽的光映在脸上,
像一层冰冷的霜。窗外北城的冬夜,雪粒子敲打着巨大的落地玻璃,沙沙作响,
是这座城市跨年夜的背景音。我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
目光从电脑屏幕上堆积如山的项目文件移开,落在桌角那两张被捏得有些发皱的机票上。
巴黎。三天后。顾沉答应我的。十五年了。从弄堂里拖着鼻涕虫打架的小屁孩,
到如今顾氏集团呼风唤雨的少东,我的目光似乎从未真正从他身上移开过。
这趟迟来的“庆功旅行”,是我为拿下宏远科技那个地狱级难度的项目后,向他索要的奖赏。
他说:“薇薇,等我开完这个会,零点,天台餐厅,给你庆功。
”指针缓缓滑向十一点五十分。胃里隐隐传来熟悉的绞痛,提醒着我又一次错过了晚饭。
我关掉最后一个文档,拿起手机,指尖悬停在顾沉的号码上方。犹豫片刻,还是没拨出去。
算了,再等等。他总是很忙。指尖无意识地在屏幕上滑动,刷新着朋友圈。
——璀璨的烟花、喧闹的派对、紧紧相拥的情侣……世界的热闹仿佛都浓缩在这方寸屏幕里,
唯独没有属于我的那一点。就在指针即将跳过十一点五十九分的瞬间,一条新的动态,
像淬了毒的冰锥,毫无预兆地扎进了我的视线。发布者:顾沉。配图:巴黎埃菲尔铁塔,
在无数跨年灯光的簇拥下,宛如一座燃烧的金色巨塔。塔下,顾沉微微侧头,
嘴角噙着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宠溺的笑意。他身边,
依偎着一个穿着白色羊绒大衣、笑容明媚灿烂的女人——苏晴。
顾沉的文案简洁得刺眼:「新岁,新程。@苏晴」几乎在同一秒,
下方紧跟着刷出了苏晴的动态。同样的铁塔夜景,同样的两人合照。
她的配文透着毫不掩饰的甜蜜:「跨越山海,终抵星辰。余生,请顾先生多多指教。@顾沉」
轰——!世界的声音瞬间被抽空,只剩下血液在耳膜里疯狂鼓噪的嗡鸣。
胃部的绞痛猛地加剧,尖锐地顶上来,喉咙口泛起浓重的铁锈味。我死死攥着手机,
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冰冷的金属外壳硌得掌心生疼。屏幕上那两张幸福洋溢的笑脸,
被指尖的颤抖晃得有些模糊。巴黎铁塔……金色的光……他说要开完会给我庆功。他说零点,
天台餐厅。原来,他的庆功宴,在巴黎,主角是苏晴。那个追了程屿五年,
追得整个圈子人尽皆知、轰轰烈烈的苏晴。那个总是用湿漉漉的眼神望着程屿,说“程屿哥,
除了你,我谁都不要”的苏晴。他们是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
是在我为了宏远项目熬通宵改方案的深夜?还是在我顶着高烧飞往南城谈判的航班上?
抑或是……更早?那些被顾沉以“忙”为借口推掉的约会,那些他心不在焉的敷衍时刻,
原来都填满了另一个女人的身影?苏晴……她不是口口声声爱程屿爱得要死要活吗?荒谬。
恶心。像吞了一只活苍蝇,黏腻冰冷的窒息感从胃里一路蔓延到心脏,四肢百骸都冻僵了。
我猛地推开椅子站起来,动作太大带倒了桌上的水杯。“哐当”一声脆响,玻璃碎裂,
水渍混合着胃里翻涌上来的酸水,狼狈地洇开在昂贵的地毯上。窗外,
北城新年的第一波盛大烟花骤然升空,炸裂,将整个夜空映照得如同白昼,
流光溢彩地泼洒在办公室冰冷的玻璃幕墙上。绚烂的光影在我苍白的脸上明明灭灭,
衬得我像个格格不入的孤魂野鬼。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喜庆轰鸣声中,手机突兀地震动起来。
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程屿。那个被苏晴高调追了五年、此刻头顶绿得发光的男人。
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撞击着肋骨,一下,又一下。一种近乎毁灭的冲动攫住了我。
我盯着那个名字,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最终,在一片冰冷的麻木中,划开了接听键。
“喂。”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带着连自己都陌生的平静。电话那头没有立刻回应。
背景音是机场特有的、空旷而带着回音的广播声,隐约还有飞机引擎的轰鸣。
一种巨大的、死寂般的沉默顺着电波蔓延过来,沉重地压在耳膜上。
过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程屿的声音才传来。那声音低沉、平直,听不出任何情绪的起伏,
像深冬结冰的湖面,冷硬得吓人。“看到了?”他只问了三个字。“嗯。”我喉咙发紧,
一个字都像是挤出来的。又是一阵沉默。机场的广播似乎报了一个航班号,飞往巴黎的。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依旧冰冷得像淬火的金属,
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破釜沉舟般的确定:“林薇。”“嗯?”“合作吗?
”他的问题简短、直接,像一把出鞘的刀,寒光凛冽,“联手,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
付出点像样的代价。”窗外的烟花还在不知疲倦地绽放,将整个城市映照得如同虚幻的童话。
胃部的绞痛奇迹般地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尖锐、更冰冷的东西,
在胸腔深处疯狂滋长、蔓延。我看着地毯上那摊狼藉的水渍和玻璃碎片,
映着窗外变幻的光影,像一幅扭曲的抽象画。手机贴在耳边,
程屿那边机场的嘈杂背景音仿佛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噪音。“合作愉快?
”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稳,甚至带上了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冰凉的锐气。电话那头,
程屿似乎极轻地嗤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没有温度,只有一片荒芜。“正有此意。”他回答,
斩钉截铁。---三天后,北城民政局。冬日的阳光带着一种虚假的暖意,
透过高大的玻璃门照进来,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冷清的影子。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纸张油墨混合的、特有的官方气味。我和程屿分别从不同的方向走来。
他穿着一身剪裁精良的深灰色羊绒大衣,身形挺拔,脸上没什么表情,只下颌线绷得有些紧。
我则是一身利落的黑色西装套裙,外面裹着同色系的大衣,长发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
脸色有些苍白,但妆容精致,口红选了最提气场的正红。
我们像两个即将奔赴重要商务谈判的对手,在民政局门口狭路相逢。
视线在空中短暂地碰撞了一下,彼此眼中都只有一片沉寂的冰湖,映不出半点波澜。
没有寒暄,没有多余的眼神交流。他侧身,替我拉开了沉重的玻璃门。
一股更强的暖气混合着更浓郁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流程走得异常高效。填表,拍照。
摄影师机械地指挥着:“靠近一点,先生头往女士这边偏一点…好,笑一下。
”我和程屿的嘴角同时扯动,试图弯出一个弧度。闪光灯“咔嚓”亮起的瞬间,
我从对面光洁的墙壁反光里,看到了我们两人的样子——靠得足够近,
笑容却僵硬得如同橱窗里的塑料模特,眼底深处是如出一辙的冰冷和空洞。那不像结婚照,
倒像两张拼凑在一起的通缉令合影。钢印落下,发出沉闷而具有仪式感的“咔哒”声。
两本簇新的、印着国徽的红色小册子被工作人员推了过来。“恭喜二位。
”工作人员公式化地微笑。“谢谢。”程屿的声音低沉,率先拿起属于他的那本,
看也没看就塞进了大衣内袋。我也拿起我的。硬质的封皮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带着新纸张特有的、略显刺鼻的气味。这抹红色,此刻显得如此刺眼和不真实。
走出民政局的大门,冷风立刻卷走了室内那点虚假的暖意,吹得人脸颊生疼。
阳光依旧明晃晃的,却毫无温度。程屿在台阶下站定,转过身。他比我高很多,
投下的影子将我完全笼罩。“林薇,”他开口,声音在寒风里显得异常清晰,“契约生效。
”我抬眼看他。他的目光锐利,像手术刀,精准地剖开我们之间那层心照不宣的伪装,
直抵冰冷的现实核心。“目标明确:狙击顾沉手上那个新能源电池项目,
那是顾氏未来五年的核心增长点,也是他立足董事会的根本。”他语速平稳,条理清晰,
如同在部署一场商业战役,“他在巴黎的‘新程’,得用点真金白银来奠基。苏晴,
”他顿了一下,这个名字从他口中吐出,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冰冷的嘲讽,
“她父亲苏明远的远航资本,是顾沉这个项目最大的潜在投资人。
”寒风卷起地上枯黄的落叶,打着旋儿掠过我们脚边。程屿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敲在冰冷的空气里,也敲在我同样冰冷的心上。“所以,我们要做的,”我接上他的话,
声音同样没有起伏,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是让远航资本对顾沉失去信心,
让他的项目胎死腹中,同时……”我微微眯起眼,迎着刺目的阳光,
“让苏晴引以为傲的‘星辰’,变成一场代价高昂的笑话。
”程屿的唇角极细微地向上牵动了一下,那不是一个笑容,更像是对猎物踏入陷阱的确认。
“没错。我这边有顾沉技术团队核心人员的一些‘动向’,
还有他们提交给投资方那份过于乐观的可行性报告里,几个关键数据的‘水分’。
”他从大衣内袋里拿出一个薄薄的、没有任何标识的银色U盘,递了过来。
“这里面是初步资料。你负责远航资本那条线,苏明远对你印象一直不错,
他信任你的专业判断。”我接过U盘,冰冷的金属外壳瞬间汲取了指尖的温度。沉甸甸的,
仿佛承载着足以摧毁一段过往的重量。“好。”我将U盘紧紧攥在手心,
坚硬的棱角硌着掌心,“远航资本下周有个非公开的行业趋势研讨会,苏明远亲自主持。
我会拿到邀请函,并确保他看到该看的东西。”程屿点了点头,目光扫过我身后空旷的街道。
“住处?”“我公寓。”我下意识地回答,随即补充,“客房空着。”“嗯。”他应了一声,
没有多余的话,“地址发我。晚上见。”说完,他转身,大步走向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宾利,
背影挺拔而决绝,很快融入了车流。我独自站在民政局门口冰冷的台阶上,
手里捏着那本滚烫的红色证书和冰冷的U盘。阳光刺眼,寒风如刀。周围是匆匆而过的行人,
脸上带着新年的憧憬或生活的疲惫。没有人知道,就在刚刚,两个心死如灰的人,
签订了一份以婚姻为名的复仇契约。一场没有硝烟,却注定你死我活的战争,
正式拉开了帷幕。---位于CBD核心区的“云端”顶层公寓,
270度的落地窗将北城璀璨的夜景尽收眼底。灯火如织,车流如河,
勾勒出这座冰冷都市繁华的脉络。然而这繁华,此刻却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透不进一丝暖意。公寓里静得可怕,只有中央空调系统发出低微的、恒定的嗡鸣。
我和程屿各自占据着巨大客厅的一角,如同两颗隔着遥远星系的星球,
被无形的引力强行拉拽到同一片空间,却散发着截然相反的冰冷磁场。
他坐在宽大的黑色真皮沙发里,面前摊开着一台超薄笔记本电脑,
屏幕的冷光映着他轮廓分明的侧脸,神情专注而冷峻,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
发出清脆而规律的声响。我则盘腿坐在落地窗边的白色羊毛地毯上,后背靠着冰冷的玻璃。
膝盖上放着我的笔记本,
屏幕上是远航资本和苏明远个人近几年的所有公开及非公开的投资报告、访谈记录。
旁边散落着几份打印出来的文件,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密密麻麻地做着标记和分析。
手边放着一杯早已冷透的黑咖啡。空气凝固,只有敲击键盘和翻动纸张的声音交替响起,
像某种古怪而压抑的协奏曲。
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由文件、数据和各自翻涌的恨意构筑的墙。
直到墙上的复古挂钟沉闷地敲响十一下。程屿合上笔记本,揉了揉眉心,
动作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抬眼,目光扫过我手边冷掉的咖啡杯和地上散乱的文件。
“咖啡?”他的声音打破了长久的寂静,低沉,没什么情绪,像在问一件公事。
我正埋首于一份苏明远三年前关于新能源投资风向的讲话稿,
试图从中找出他偏好的蛛丝马迹,闻声头也没抬:“不用,谢谢。”他站起身,
走向开放式厨房。很快,咖啡机运作的嗡鸣声和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片刻后,
他端着两杯热气腾腾的黑咖啡走了过来。一杯放在我手边的矮几上。“提神。”他言简意赅,
自己则端着另一杯,靠在旁边巨大的承重柱上,目光投向窗外无边无际的灯火,沉默地喝着。
深褐色的液体在白色的骨瓷杯里冒着袅袅热气。浓郁的香气钻入鼻腔,
带着一种令人清醒的苦涩。我敲击键盘的手指停顿了一下,最终还是端起杯子,抿了一口。
滚烫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短暂的暖意,随即是更深的苦涩在舌根蔓延开。“苏明远这人,
”我放下杯子,目光依旧停留在屏幕上,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有些突兀,“极其自负,
又极度迷信所谓的‘技术壁垒’。他投项目,技术领先性是第一要素,
其次才是市场前景和团队。”程屿的目光从窗外收回,落在我身上,
带着审视的意味:“顾沉这次押注的固态电池技术,宣称能量密度提升40%,
成本下降30%,专利壁垒坚固。苏明远很吃这套。”“所以,我们要让他看到,
这壁垒是纸糊的。”我调出U盘里的一个文件夹,将屏幕微微转向他的方向。
上面是几份技术文档的扫描件和一份内部邮件截图。“顾沉的技术总监张维,
上个月私下接触过‘星海科技’的人。星海是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邮件里,
量产时间表用了‘mission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词。
还有这份报告,”我点开另一份文件,“他们实验室最新一轮的循环测试数据,
衰减率远高于他们提交给投资方报告里的数字。”程屿走近几步,俯身看着屏幕上的内容。
他身上清冽的雪松混着淡淡烟草的气息瞬间压过了咖啡的苦涩,笼罩下来。距离很近,
我甚至能看清他浓密睫毛在冷光下投下的一小片阴影。“张维……”他低声念着这个名字,
眼神锐利如鹰隼,“顾沉给他的期权承诺,似乎因为项目延期,兑现遥遥无期了。人心浮动。
”他直起身,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这份内部报告和邮件,出现在苏明远的案头,
会很有趣。”“不止。”我关掉文件夹,调出远航资本内部一份非公开的评估报告截图,
“苏明远最忌讳的,是技术路径被打败。顾沉押注的是硫化物固态电解质路线。而据我所知,
”我抬眼,迎上程屿的目光,“你投资的‘启源科技’,在氧化物路线上,
上个月刚取得突破性进展,循环寿命和倍率性能都远超预期?”程屿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
随即化为更深沉的锐利:“消息很灵通。启源的技术简报,下周一会正式发布。
”“时间刚好。”我端起冷掉的咖啡又喝了一口,苦涩在口腔里蔓延,
却带来一种近乎病态的清醒,“远航资本的闭门研讨会,就在下周二。
苏明远会先看到顾沉团队的‘水分’,再听到启源突破的消息。雪上加霜。
”我们隔着冰冷的空气对视着。彼此眼中都没有笑意,
只有冰冷的算计和一种奇异的、建立在共同毁灭目标之上的默契。
复仇的蓝图在冰冷的咖啡香和满屏的数据中,逐渐变得清晰而锋利。
“需要一份‘恰到好处’的匿名包裹,送到苏明远的私人助理手里。
”程屿的声音低沉而确定,“研讨会前一天。”“我来安排。”我点头。匿名信,匿名邮件,
这些灰色的手段,在资本圈心照不宣。为了达到目的,有些规则可以暂时搁置。计划初定,
那股支撑着我的、紧绷的神经似乎稍稍松弛了一瞬。随之而来的,
是更深重的疲惫和一种无所适从的空虚。巨大的落地窗外,城市的灯火依旧璀璨,
却照不进这间冰冷的、名为“家”的公寓。程屿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突如其来的沉寂。
他拿起空掉的咖啡杯,走向厨房水槽。水流声哗哗响起。我抱着膝盖,下巴抵在膝头,
目光无意识地落在散落在地上的文件上。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滑落出来,
是苏晴去年生日派对上的抓拍。她穿着粉色的公主裙,笑容灿烂地依偎在顾沉身边,
顾沉的手亲昵地搭在她肩上。照片右下角,
还有顾沉龙飞凤舞的签名:“ToMySunshine”。胃里那熟悉的绞痛感,
毫无预兆地再次翻涌上来。比跨年夜那天更猛烈,带着一种钝刀子割肉的、迟来的痛楚。
十五年的点点滴滴,那些隐秘的期待,小心翼翼的靠近,
无数个为他拼搏的理由……在这一刻,被这张照片彻底碾碎成齑粉。我猛地捂住嘴,
压抑住喉间翻涌的恶心感,身体不受控制地蜷缩起来。水流声停了。程屿转过身,
手里拿着擦干的杯子。他看到我蜷缩在地毯上微微发抖的样子,脚步顿了一下。“怎么了?
”他的声音依旧没什么温度,但似乎少了几分之前的冷硬。“没事。”我咬着牙,
从齿缝里挤出两个字,试图撑起身体,却因为胃部的剧烈痉挛而再次弯下腰,
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脚步声靠近。阴影笼罩下来。一杯温水被递到眼前。
握着杯子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喝了。”是命令式的口吻,
不容置疑。我抬起冷汗涔涔的脸,视线有些模糊。程屿就站在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眉头微蹙。他没有弯腰,也没有伸手扶我的意思,只是那么站着,手里稳稳地端着那杯水,
像在完成一项必要的程序。胃部的绞痛和心口翻腾的屈辱感交织在一起。我猛地挥手,
想要打掉那杯水。“用不着你假好心!”啪!杯子被我挥开,脱手飞出,
砸在光滑的实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碎裂声!温水和玻璃碎片瞬间溅开,
有几片甚至弹到了我的脚踝,带来冰凉的刺痛。空气瞬间凝固。
程屿的手还维持着递出水杯的姿势,悬在半空。他低头看着地上狼藉的碎片和水渍,
又缓缓抬起眼,目光落在我因疼痛和愤怒而显得苍白的脸上。那眼神深不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