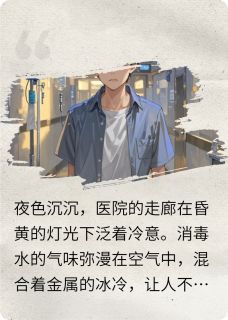
第一卷:暗涌与冰裂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窗外飘进来的、闷热八月傍晚的潮气,
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粘稠。林然的手指在冰冷的门框上蜷了又松,掌心汗涔涔的。
姐姐林雪就躺在那门后的病床上,白色的床单盖在她身上,衬得她脸色更加苍白。
这间单人病房,此刻像一座孤岛,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只剩下他与她之间,
那根早已绷紧到极限的弦。门缝里透出病房内惨白的光,
也隐约传来心电监护仪规律而单调的“滴滴”声,那是林雪生命尚存的证明,
也是此刻压在他心头最沉重的负担。他不清楚自己为何又站到这里,
是因为父亲在电话里疲惫苍老的声音?“你姐……情况不太好,你有空的话来……”,
还是因为昨晚那个光怪陆离的噩梦里,他拼命奔跑,
身后却总是姐姐那双冷静又带着审视的眼睛?他甩甩头,仿佛要把这些杂念驱散。他知道,
一旦踏进这个房间,就意味着再次踏入那条看不见的河,河水冰冷刺骨,名为“控制”。
他终是推开了门。门轴发出细微的**,惊动了床上的人。
林雪的目光如同探照灯般扫了过来,尽管她刚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手术,虚弱地半倚在床头,
可那眼神里的锐利和习惯性的审视丝毫未减。嘴角,惯常地勾起了一丝微妙的弧度,
像是嘲讽,又像是等待猎物走进陷阱时的从容。“来了?”声音带着手术后的沙哑,
却依旧清晰地划破病房的静谧。这三个字,像一把无形的钥匙,
轻易就打开了林然心底那个名为“服从”的盒子。
过往的无数画面蜂拥而至:母亲去世后厨房里摔碎的碗(那次他只是想学着帮忙),
中学那次关键的月考(他考砸了,而她在客厅的灯光下用红笔批改他的试卷直到深夜),
大学专业的选择(他想学美术,她却拿着精算师的就业报告单给他看)……每一次,
她都这样,用一句不轻不重的话,就把他钉在原地,动弹不得。林然喉咙发紧,
干巴巴地回答:“嗯,爸让我来看看你。”他刻意提到父亲,像是为自己找到一个正当理由,
以此掩饰内心的动摇和那份该死的、根深蒂固的服从欲。
他在床边一张硬邦邦的塑料椅上坐下,眼神落在窗台上那株蔫头耷脑的绿萝上,
不敢与姐姐对视。窗外的天空阴沉沉的,浓云压得很低,预示着一场酝酿已久的暴风雨。
“他忙他的就好。”林雪淡淡地应着,目光却落在林然略显拘束的坐姿上,“你自己呢?
最近工作怎么样?听说……你换部门了?”她的语速不快,每一个字却都像经过精确计算。
果然来了。林然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她消息灵通。
上个月他刚从销售部换到了市场部创意小组,虽然薪水没变,
但更接近他喜欢的文案策划工作。他知道姐姐对“创意”这种东西向来嗤之以鼻,
认为是不务正业,远不如销售的数字来得实在和安全。他低下头,
看着自己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膝盖,声音低低的:“嗯,刚调过去一阵,还在适应。
”他感觉到林雪的目光像针一样刺在他身上。“从销售岗去搞什么创意?销售做得好好的,
稳定,能见收益,晋升空间也清晰。创意……”林雪轻轻哼了一声,
像是在谈论一个过于天真幼稚的游戏,“那是些什么飘在云端的东西?现在大环境这么差,
你倒有心思去追求这些不切实际?你知不知道,隔壁床张姨的儿子,就因为公司架构调整,
他们整个创意部门都……唉。”她没有继续说下去,但那声叹息,
连同她话语里那种不容置喙的判断,已经在林然的心底投下巨大的阴影。稳定,安全,
看得见的收益……这是林雪信奉的铁律,也是她为他规划的人生模板中的核心词汇。
任何偏离这个模板的行为,在她看来都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
甚至是对她“保护”的一种背叛。林然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收紧,指甲陷入布料。
那股熟悉的无形压力再次攥紧他的心脏,让他几乎喘不上气。他想争辩,想说他做得并不差,
市场部的反馈也还可以,甚至他的方案还被总监在会上表扬过……但话到嘴边,
迎着姐姐那双仿佛洞悉一切、带着“为你好”旗帜的眼睛,
他所有为自己辩解的词句都变得苍白无力。他只能再次沉默,把头垂得更低。
病房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寂静,只剩下仪器的“滴滴”声,以及窗外更显压抑的雷声,
闷闷地在远方滚动。雨,似乎快要来了。第二卷:风暴降临不知沉默了多久,
也许只有几分钟,也许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林然觉得必须做点什么,
打破这快要将他溺毙的僵局。他站起身,拿起床头的保温壶,
声音依然有些僵硬:“我……我去给你打点热水。”就在他转身的刹那,
林雪的声音再次响起,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然然,辞职吧。”这四个字,
仿佛平地一声炸雷,瞬间劈开了林然所有摇摇欲坠的心理防线。他猛地转身,
保温壶差点脱手:“什么?!”林雪的神情没有丝毫波动,目光直视着他,
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理所当然:“销售部那边,李经理前两天来探病,聊起你现在的情况。
我知道你这孩子,从小就心软,不会拒绝人。创意组那边,我知道不是你想去,
肯定是部门变动把你硬塞过去的,或者……被他们画的什么大饼给骗了。你不适合那个,
太虚浮。我已经和李经理说好,他那里还缺个人手,你回去,他会照顾你。
这个月底前就去办手续。”“轰隆!”窗外一声炸雷猛地劈开了天空的云层,
刺目的闪电瞬间照亮了病房内煞白的墙壁和两张同样惨白的脸。紧接着,瓢泼大雨倾盆而下,
重重地砸在玻璃窗上。林然的心脏,也随着那雷声猛烈地撞击着胸腔。辞职?回去?照顾我?
一股难以言喻的冰冷和滚烫的感觉同时在他体内炸开。他明白了。他全明白了。
李经理所谓的“好心探望”,根本是受了她林雪的“委托”!她不仅知道他换了岗位,
更是在他背后,轻描淡写地为他安排了“回归”的路线,甚至帮他找好了“下家”,
还贴心地用了“照顾”这个充满施舍意味的词。这感觉比当众被人扇了一耳光更甚!
是一种被连根拔起、连选择权都被剥夺的彻骨侮辱!“你调查我?!
”林然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和震惊而颤抖着,眼睛死死盯着病床上的姐姐,
“你有什么权利替我做主?有什么权利背着我安排我的工作?!
”林雪似乎没料到他会反应如此激烈,眉头微微蹙起,
但语气依旧保持着她一贯的冷静克制:“调查?你是我弟弟,我问问你的情况怎么了?
这叫关心!林然,你现在怎么变得像吃了火药桶?你冷静点!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你现在在那个不靠谱的创意组能有什么出路?李经理那里是稳定的核心部门……”“为我好?
!为了我好?!”林然几乎是咆哮出声,压抑了二十几年的委屈、愤怒、屈辱、不甘,
在这一刻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冲垮了他所有的理智堤坝。
保温壶“哐当”一声砸在地上,滚烫的开水溅出来,烫伤了他的脚踝,他却浑然不觉。
他指着林雪,手抖得厉害,“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问过我真正想干什么?!母亲在的时候,
她说我是多余的!你呢?你扮演着好女儿、好姐姐的角色,你买书给我,生病照顾我,
可我每次稍微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每次试图走一条你觉得不正确的路,你就会像今天这样!
用你的‘为我好’来绑架我!用你的‘关心’来控制我!林雪,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我的姐姐,还是套在我脖子上的枷锁?!”他的声音撕裂着,带着哭腔,眼眶通红,
却倔强地一滴泪都没有掉下来。窗外暴雨如注,雷声滚滚,
像是给这场酝酿了半生的家庭战争配上了最激烈的交响。雨水疯狂冲刷着玻璃窗,
病房内的光线也因此明灭不定,映照着两张同样因激动而变形的脸。
林雪的脸色从未有过的难看,嘴唇也失去血色。
她大概从未想过那个在她面前一向隐忍、沉默、甚至有些唯唯诺诺的弟弟,
会爆发出如此巨大而尖锐的反抗。她挣扎着想坐直身体,
胸口因为激动和术后的虚弱而起伏不定:“枷锁?林然,你说我是枷锁?!没有我林雪,
你能平安长大?!母亲走得那么早,父亲天天忙得不着家,是谁给你做的饭?
是谁给你洗的衣服?是谁给你开家长会?是谁在你被人欺负时替你出头?!是我!都是我!
你那个什么可笑的梦想,什么创意?它能养活你自己吗?
它能让你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站稳脚跟吗?你忘了你刚毕业那会儿,
找不到工作天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样子了吗?是谁托关系把你弄进的公司?!
你现在跟我说枷锁?!”她每一声质问都像是用尽了力气,声音也尖锐起来,
带着愤怒的颤抖。“对!就是你!”林然毫不退让,眼泪终于冲破了他强忍的倔强,
无声地滚落下来,砸在地面那滩浑浊的水渍里。他哽咽着,
声音却带着一种绝望的清晰:“那些照顾,那些帮助,我谢谢你!可我更恨你!
你一边照顾我,一边用这种照顾提醒我,我是个没用的人!是个废物!
是个离不开你的寄生虫!你把我的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可你有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要这些?
!我宁愿我从来没吃过你做的饭!宁愿我自己去挨揍!宁愿我自己像条狗一样在街上找工作!
至少那样我知道我自己爬起来了!我知道我是靠自己活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活在你的施舍里,活在你的阴影下!林雪,我不是你用来满足你控制欲的玩偶!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最后几个字,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嗓子已经沙哑变形。
着病床上脸色煞白、胸口剧烈起伏、眼神里除了愤怒还混杂着惊愕、失望和深深受伤的姐姐,
一股巨大的悲怆和无力感像冰冷的潮水将他彻底淹没。他忽然失去了所有力气,踉跄着后退,
靠在了冰冷的墙壁上。暴雨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疯狂地捶打着世界。病房里死寂一片,
只剩下仪器“滴滴”的冷酷声响,像是为这场两败俱伤的对峙倒计时。
林然的眼泪无声地流着,林雪则紧咬着下唇,胸口急剧起伏,显然在竭力压制着翻腾的情绪。
她的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愤怒,有不甘,有被“忘恩负义”刺伤的痛楚,或许,
在最深最深的角落里,还有一丝微不可察的迷茫和恐慌。
第三卷:沉默的刀锋暴烈的争吵过后,是更深沉、更压抑的沉默。
这寂静比刚才的咆哮更令人窒息,充满了未爆弹的硝烟味和无言的痛苦。林然靠着冰冷的墙,
身体的颤抖还未完全平息。刚才那番宣泄几乎耗尽了他积攒了小半生的所有勇气。
他不敢抬头看林雪的表情,那沉默的注视比任何责骂都更让他心悸。
汗水混合着未干的泪痕粘在脸上,冰冷腻滑。他下意识地将手伸进裤兜,
那里装着一个小铁盒,
里面是他省吃俭用买的廉价烟草——那是他在无数个加班的深夜、在无数次被生活打击后,
独自在阳台上点燃的仅有的慰藉,是他的“不务正业”,
也是他与姐姐所期望的那个“优秀员工”形象之间,一道隐秘的反叛。他想抽一支,
哪怕一口,压下喉咙口翻涌的血腥味和心口那巨大的空洞感。但这是医院病房。
他摸到了烟盒冰冷的棱角,指尖在上面无意识地摩挲着,终究没有勇气拿出来。
他害怕看到林雪眼中更浓的失望和不屑。林雪那边则更静了。
她像一尊失去了所有生气的雕塑,只是靠在床头,眼睛看着窗外如注的暴雨。
雨水在玻璃上汇聚成股流下,不断冲刷变形的夜景映在她的瞳孔里,
却似乎没有倒映出任何东西。她放在白色被单上的手,手指微微蜷起,又松开,
像是在努力抓住什么,又徒劳地发现手心空空。那是一种深刻的疲惫。
她引以为傲的逻辑和规划,在那句“寄生虫”的控诉面前,似乎失去了所有的支点。
她想辩解,喉咙却像是堵着一团浸水的棉花,又冷又重,发不出任何声音。她能说什么?
说这一切的控制源于她对母亲早逝后家庭分崩离析的恐惧?
说她对林然那份近乎扭曲的执着保护,
其实是害怕自己守护了十几年的“完整的家”最终也化为泡影?不,她说不出口。
林然那带着血泪的指控,早已将她的逻辑堡垒冲击得摇摇欲坠,
只剩下内心深处那份难以启齿的恐慌在疯狂蔓延——如果他真的挣脱了,离开了,
她林雪守护的一切意义,是否将轰然倒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沉默像是实体一样在挤压着病房的空间。护士走进来换药,被这几乎凝固的气氛吓了一跳,
动作迅速而无声,换好药瓶,看了一眼监护仪上的数据(血压似乎有所升高,
心率也不太稳),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对峙般沉默的两人,最终还是什么也没问,
飞快地离开了。病房里再次只剩下他们两人,以及窗外永无止境般的雨声。
雨势似乎小了一些,不再是砸,而是倾泻。林雪的目光,缓缓地,艰难地,
从窗外移到了林然身上。她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声音发出。
她看着他靠着墙、仿佛耗尽了所有力气的样子,看着他低垂的头颅上凌乱的黑发,
看着他洗旧了的衣服……一些久远的片段,
不受控制地在脑海中闪现:片段一:那是母亲刚走不久后的冬天,特别冷。林然放学回来,
小脸冻得通红,校服外套敞开着。她刚加班回来,又冷又累,看到他这样,一股无名火起,
冲上去就骂:“跟你说多少次把扣子扣好!你想感冒死掉给家里添麻烦是不是?!
”林然吓得浑身一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小声辩解:“有……有同学把我的围巾抢走了……”她当时只觉得烦躁:“抢?
你不会抢回来吗?哭什么哭!没出息!”现在想起来,
那天他眼睛里的委屈和无助……片段二:林然高考结束拿到成绩单那天。
他分数过了重点线,但比她预估的少了二十几分。父亲难得在家,看到分数,
失望地叹了口气,转身进了书房。她把林然的志愿表拿过来,
看着他勾选的几所偏文的大学和专业,眉头皱得死紧。她把他拉到小书房,
把他辛苦搜集的那些艺术设计类院校和专业介绍资料扔进垃圾桶,
拿出厚厚一叠她早已准备好的金融、会计、管理类专业的名册。“别犯傻。
这些才是有前途的。你以为靠画画能吃饱饭?
”她记得当时他死死盯着垃圾桶里那些散落的彩页,眼神一点点暗下去,
最终只回了一个字:“……嗯。”片段三:林然刚进公司,在销售部实习,
天天被人呼来喝去,做各种杂活累活。他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小订单后的那个深夜,
他发微信给她,语气带着难得的兴奋:“姐!我今天自己签了一单!客户说下次还找我!
”她当时也在加班,看着电脑上复杂的财报,随手回了一句:“不错,继续努力。
别忘了把客户详细资料和跟进记录填好。”隔了一会儿,他回:“嗯。
”语气又淡了下去。她没在意。现在想来,
他那份小心翼翼想要分享的、也许只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和喜悦,在她眼里,
似乎从来都不值一提。一种迟来的、尖锐的、名为“愧疚”的东西,夹杂在愤怒和恐慌之中,
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刺穿了林雪冰封般坚硬的心脏,带来陌生又剧烈的疼痛。
她的手指猛地攥紧了被单,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林然似乎感受到了她的注视,终于抬起头。
他的眼睛依旧红肿,但情绪似乎在刚才的爆发后沉淀了下去,
变成一种更深沉、更决绝的东西。他不再有歇斯底里的愤怒,眼神平静得可怕。
他用袖子胡乱地擦了擦脸,站直身体,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我走了。你……好好养病。
”他没有说“再见”,也没有说“下次再来看你”。这四个字,像是最后的告别词。
他弯腰捡起地上已经变形的保温壶盖子(壶体早已在刚才的混乱中摔裂,
热水浸湿了一小块地面),将它放在了旁边的床头柜上。然后他转身,不再看她一眼,
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病房外昏暗的走廊,身影迅速被走廊的阴影吞噬。
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林雪僵硬地坐在病床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扇紧闭的门。林然离开时最后那平静得可怕的眼神,像一把冰冷的匕首,
在她心头最脆弱的地方狠狠剜了一下。刚才翻涌的心绪瞬间被极度的恐慌席卷。她不能!
她不能失去林然!没有她控制着的林然,那还是林然吗?没有围绕着她旋转的弟弟,
她林雪的存在价值又还剩什么?她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家,
母亲去世后她就发誓要守住的家,难道就要这样崩塌?!不!不行!极度的恐惧压倒了一切,
甚至暂时压过了刚刚涌起的愧疚。她用颤抖的手摸索着按响呼叫铃,
尖锐急促的**在寂静中突兀响起。护士很快推门进来:“林女士,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林雪指着门的方向,声音因为急切而尖利:“小张护士!快!快去看看我弟弟林然!
他刚跑出去了!情绪很不好!快把他叫回来!快点!”她语无伦次,
眼神里充满了失去控制的惊惶,“外面……外面那么大的雨!他淋了雨会病的!
快点把他找回来!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姐姐错了?告诉他别走?
她卡壳了,巨大的恐惧让她无法思考,只能重复着:“把他找回来!快点!
”那份对失去控制的恐慌,此刻压倒性地战胜了她所有其他的情绪。
小张护士被她激动的样子吓到了,连忙点头:“好好,您别急!我马上去!
”说完迅速追了出去。房间里再次陷入死寂,只剩下林雪自己因为激动而沉重的喘息声。
她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身体微微颤抖。窗外的雨声再次清晰起来,像是在呜咽,
又像是在无情地嘲笑着病房内这片无声的战场。她刚才那失态的呼叫,
像一记耳光抽回了她试图反思的念头——不,她没做错!她只是……太害怕失去了!
他只是闹小孩子脾气!他不能走!林然……必须回来!她的世界,
不能没有这个她一直牢牢攥在手心的弟弟。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她的心脏,越收越紧。
那份刚刚萌芽的、对林然独立人格的痛苦领悟,
被她更强烈的控制欲牢牢地压制在了心底深处,再次冻结成冰。
她此刻只有一个念头:找回他。第四卷:雨夜中的寻找与内心的挣扎护士小张跑出病房,
只看到走廊尽头电梯门恰好合上,楼层指示灯显示下行。她快步追到电梯口,
但显然赶不及了。她立刻转向楼内消防通道的楼梯口,往下追了几层,又匆匆跑出大楼侧门。
住院部大楼外,暴雨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豆大的雨点被狂风撕扯着,
砸在沥青路面、花坛的绿叶上以及屋檐下避雨的人们身上,奏响一片嘈杂狂乱的乐章。
地面腾起一层迷蒙的水雾,路灯的光线被折射得模糊不清,只能照亮一小圈湿漉漉的地面。
车灯的光柱在雨幕中艰难地切割着视线,喇叭声也变得沉闷遥远。
整个世界仿佛都沉浸在冰冷的水牢里。小张站在急诊大厅的门口檐下,焦急地在雨中搜寻。
大雨模糊了一切。
她看到一个穿着和印象中林然相似颜色衣服的瘦高身影正快步走向远处公交车站的方向,
伞都没打,身影在雨中显得格外单薄模糊。她下意识地喊了一声:“林先生!等等!
”但她的声音瞬间被雨声淹没。那人没有半点停顿,径直消失在站点的雨棚和人流车流里。
小张犹豫了一下,没有冲进那么大的雨里去追一个可能认错的人——她穿着单薄的护士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