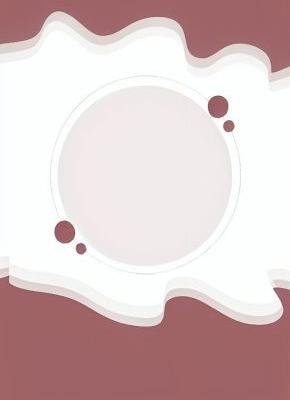
岑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停尸间的。
她回到家,把自己扔进浴缸,用最烫的热水反复冲刷自己的身体,尤其是那只触碰过尸体的手。皮肤被烫得通红,她却感觉不到疼,那股阴冷的、死寂的触感,仿佛已经刻进了骨头里。
一千字的体验报告。
她坐在书桌前,对着空白的文档,脑子里却一遍遍回放着停尸间里的画面。裴烬冰冷的声音,那具尸体刺骨的寒意,还有他握住她手腕时,那截然相反的、灼人的温度。
她写不出来。她只能写下“恐惧”两个字,然后就再也无法继续。
第二天,她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去了剧组。
裴烬已经在专属的休息室里等着她了。他正在看一份文件,似乎是医学期刊,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和复杂的人体解剖图。
“报告。”他头也没抬。
岑鸢把只写了两个字的A4纸递过去,声音干涩:“我……写不出来。”
裴烬终于抬起头,视线从那张几乎空白的纸,移到她的脸上。
“黑眼圈,眼球有红血丝,嘴唇干裂起皮。”他冷静地分析,“昨晚的睡眠时间应该少于三小时。有噩梦?”
岑鸢一惊,他怎么知道?
“人在极度恐惧后,大脑皮层会持续处于兴奋状态,导致入睡困难和梦魇。这是正常的应激反应。”他把那张纸推了回来,“把你昨晚梦到的东西写下来,这也是报告的一部分。”
岑鸢咬着下唇,没动。
“怎么,需要我帮你回忆?”裴烬的眼神微微一变,带上了一丝危险的意味。
“我梦到你了。”岑鸢几乎是脱口而出,带着一丝豁出去的决绝。
裴烬的动作停顿了一瞬。
“继续。”
“我梦到……你拿着手术刀,站在我的床边,”岑鸢的声音在发抖,却强迫自己说下去,“你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然后,你开始……解剖我。从脚开始,一点一点,把我的皮肤剥下来……”
她每说一个字,裴烬的眼神就深邃一分。他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只是专注地听着,像一个在聆听病人陈述病情的医生。
“你一边剥,一边给我讲解,这是胫骨前肌,这是腓肠肌……你告诉我,我的肌肉纤维很漂亮,很适合做成标本。”
说完,岑鸢自己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裴烬却只是平静地问:“然后呢?”
“然后……我就吓醒了。”
“很好。”裴-烬点点头,似乎很满意,“恐惧让你的潜意识开始工作了。把这些,详细地写进你的报告里。今天下班前交给我。”
他低下头,继续看他的期刊,仿佛刚才那段恐怖的梦境描述,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
岑鸢感觉自己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她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反抗,来控诉他的变态,结果却正中他的下怀。
接下来的几天,裴烬的“指导”变本加厉。
他会突然出现在拍摄现场,用各种方式中断她的表演。
当她要演出被饥饿折磨的虚弱时,他会让人在她面前摆满美食,然后冷冷地看着她,命令她不准动。
当她要演出对黑暗的恐惧时,他会把她关进一个完全密闭的道具箱里,然后在外面不紧不慢地敲击箱子,模仿心脏跳动的声音,一声,又一声,直到她崩溃尖叫。
剧组的人都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她。他们佩服她的敬业,也私下议论裴顾问的手段太过“硬核”。只有导演李诚,每天看着监视器里岑鸢那“真实到令人发指”的表演,笑得合不拢嘴。
岑鸢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她开始分不清现实和戏剧。有时候,她看到穿着白衬衫的裴烬,会下意识地想要逃跑。她甚至开始失眠,掉发,体重直线下降。
经纪人赵姐来看她,心疼得直掉眼泪。
“鸢鸢,我们不拍了行不行?再这样下去,电影拍完,你人也毁了!”
岑鸢摇摇头。她不能不拍。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这已经变成了她和裴烬之间的一场角力。她想证明,她可以演好这个角色,而不是被他当成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实验品。
这天,要拍一场女主角试图逃跑,被抓回来后,与变态医生对峙的戏。
开拍前,裴烬把岑鸢叫到一边。
“今天的戏,重点是眼神。”他说。
“我知道,要演出绝望中的反抗。”岑-鸢有气无力地回答,这些天她已经被折磨得麻木了。
“不。”裴烬否定了她,“我要的不是反抗。我要你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找到地狱。”
岑鸢愣住了。
“什么意思?”
“你的角色,在无数次的折磨后,已经意识到,她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施虐者。他的眼睛里,藏着比囚禁和痛苦更深的东西。那是一个已经坍塌的世界,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地狱。”裴烬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找到它。”
“Action!”
岑鸢被粗暴地推倒在地,裴烬扮演的医生角色,缓缓走到她面前。
摄影机给了裴烬一个脸部特写。
岑鸢抬起头,被迫迎上他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