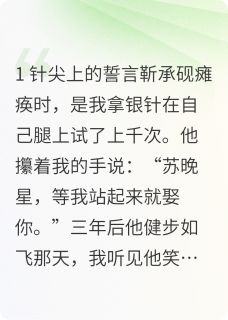
1针尖上的誓言靳承砚瘫痪时,是我拿银针在自己腿上试了上千次。
他攥着我的手说:“苏晚星,等我站起来就娶你。”三年后他健步如飞那天,
我听见他笑着对白月光解释:“残废时的承诺,怎么能当真?”我转身拨通家族电话:“爸,
苏氏财团的继承权,我要了。”后来拍卖会上,他红着眼问我针灸留下的疤疼不疼。
新任未婚夫挡在我身前轻笑:“靳总记性真差,你扔掉的星星——现在是我的太阳了。
”碎裂声在死寂的房间里炸开,像一块冰狠狠砸进凝固的沥青里。
一份边缘卷曲的康复评估报告被狠狠掼在冰冷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
白纸黑字瞬间被泼洒的深褐色药汁浸染、污浊。刺鼻的苦味混合着绝望的气息,
沉甸甸地弥漫开。“滚!都给我滚出去!
”嘶哑的咆哮从房间中央那张宽大的定制病床上爆发出来,
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的困兽般的狂躁。靳承砚额角青筋暴起,
那双曾经锐利如鹰隼、轻易就能搅动商场风云的眼睛,
此刻只剩下狂怒的赤红和深不见底的灰败。
他像一头被锁链禁锢了太久、终于彻底失控的凶兽,胸膛剧烈起伏,
每一次呼吸都扯动着盖在腿上的薄毯,那下面,
是医生们口中“不可能再站起来的”沉重废墟。昂贵的紫檀木床头柜被他一掌扫落在地,
上面价值不菲的骨瓷茶杯应声粉碎,碎片混合着残余的药液,在地板上溅开一片狼藉。
他砸了所有能够到的东西,手臂因为过度用力而颤抖,
每一次挥动都耗尽了他刚刚积聚起的一点点力气。最后,他颓然倒回堆叠的枕头里,
粗重地喘息,胸口剧烈起伏,汗水浸湿了额发,黏在苍白的皮肤上。
房间里只剩下他破碎的、带着血腥味的喘息,以及一地昂贵的狼藉。
厚重的丝绒窗帘被拉开了一条缝隙,惨淡的冬日光线斜斜地刺进来,
恰好落在他紧握成拳、指节发白的手上,
也照亮了床边散落一地的、来自不同权威医院却结论惊人的报告书——每一份,
都像一道冰冷的判决,彻底封死了他脚下的路。门被小心翼翼地推开一道缝,
发出细微的吱呀声。苏晚星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细瓷碗,脚步放得极轻,
像怕惊扰了什么脆弱的幻影。她瘦了很多,曾经带着点婴儿肥的脸颊微微凹陷下去,
衬得那双总是含着温润水光的眼睛更大,此刻盛满了浓得化不开的疲惫和忧虑。
她穿着一件素净的米白色羊绒衫,柔软的质地却掩不住肩背挺直时透出的那股无声的倔强。
看到满地的狼藉和床上那个被暴怒和绝望抽空了所有生气的男人,苏晚星的眼神猛地一痛,
像是被无形的针狠狠扎了一下。但她没有惊呼,甚至没有立刻说话。
她只是安静地绕过地上的碎片和污渍,如同绕过一片无声的雷区,走到床边。“承砚,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平静,像羽毛拂过紧绷的弦,“先把药喝了,好吗?
今天的方子,李老稍微调整了一下。”她把碗递过去,碗沿温热。靳承砚猛地扭过头,
猩红的眼睛死死盯住她,那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只有冰冷的、带着毁灭欲的火焰。“喝?
”他嗤笑一声,声音像砂纸摩擦着粗糙的木头,“喝了它,我的腿就能动了?苏晚星,
收起你这套假惺惺!你们都一样,除了这些没用的苦水,还能给我什么?同情?
还是看一个废物的笑话?”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锥,狠狠扎进苏晚星心里。
端着碗的手指用力到骨节泛白,滚烫的药汁隔着薄薄的瓷壁灼烧着她的指尖,
却远不及他话语带来的寒意刺骨。她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喉咙口的哽咽和眼底汹涌的酸涩。
“不是同情,”她迎着他暴戾的目光,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持,
“是相信。靳承砚,我相信你能好起来。医生的话,不是最终裁决。”“相信?
”靳承砚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猛地撑起上半身,动作牵动了麻木的下肢,
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让他本就难看的脸色更加扭曲,“你拿什么相信?拿这些骗鬼的汤药?
还是拿你那些可笑的、翻烂了的医书?!”他喘着粗气,眼神疯狂地扫视着她,
最终定格在她眼底那抹固执的光上,那光芒像针一样刺着他,他猛地挥手——“啪!
”苏晚星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狠狠撞在手腕上,剧痛传来,她下意识地松开手。
那只精致的细瓷碗在空中划出一道刺眼的弧线,重重摔在冰冷的地板上,瞬间四分五裂。
滚烫的、深褐色的药汁泼溅开来,如同肮脏的血,沾染了她素净的裤脚和光洁的地板,
也彻底浇熄了她眼底最后一丝微弱的、强撑着的希望火苗。碎片和药汁溅开,
有几滴滚烫的液体溅到了苏晚星**的脚踝上,瞬间红了一片。她站在那里,一动未动,
垂着眼睑,看着脚下那片狼藉的深褐色和自己的裤脚,还有脚踝上那点迅速蔓延开的灼痛。
房间里死一般寂静,只剩下靳承砚粗重而压抑的喘息声。过了很久,
久到地上的药汁都开始变冷、凝固,苏晚星才慢慢蹲下身。她没有去管脚踝的烫伤,
只是伸出微微颤抖的手,小心地、一片一片地,拾起那些锋利的碎瓷片。
指尖被锋利的边缘划破,渗出细小的血珠,混在冰冷的药汁里,颜色变得模糊。她一言不发,
默默地清理着这片由他亲手制造的废墟,动作缓慢而专注,仿佛在进行某种无声的仪式。
靳承砚靠在床头,胸膛依旧剧烈起伏,但赤红的眼底,
那疯狂毁灭的火焰似乎被那片沉默的、固执清理的身影浇熄了一角,
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冰冷的灰烬,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连他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狼狈。
碎瓷片冰冷的触感和指尖被划破的细微刺痛,像一根根细小的针,
不断刺入苏晚星紧绷的神经。她将最后一片染着深褐色药渍的碎片放入托盘,站起身,
没有看床上那个如同风暴过境后废墟般的男人,也没有处理脚踝上那片灼热的红痕。
她端着盛满碎片的托盘,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棵被风雪压弯却不肯折断的细竹,
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这间弥漫着绝望和药味、令人窒息的房间。轻轻带上沉重的房门,
隔绝了里面压抑的气息。苏晚星靠在冰凉的门板上,长长地、无声地吸了一口气,
仿佛要把肺里淤积的浊气全部置换掉。走廊尽头高大的落地窗外,是冬日午后惨淡的天光,
无力地洒在光洁的地板上。她端着托盘,
走向自己的房间——那个位于主卧斜对面、原本用作客卧、如今成了她全部世界的狭窄空间。
推开房门,一股混合着淡淡艾草和药草的特殊气息扑面而来,冲淡了鼻腔里残留的苦涩药味。
房间里光线充足,却显得异常拥挤。一张单人床靠在墙边,上面铺着素净的格子床单。
占据房间大部分空间的,是一张宽大的、略显陈旧的实木书桌,
以及旁边一个几乎顶到天花板的沉重书柜。书柜里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空隙。
最显眼的是几排厚厚的硬壳精装书,
尔骨科》、《实用神经病学》、《脊髓损伤康复医学进展》……这些专业书籍像沉默的士兵,
昭示着主人涉足的艰深领域。旁边则是成排的中医典籍,
《黄帝内经》、《针灸大成》、《本草纲目》……书页边缘磨损得厉害,
泛着被无数次翻阅后的毛边。更引人注目的是书桌和旁边矮柜上堆叠如山的笔记本,
不同颜色,密密麻麻写满了娟秀又略显急促的字迹,
夹杂着各种穴位图、药方配伍、人体经络走向的简图。房间的另一角,
则是一个小小的“医疗角”。一个便携式的消毒锅嗡嗡低鸣着,
旁边散落着几盒一次性针灸针。
一盏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立在一个略显简陋的、覆盖着白色棉布的**床旁边。**床的一头,
固定着一个木制的人体腿部模型,上面用红蓝两色清晰地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穴位名称,
环跳、风市、阳陵泉、足三里、悬钟……每一个名字,
都连接着床榻上那个男人毫无知觉的下肢。苏晚星将托盘轻轻放在书桌一角,
目光扫过那个腿部模型,最终落在自己光洁的小腿上。她沉默地走到**床边坐下,
卷起宽松的裤腿,露出匀称白皙的小腿。灯光下,那原本光洁的皮肤上,
却布满了新旧交叠的痕迹:一片片或深或浅的淤青,
像散落的不规则地图;一些细小的、已经结痂的暗红色针孔,
密密麻麻地点缀在几个关键的穴位周围,如同星辰的印记;还有几处微微凸起的硬结,
那是反复**留下的痕迹。她伸出手指,指尖带着薄茧,
轻轻按压在小腿外侧的“风市”穴上。那里有一片新鲜的、硬币大小的青紫,
是昨晚练习时失手扎深了留下的。一阵尖锐的酸痛立刻从按压点蔓延开,
让她不由自主地蹙紧了眉头。她没停,手指继续向下,滑过“阳陵泉”,
那里的皮肤颜色明显更深,反复施针的痕迹清晰可见。再往下,是“悬钟”穴,
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刚刚结痂的针眼,周围还带着一圈淡淡的红晕。每一次按压,
都带来清晰的痛感,像无数根细小的针在皮肉下搅动。苏晚星紧咬着下唇,
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身体因为疼痛而微微颤抖。但她没有停下,只是闭上眼睛,
强忍着那深入骨髓的酸胀和刺痛,努力地感知、记忆着。指尖下的触感,肌肉的细微反应,
神经的传导方向……这些细微的、常人难以察觉的感受,
是她从那些艰深晦涩的典籍和无数次在自己身体上的“实验”中,
一点一滴摸索、积累起来的“语言”。她必须懂。只有她懂了,
才能试着去叩响靳承砚那双被宣判了“死刑”的腿。汗水顺着鬓角滑落,
滴在**床白色的棉布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苏晚星睁开眼,眼神疲惫却异常清亮。
她拿起放在旁边矮柜上的一本摊开的厚笔记本,翻开最新的一页。
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
施针穴位组合、艾灸时间、靳承砚当天的细微反应(哪怕只是肌肉的一次极其微弱的跳动),
以及她自己在相应穴位上施针后的详细感受和推测。她拿起笔,沾了沾墨,
手腕悬在纸页上方,微微颤抖。笔尖落下,写下今天的日期,然后顿了顿。
墨迹在纸上晕开一小点。她写:“风市,酸胀感明显,针感可向下传导至足背外侧。阳陵泉,
针下触及腓骨,需更谨慎入针角度。悬钟,针感强烈,
疑与深部神经有关……”她的字迹依旧娟秀,却带着一种疲惫的沉重。写完最后一笔,
她放下笔,目光落在旁边矮柜上。那里放着一个打开的针灸包,
一排排闪亮的银针整齐地插在蓝色的消毒衬布上,针尖闪着寒光。她伸出手,
指尖拂过那些冰冷的针具,最终抽出一根细长的毫针。她的动作很稳,
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她再次看向自己的小腿,
目光锁定在“环跳”穴的位置——那是臀部外侧一个深层的穴位,对下肢痿痹至关重要,
也是风险极高的一个穴位,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及坐骨神经。靳承砚的康复,
这个穴位是关键中的关键。苏晚星曾无数次在模型上练习,却始终不敢轻易在他身上尝试,
因为风险太大。她需要更精准的把握。需要知道针尖刺入多深,会触碰到什么,
会带来什么样的感觉,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应。而这些,只能在她自己身上试。她深吸一口气,
用酒精棉球仔细擦拭着穴位周围的皮肤,冰凉的触感让她微微一颤。然后,
她捏起那根细长的银针,屏住呼吸,眼神锐利如手术刀。针尖抵住皮肤,
微微用力——刺痛传来。她稳稳地捻动着针柄,感受着针尖刺破表皮,穿过脂肪层,
一点点深入肌肉。一种酸、麻、胀混合的奇异感觉,沿着腿部神经的走向,
开始缓慢地向下扩散,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她全神贯注,
感受着针下的每一分微妙变化,调整着角度和深度,额头上再次沁出细密的汗珠。
就在针尖似乎触及某个敏感的筋膜层时,
一阵尖锐的、如同电流窜过般的剧痛猛地从“环跳”穴炸开!那痛感来得极其突然猛烈,
瞬间冲垮了她的防线,沿着大腿后侧一路向下,狠狠抽击在膝盖窝!“唔!
”一声压抑不住的痛哼从苏晚星紧咬的牙关中溢出。她整个身体猛地一弓,
像一只被突然烫熟的虾米,捏着针柄的手指因为剧痛和用力而指节惨白,剧烈地颤抖着。
眼前瞬间发黑,金星乱冒,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的衣衫。剧痛持续了足足十几秒,
才像退潮般缓缓减弱,留下绵长而深刻的酸胀和麻木感。苏晚星瘫软在**床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色苍白如纸,汗水顺着额发和下颌线不断滴落。她缓了好一会儿,
才颤抖着手,小心翼翼地将那根深入穴位的银针慢慢捻转着退了出来。
针尖带出一星点几乎看不见的血珠。她看着那点血珠,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依旧在微微抽搐的小腿,眼中没有委屈,
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专注和一丝……了然的明悟。她挣扎着坐起身,
再次拿过那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手指依旧有些发抖,却异常坚定地落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