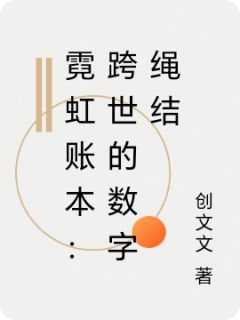
第一章:五块钱的民国旧账
江城六月的雨,总来得没头没脑。
林夏站在“诚信会计事务所”的玻璃门后,看着豆大的雨点砸在柏油路上,溅起一片模糊的白。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房东发来的催租信息:“小林,这个月房租该交了,记得转我卡上。”
她深吸一口气,把刚打印好的报表塞进帆布包。报表右上角印着“林夏实习生”,字迹鲜红,像根细针,扎得她眼睛发酸。
“林夏!”
办公室里传来老板张姐的声音,带着惯有的不耐烦。林夏攥紧包带,转身走进去。
张姐的办公桌永远堆着半人高的文件,她叼着笔,指着桌上的报表:“你这报表怎么回事?净利润算对了,但‘管理费用’里这笔‘员工福利费’,你就写个数字?谁的福利费?为什么发?发了之后员工反馈怎么样?你全没写!”
林夏低头看报表,那行“员工福利费:8620元”的数字确实孤零零的,像个被遗弃的标点。“张姐,我以为……会计只要算对数字就行。”
“算对数字就行?”张姐把报表摔在桌上,咖啡杯里的液体晃出来,在纸上洇出个褐色的圈,“你以为我让你天天对着Excel是干嘛的?数字是死的,但账是活的!你记的不是数字,是人过日子的痕迹!前儿楼下包子铺老王来对账,他账本上写‘给隔壁李奶奶送了两笼菜包,她孙子住院’,这才叫账!你这报表,干得像块晒了三天的馒头!”
林夏咬着唇没说话。她知道张姐说得对。她在事务所实习三个月,算错过三次小数点,被骂过五次“不敏感”,每次都想辩解——她不是不敏感,是真的不懂“账里的人”。她爸妈是数学老师,从小教她“数字要准”,却没教她“数字要暖”。
“明儿不用来上班了。”张姐突然说。
林夏猛地抬头:“张姐,我……”
“不是开除你。”张姐揉了揉太阳穴,从抽屉里拿出五十块钱,“给你放一天假,去旧货市场逛逛。找本老账本回来,不是超市小票那种,是以前账房先生记的,蓝布封皮,毛笔字的那种。看看人家怎么记的,悟不透就别回来。”
五十块钱被塞进手里,带着张姐手心的温度。林夏捏着钱,走出事务所时,雨小了些,风裹着潮湿的热气扑过来,她突然想起老家阁楼里,外婆的旧木箱里好像有本“老东西”,但她从没敢翻。
旧货市场在江城老城区,藏在两条窄巷中间。林夏挤过卖盗版书的摊位、摆着生锈铜锁的木桌,鼻尖萦绕着霉味、油条香和雨水打湿的泥土气。五十块钱攥在手心,被汗浸得发潮。
“姑娘,看看这个?”
一个叼着烟的老头冲她招手。他摊位前摆着个掉漆的木箱,里面堆着旧怀表、断弦的二胡,还有几本封面模糊的书。林夏蹲下来,指尖划过本《民国通俗小说选》,书页脆得像饼干。
“不是要书。”她小声说,“想要本老账本。”
“账本?”老头吐了个烟圈,弯腰从箱底翻出个蓝布包,“前儿收废品从拆迁的老楼里扒的,说是个账房先生的东西,纸都脆了,你要不?”
蓝布包被放在地上,裹着层灰。林夏伸手去解绳子,手指刚触到布料,就愣了——布是粗棉布,边缘磨得发白,正中央用褪色的毛笔写着“周记”两个字,笔锋瘦硬,像冬天冻硬的树枝。
她把布包拆开,里面是本账本。封皮内侧缝着块浅蓝补丁,针脚歪歪扭扭,像初学针线的人扎的;扉页印着个模糊的红章,油印晕开了,隐约能认出“江城·周记布庄”五个字。
“这是……民国的?”林夏指尖拂过红章,布料下的纸页硌着手心,带着种陈旧的扎实。
“谁知道呢。”老头踢了踢木箱,“收废品的说那老楼是民国时的布庄旧址,这账本估计是那时候的。五块钱,当给你练手了。”
林夏没还价。她从帆布包里摸出五块钱递过去,把账本小心地裹回蓝布,塞进包最底层。包里约着张姐给的五十块钱、刚打印的报表,还有早上没吃完的面包,旧账本的糙布蹭着塑料包装,竟有种奇怪的妥帖。
她没注意,翻账本时蹭掉的一点灰,落在了封皮的补丁上,像颗没来得及擦的星子。
从旧货市场出来,雨彻底停了。太阳把云晒得透亮,老巷的墙根下,几个老太太蹲在青石板上择菜,竹篮里的豆角绿得发亮。
“王婶,你家孙子今儿没过来?”
“去他姑家了,说要吃姑做的米糕。”
“还是你家孙子嘴甜,不像我家那个,给块糖都不说谢谢。”
林夏放慢脚步。老太太们的声音混着蝉鸣,飘进耳朵里时,她突然想起账本扉页的“周记布庄”——民国时的账房先生,会不会也这样听着街坊聊天,然后把“王婶的孙子吃米糕”记进账本?
她走到公交站,掏手机想查“周记布庄”,却发现信号只有一格。车来的时候,她把手机塞回包,指尖无意间碰了碰账本——蓝布补丁糙得硌手,像块没磨平的玉。
出租屋在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林夏爬得气喘吁吁,开门就把自己摔进沙发。沙发是房东留下的旧物,弹簧松垮,坐下去能陷出个坑。她把帆布包扔在茶几上,账本“啪”地掉出来,蓝布封皮在阳光下泛着浅白的光。
茶几上摆着早上吃剩的面包,干得掉渣。林夏起身去烧水壶,想泡杯速溶咖啡,目光却总往账本上飘。她蹲下来,指尖捏着封皮边缘翻开——
第一页是竖排的毛笔字,墨色褪得浅淡,却仍能看清笔画: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初三晴
收洋布五尺,价一元五角。赵老板说要添台缝纫机,让算工钱。晚归,巷口李婶送了碗南瓜粥,甜。”
林夏的心跳慢了半拍。
不是冰冷的“营收”“支出”,是“赵老板”“李婶”,是“南瓜粥甜”。她翻到下一页: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初四阴
进棉纱十斤,价三元。帮伙计小张垫药钱两角,他娘病了。布庄的灯坏了,摸黑记的账,字歪。”
“歪”字后面真的画了个小小的叉,像孩子做错事时的标记。林夏忍不住笑了——原来民国的账房先生也会怕写错字。
她一页页翻下去,指尖拂过“替张婶付豆腐钱一角”“给乞丐留两个馒头”“布庄的猫生了三只小猫,送了李婶一只”,这些琐碎的小事像颗颗珍珠,被“周记”两个字串成了串。
翻到“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那页时,林夏停住了。这页的字迹比前面的深些,像是写的时候用了力:
“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晴
收洋布三尺,价七角;米五斤,价一元二角。晚归,过巷口见李婶买豆腐,忘带钱,替付一角。夜凉,补账本时添了件单衣。”
“一角豆腐钱”。林夏想起张姐说的“包子铺老王的账”,突然有点发酸。她捏着这页纸,指尖无意识地蹭过“李婶”两个字,又碰了碰封皮的补丁——
就在这时,台灯“滋啦”响了声。
不是平时的电流声,是尖锐的、像电线短路的刺啦声。暖黄的灯光猛地变成刺目的红绿光,林夏眼前一黑,手里的账本掉在地上,她想去捡,却发现身体像被钉在了原地。
耳边传来嗡嗡声,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飞。她闻到一股陌生的味道——不是出租屋的霉味,是煤炉的烟味,混着油条香,还有种……潮湿的青石板味。
等她能睁开眼时,发现自己蹲在地上。
不是出租屋的瓷砖地,是带青苔的青石板,缝隙里还嵌着片干枯的槐树叶。她抬头,看见头顶挂着盏霓虹灯,红的“布”字、绿的“庄”字闪得人眼晕;远处传来“铛铛”声,一辆墨绿色电车晃过去,车头上钉着块木牌:“民国三十五年·江城第三路”。
林夏的呼吸顿住了。
她低头看自己——还是那件印着事务所LOGO的白T恤、牛仔裤,在灰扑扑的巷子里,像块走错片场的调色板。帆布包还在肩上,账本掉在脚边,蓝布封皮沾了点泥。
“姑娘,你蹲这儿干啥?”
一个穿粗布褂子的老太太走过来,挎着竹篮,篮里卧着块嫩白的豆腐。她打量林夏的裤子,眉头皱成团:“这衣裳怪模怪样的,是从南边来的?”
林夏张了张嘴,嗓子干得发紧:“我……我在找路。”
“找啥路?”老太太笑了,眼角堆起皱纹,“这是周记布庄后头的巷,就一条路。你要是迷路,先去我家坐坐——我家老头子是布庄的账房,认路。”
林夏浑浑噩噩地跟着走。老太太的竹篮蹭着她的胳膊,豆腐的凉气透过来,真实得可怕。她踢了踢脚边的石子,石子滚进石板缝,发出“嗒”的轻响——不是梦。
她真的……穿了。穿到了账本上写的“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
老太太的家在巷口第三间,院门是旧木门,上面钉着块褪色的木牌:“李”。推开院门,一股煤炉的热气扑过来——院子小得像个方盒子,正中央摆着煤炉,铝壶坐在上头,滋滋冒白汽;墙角堆着半人高的账本,全是蓝布封皮,跟她手里那本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老头子!来客了!”老太太朝屋里喊。
里屋走出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戴圆框眼镜,手里捏着支毛笔。他看见林夏,愣了下:“这位姑娘是?”
“迷路的,穿得怪,怕是外乡人。”老太太把豆腐放进碗柜,“你给指个路,我去热粥。”
男人点点头,让林夏坐板凳。板凳是竹编的,凉得硌**。“姑娘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
林夏攥着帆布包带,手心冒汗。她能说“我从2024年来”吗?他会不会把她当疯子?可看着男人手里的毛笔,看着墙角的账本,她又觉得不说不行——这一切都和那本账本有关。
“我……我从2024年来。”她闭着眼说,声音发颤。
男人笑了,以为她开玩笑:“2024?这年数倒新鲜。我是周记布庄的账房,姓周,你叫我周先生就好。”他指了指墙角的账本,“这些都是布庄的账,从民国二十六年记到现在——姑娘要是不嫌弃,先喝碗粥,等会儿我带你去巷口问问。”
林夏盯着他的手。那双手骨节分明,指尖沾着墨,捏着账本翻页时,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她突然想起自己那本账本扉页的“周记布庄”——难道……
她猛地掏出账本递过去:“周先生,您看这个。”
周先生接过来,指尖刚触到封皮,眼镜都差点滑下来。他翻到扉页,摸了摸模糊的红章,又捏起封皮的补丁,喉结动了动:“这是……我的账本。这补丁是内人去年缝的,她针脚笨,就这水平。”
林夏心“咚”地沉下去——真的是他的。
“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周先生翻到那页,突然抬头看林夏,“你说你从2024来?今日就是六月十二。”他指了指账本上“替李婶付一角豆腐钱”,“方才内人去买豆腐,回来还说‘忘带钱,亏得周账房路过’——我根本没出门。”
林夏懵了。难道账本上的“替付一角”,是她来之前发生的?还是……因为她碰了账本,才出了这岔子?
铝壶“呜”地响了,白汽漫出来,模糊了周先生的脸。林夏突然想起出租屋的台灯——她摔在地上的咖啡杯,是不是还在半空悬着?
“姑娘,你脸色怎么这么白?”周先生递过来杯白开水,“是不是吓着了?”
林夏接过水杯,指尖碰着杯壁的凉,突然想起张姐的话——“账是活的,记的是人过日子的痕迹”。她看着周先生手里的账本,看着院角的煤炉,看着墙上挂着的旧日历(上面印着“民国三十五年六月”),突然觉得,或许张姐让她来旧货市场,不是为了让她学记账,是为了让她来看“日子”。
“周先生,”林夏深吸一口气,“我没骗你。我真的从2024来。这本账本,是我在旧货市场买的,五块钱。”
周先生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盯着林夏的眼睛,看了很久,突然说:“你知道我内人叫什么吗?账本补丁是她缝的,除了我,没人知道她的名字。”
林夏的心提了起来。她哪知道?账本上根本没写!她张了张嘴,刚想说“不知道”,突然想起账本某页夹着的一张小纸条——那页记着“给阿芸买胭脂一盒,价三角”,纸条上画着朵小小的梅花。
“她……叫阿芸?”林夏试探着说。
周先生手里的水杯“啪”地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
他看着林夏,眼睛瞪得很大,嘴唇哆嗦着:“你……你怎么知道?”
林夏的后背沁出冷汗。她猜对了。但这猜对,让她更慌了——她不仅穿越了,还闯进了一个和她手里的账本死死绑在一起的人的生活里。
巷口传来“铛铛”的电车声,远处有人喊“卖豆腐嘞”,煤炉上的铝壶还在滋滋冒白汽。林夏看着地上的碎瓷片,突然明白:她不是来“看”日子的,她是掉进日子里了。
掉进了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掉进了周记布庄的账里,掉进了这个叫周明诚的账房先生的生活里。
而她手里的这本账本,或许不只是账本。
它是钥匙,是桥,是把她从2024的出租屋,拽进1946的青石板巷的,一根看不见的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