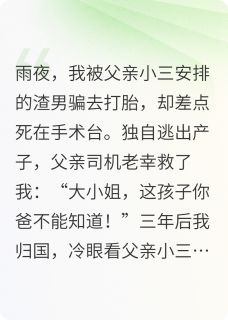
雨夜,我被父亲小三安排的渣男骗去打胎,却差点死在手术台。独自逃出产子,
父亲司机老幸救了我:“大**,这孩子你爸不能知道!”三年后我归国,
冷眼看父亲小三挺着新孕肚耀武扬威。我笑着递上亲子鉴定:“爸,您新宝贝的爹,
是……小三当场流产,父亲心脏病发。那人跪地求饶!看谁还敢说,假千金成不了真凤凰!
---冰冷的雨像钢针,扎透了我单薄的衬衫,黏在皮肉上。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
肚子一阵紧过一阵地抽,像有只手在里面拧我的肠子。我瘫在巷子深处湿漉漉的垃圾箱边,
连哭的力气都没了。血混着雨水,在脚下蜿蜒,刺目的红。那个金发碧眼的畜生,
我爸小三陈美琳“精心”安排给我的“完美男友”,下午还搂着我的腰,
甜言蜜语哄我躺上那家黑诊所的手术台。麻药刚推进去,
我就听见他和医生用蹩脚的英语讨价还价,内容不是手术费,是我的命!“……弄干净点,
别留尾巴,陈总说了,钱加倍。”我他妈当时就炸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一脚踹翻旁边的手术器械盘,趁着医生捂脸的功夫,
连滚带爬冲出了那间弥漫着消毒水和死亡味道的屋子。后面是那畜生气急败坏的吼叫和追赶。
拼了命地跑,肚子里的东西像铅块一样往下坠,撕裂的痛楚一阵猛过一阵。雨越下越大,
砸在脸上生疼,糊住眼睛。身后追赶的脚步声好像没了,也可能被雨声盖住了。
我实在撑不住了,一头栽进这条散发着馊味的死胡同。完了吗?我缩在冰冷的墙角,
牙齿磕得咯咯响,手指死死抠着湿透的牛仔裤口袋。里面硬邦邦的,
是临走前我妈偷偷塞给我的一个小金佛挂坠。妈……眼泪混着雨水流进嘴里,又咸又苦。爸?
呵,他这会儿大概正搂着陈美琳那**,摸着她的新肚子,畅想他的“美满家庭”呢!
哪会管我这个“不懂事”的“前妻”女儿的死活?剧痛猛地攫住我,
像一把烧红的铁钳在肚子里疯狂搅动。我眼前发黑,喉咙里发出野兽濒死般的嗬嗬声,
指甲抠进潮湿的砖缝,几乎要折断。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向下奔涌、撕裂……不知过了多久,
也许只是一瞬,也许是一万年。我脱力地靠在冰冷的墙上,浑身抖得像风里的破布。
身下一片狼藉的血泊里,一个沾着血污、小得可怜的东西在微弱地蠕动,
发出细得像猫叫的哭声。我的……孩子?我和那个渣男的……孽种?
恐惧和厌恶瞬间淹没了我。它不该活!它活着就是个定时炸弹!陈美琳会用它把我踩进泥里,
我爸会彻底厌弃我!我咬着牙,血从嘴角渗出来,颤抖的手伸过去,想……“大**!
”一个急促、压低的熟悉声音像惊雷一样在巷口炸响。我吓得一哆嗦,猛地缩回手,
心脏差点从喉咙里蹦出来。一道刺眼的车灯划破雨幕,晃得我睁不开眼。
高大的身影顶着雨冲进来,是家里的老司机,幸叔!他平时沉默得像块石头,只负责开车。
幸叔冲到跟前,看到我身下的血泊和那个蠕动的小东西,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
眼珠子瞪得溜圆,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一个字。他猛地脱下自己的旧外套,
动作快得像被火烧了**,胡乱地裹住那个还在微弱啼哭的小东西。“大**!
你…你糊涂啊!”他声音抖得厉害,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恐惧和焦灼,几乎是吼出来的,
又死死压着嗓子,“这孩子…这孩子的事儿,打死都不能让柳总知道!一个字都不能透!
听见没?!”他蹲下来,手忙脚乱地用外套把孩子裹得更严实,只露出一张皱巴巴的小脸。
雨水顺着他沟壑纵横的脸往下淌,分不清是雨还是汗,或者别的什么。他抬头看我,
眼神复杂得要命,有震惊,有恐惧,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狠劲儿。“陈美琳那毒妇,
她是要你的命啊!她说你是野种,假千金成不了真凤凰!
这事要是让她知道了…还有这孩子…”他喉结滚动,声音哑得厉害,“柳总那边…唉!
你信我,大**,这事儿必须捂死了!这孩子…不能留!”他最后几个字,
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冰冷的决绝。他猛地站起来,
抱着那团被旧外套裹紧的小东西,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沉重的石头砸在我心上。
“你撑住!我去…处理干净!”他撂下这句没头没尾的话,抱着那个裹着婴儿的包裹,
转身就冲进了瓢泼大雨里,身影很快被雨幕吞没。巷子里只剩下我,
躺在冰冷的血水和雨水里,像个被掏空的破布娃娃。幸叔那决绝的背影和那句“处理干净”,
像冰锥子扎进我脑子里。身体还在流血,心却像是被掏空了,
只剩下一个冰冷的、灌满仇恨的窟窿。
…我爸…幸叔…还有那个刚出生就被带走的、连脸都没看清的孽种……冰冷的雨水砸在脸上,
混着滚烫的恨意流进嘴里。………三年。足够让一个差点死在雨夜垃圾堆旁的女孩,
脱胎换骨,变成一把淬了剧毒的刀。海城国际机场的VIP通道,光可鉴人。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稳定,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节奏感。我摘下墨镜,
露出后面那双淬炼过的眼睛。冰冷,锐利,像打磨好的钻石,
映着机场顶棚巨大的玻璃天幕投下的阳光,却毫无暖意。“柳董已经在车里等您了。
”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笑容职业得有些僵硬的助理快步迎上来,微微躬身,态度恭敬,
眼神却忍不住飞快地在我脸上扫了一下,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我扯了扯嘴角,
算是个回应。三年了,我爸柳振山,终于“想起”他还有个在国外“深造”的女儿了?
我跟着助理走向那辆熟悉的黑色加长幻影。车门被恭敬地拉开。宽大的后座上,
我爸柳振山正襟危坐,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是那种惯常的、掌控一切的威严。他身边,
依偎着一个女人。陈美琳。她穿着剪裁完美的孕妇裙,
丝绸料子柔顺地包裹着明显隆起的腹部,脸上是精心描绘过的妆容,红唇饱满,
眉眼间那股得意劲儿几乎要溢出来。看到我,她立刻绽开一个甜得发腻的笑容,
一只手还下意识地、炫耀般地轻轻抚摸着那个圆滚滚的肚子。“哎呀,芽芽回来啦!
可算把你盼回来了!”她声音又娇又脆,带着刻意的亲热,“看看,瘦了!
在国外吃了不少苦吧?快让阿姨看看!”她作势要伸手拉我,动作间,
一股浓郁的、甜腻的香水味扑面而来。我侧身,避开了她的手。动作不大,但足够清晰。
空气瞬间凝固了一下。我爸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爸。”我看向柳振山,
声音平静无波,像在念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嗯,回来就好。”柳振山沉声开口,
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似乎想看出些什么,最终只是点点头,“先回家。
”陈美琳脸上的笑容僵了僵,随即又夸张地扬起,手更加用力地护住肚子,
像是在宣示**:“对对对,回家!你爸呀,天天念叨你!家里一切都好,
你弟弟妹妹也整天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呢!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她说着,
身体又往柳振山那边靠了靠,眼神瞟向我,带着一丝隐秘的挑衅。一家人?和和美美?
我胃里一阵翻腾,几乎要呕出来。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疼痛让我保持着最后的清醒。
我垂下眼睫,遮住眼底汹涌的冰寒。***柳家大宅,灯火通明,奢华得像个金丝笼。
晚餐是精心准备的“团圆宴”。长条餐桌铺着雪白餐布,银质餐具闪闪发光。
陈美琳像个真正的女主人一样,坐在柳振山右手边,指挥着佣人布菜。“振山,
你尝尝这个鱼,我特意让厨房做的,对胎儿好。”她夹起一块雪白的鱼肉,放进柳振山碗里,
声音温柔似水。柳振山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温和笑意:“嗯,你有心了。
”他抬眼看向坐在他对面、沉默用餐的我,“芽芽,在国外学得怎么样?
公司最近有几个新项目,你既然回来了,也该学着上手了。”“爸,”我放下银叉,
金属碰在骨瓷盘沿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我抬眼,目光直直地看向陈美琳,
嘴角勾起一个冰冷的弧度,“接手项目之前,我有个‘礼物’,想送给我亲爱的陈阿姨。
”陈美琳脸上的笑容一滞,抚摸着肚子的手也停了下来,警惕地看着我:“芽芽,
你……”我没给她说完的机会。从随身的爱马仕手包里,
慢条斯理地抽出一个薄薄的、印着某知名生物鉴定机构LOGO的牛皮纸文件袋。
动作优雅得像是在抽一张邀请函。“啪”的一声轻响。文件袋被我随手丢在光滑的桌面上,
不偏不倚,正好滑到陈美琳面前。“阿姨,”我的声音不高,却像淬了毒的冰棱,
清晰地穿透餐厅的每一个角落,“您怀着爸的骨肉,辛苦操持这个家,劳苦功高。
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陈美琳的脸色变了变,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强笑道:“芽芽,
你这孩子,搞什么名堂?一家人还弄这些虚的……”她伸手想去拿,又有些犹豫。
柳振山的眉头已经拧成了疙瘩,威严的目光扫过我,带着不悦:“柳芽!你搞什么鬼?
什么礼物?有话直说!”“爸,您别急啊。”我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
好整以暇地看着陈美琳那张强作镇定的脸,“就是一份亲子鉴定报告。我啊,就是好奇,
想看看阿姨肚子里这位‘金疙瘩’,到底是不是我们柳家的真龙种。”“轰——!
”我的话像一颗炸弹,瞬间引爆了整个餐厅。“柳芽!你胡说什么!”陈美琳猛地站起来,
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声响。她脸色惨白,丰满的胸脯剧烈起伏,
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颤抖地指向我,尖声叫道:“你疯了!你污蔑我!振山!你看看她!
她这是要毁了我们这个家啊!”柳振山“腾”地站起身,脸色铁青,额角的青筋都暴了起来,
眼神像要吃人:“柳芽!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立刻给我道歉!向美琳道歉!
”他的声音因为震怒而发颤,巨大的压迫感笼罩下来。佣人们吓得大气不敢出,
纷纷低头后退。餐厅里死一般安静,只剩下陈美琳急促的喘息声。我迎着我爸暴怒的目光,
脸上的笑容反而加深了,冰冷,带着一种残忍的戏谑。我伸出手指,
轻轻点了点桌上的文件袋,动作轻佻得像在逗弄一只即将被碾死的蚂蚁。“爸,
别急着发火嘛。我是不是胡说,您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我的目光转向面无人色的陈美琳,
一字一顿,清晰地吐出那个名字,“阿姨,您和司机老幸,私下交流挺‘深入’啊?
这肚子里的宝贝,确定是我爸的?不是老幸的种?”“老幸”两个字,像两根烧红的钢针,
狠狠扎进了陈美琳的耳朵里。她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嘴唇哆嗦着,
眼睛惊恐地瞪大,仿佛看到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不…不可能…你…你胡说八道!
”她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声音劈了叉,猛地扑向桌上的文件袋,像是要把它撕碎,“假的!
都是假的!你陷害我!”柳振山也被“老幸”这个名字砸懵了。他看看状若疯癫的陈美琳,
又看看桌上那份刺眼的文件袋,再看看我笃定而冰冷的眼神,
巨大的疑云和一种被愚弄的愤怒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理智。他一把抢在陈美琳前面,
粗暴地抓过文件袋,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几下撕开封口,抽出了里面的报告纸。
餐厅里只剩下纸张被粗暴翻动的哗啦声,和柳振山越来越粗重的喘息。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每一秒都像刀子刮在陈美琳的神经上。她瘫坐回椅子上,双手死死护着肚子,
身体筛糠一样抖,眼神惊恐绝望地在我和柳振山之间来回扫视。
柳振山捏着报告纸的手开始剧烈地颤抖。他的脸色从铁青转为一种可怕的猪肝色,
眼睛死死盯着报告结论那一栏,眼珠像是要凸出来。他猛地抬头,血红的眼睛像喷火的怪兽,
死死锁住瑟瑟发抖的陈美琳。“陈!美!琳!”这三个字是从他牙缝里,
带着血腥味挤出来的。“振山…振山你听我解释!是她害我!是她伪造的!
”陈美琳涕泪横流,扑过去想抓柳振山的手臂,“我对你是真心的!这孩子是你的!
是你的啊!”“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用尽了柳振山全身的力气,
狠狠抽在陈美琳的脸上。陈美琳被打得惨叫一声,整个人从椅子上摔倒在地,
额头“咚”地一声磕在坚硬的桌腿上。“啊——!”她发出凄厉的惨嚎,双手死死抱住肚子,
身体蜷缩成一团,脸色瞬间变得惨金。
“痛…我的肚子…好痛…振山…救…救孩子…”殷红的血,
迅速在她昂贵的真丝孕妇裙下摆洇开,像一朵狰狞邪恶的花,越开越大,染红了光洁的地板。
柳振山看着地上的血,又看看手里那份铁证如山的报告,
巨大的打击和愤怒让他身体猛地一晃,脸色由猪肝色瞬间转为骇人的死灰。他一手捂住胸口,
一手死死抓住桌沿,指关节捏得咯咯作响,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倒气声,
整个人像一座瞬间失去支撑的泥塑,直挺挺地向后栽倒!“砰!”沉重的身躯砸在地板上,
发出沉闷的巨响。“柳董!”“快叫救护车!”餐厅彻底乱了套。
佣人们惊恐的尖叫、奔跑声、打电话的嘶喊声乱成一锅粥。我依旧坐在椅子上,
冷眼看着眼前这出人间惨剧。陈美琳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滚哀嚎,柳振山倒在地上,
身体微微抽搐,口角溢出一丝白沫。真讽刺啊,他心心念念的“美满家庭”,
他精心构建的“子女和睦”,就在这一瞬间,被他最宠爱的女人和最信任的司机联手,
砸了个稀巴烂。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食物残羹的油腻味,还有恐惧和绝望的气息。混乱中,
一个熟悉的身影踉踉跄跄地冲了进来,是司机老幸!他大概是听到动静赶来的,
脸上还带着长途开车的疲惫,一进门看到餐厅里的景象,尤其是倒在血泊里哀嚎的陈美琳,
他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僵在原地,脸色煞白。“美…美琳!”他失声叫出来,
下意识就想冲过去。我的目光,像冰冷的探照灯,瞬间锁定了他。
老幸的脚步硬生生钉在了原地。他感受到我的注视,僵硬地、一点点地转过头。
当他的目光对上我那双毫无温度、只有深渊般寒意的眼睛时,他浑身剧烈地一抖,
仿佛看到了地狱里爬出来的索命恶鬼。三年前雨夜巷子里他那句“处理干净”,
和他此刻惊恐绝望的眼神,在我脑中重叠。救护车刺耳的鸣笛声由远及近,
打破了别墅里混乱的死寂。
佣人们七手八脚地抬着昏迷不醒的柳振山和还在痛苦**、身下血流不止的陈美琳往外冲。
担架轮子碾过沾血的地板,留下粘腻的痕迹。餐厅里一片狼藉,昂贵的菜肴打翻在地,
混合着血污,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只剩下我和呆立在门口、面无人色的老幸。
刚才还人声鼎沸的修罗场,此刻只剩下令人窒息的空旷。窗外的霓虹灯光怪陆离地投射进来,
在地板上的血渍上跳动,像鬼火。老幸像被抽掉了骨头,膝盖一软,
“噗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地。坚硬的大理石地面发出沉闷的回响。
他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往下滚,砸在地板上,洇开一小片深色。他双手死死撑住地面,
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身体抖得像狂风中的枯叶。他不敢抬头,声音嘶哑破碎,带着哭腔,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血沫:“大…大**…饶命!饶命啊!”我慢慢站起身,
高跟鞋踩过冰冷的地板,发出“哒、哒、哒”的声响,在这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老幸濒临崩溃的神经上。我在他面前站定,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匍匐在地、抖成一团的脊背。“饶命?”我的声音很轻,
带着一丝玩味的冰冷,像毒蛇的信子舔过他的耳膜,“幸叔,三年前那个雨夜,
你抱着那个刚出生的孩子冲进大雨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饶他一命?”老幸猛地抬起头,
脸上涕泪横流,混合着汗水和极度的恐惧,整张脸扭曲得不成样子。
他嘴唇剧烈哆嗦着:“我…我…大**!我错了!我鬼迷心窍!是陈美琳!是她逼我的!
她说那孩子留不得!留不得啊!”他语无伦次地哭喊,手胡乱地抓着地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