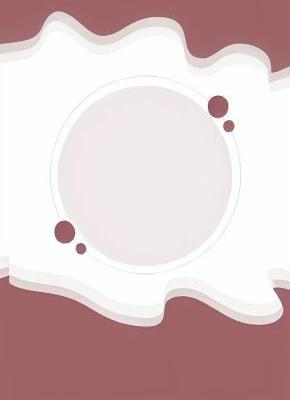
二十八岁那年,他的白月光回来了。那姑娘身子弱,流产后调理了两年也没好全,
他直接开车带她去杭州找老中医问诊。独留胰腺癌晚期的我,走在次年春天。
1白月光进门那天,我刚给他奶奶喂完药我嫁给林屿时,才二十三岁。二十八岁这年,
他心里念了多年的人回来了。而我,胰腺癌晚期,顾砚偷偷告诉我,最多还有半年。
顾砚是我养父母的儿子,市一院消化科的医生,也是我名义上的哥哥,这事我们瞒了所有人。
林屿接回夏栀那天,我刚给他奶奶喂完降糖药。老太太得阿尔茨海默症三年了,
脑子时清时混,此刻正抓着我的手,指腹摩挲着我虎口处的薄茧,
念叨个不停:“小屿那孩子,总熬夜改建筑图,眼睛要熬坏的,晚晚你多盯着点他,
让他按时睡觉。”我耐着性子应着,拿棉柔巾蘸了温水,轻轻擦净她嘴角残留的药渍。
老太太牙口不好,我每次都把药片掰成四分之一,混在温凉的蜂蜜水里搅匀,
再用小勺一勺勺喂进她嘴里,生怕她呛着。刚把药盒放进床头柜的抽屉,
玄关处就传来“砰”的一声巨响,门被撞开了。
唐晓拎着个印着“晚星花店”logo的帆布包冲进来,帆布包带子都歪了,
她跑得气喘吁吁,脸上满是急色,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晚晚!
林屿……林屿真把夏栀接回来了?我刚才在小区门口看见他们了!
”我捏着抽屉把手的指节瞬间泛白,连指腹都因为用力而失去了血色。夏栀这名字,
像根细针,扎在我心里五年了。她是林屿的初恋,是林母从小就认定的“儿媳人选”。
当年林家做家装工程时出了事故,赔光了家底还欠了外债,夏栀转头就跟了个做地产的老板,
嫁去了广州,连句告别都没跟林屿说。如今她离婚了,听说还流产过一次,身子垮得厉害,
灰头土脸地回了宁州,倒成了林屿心尖上要捧着的人。“夏栀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还咳嗽了两声,林屿立马就把自己的羊绒围巾解下来给她围上了!”唐晓越说越气,
抬手拍了下餐桌,桌上的玻璃杯都震得响,“他还帮夏栀拎那个二十寸的行李箱,
生怕她累着,过马路的时候,更是一直护着她,替她挡开骑共享单车的人!晚晚,
你忘了上个月你腹痛到直不起腰,我陪你去医院,你给他打电话,他只说‘项目忙走不开’,
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那冷淡劲儿跟现在比,简直是两个人!”“是不是小屿惹你不高兴了?
”老太太察觉到我脸色不对,拉着我的手皱起眉头,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护着我的意思,
“等他回来,奶奶拿鸡毛掸子抽他!敢欺负我们晚晚,反了他了!”我赶紧按住老太太的手,
把她扶回沙发上,柔声哄道:“没有,奶奶,您别多想,夏栀就是来做客的,
我上去跟她打个招呼,您在这儿看会儿越剧,遥控器在您手边,想看哪个台就换哪个。
”说完,我转身往楼梯走,刚走到二楼转角,就撞见林屿从客房里出来。
他穿着我去年生日送他的深灰色针织衫,袖口还留着我缝补过的细微痕迹,
可此刻他脸上的神情,却陌生得让我难受。“夏栀坐了四个小时的车,累得很,想歇会儿,
你别上去打扰她。”林屿直接挡在我面前,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
“从市区的快捷酒店到咱们家,车程才五十分钟,就算堵车,也用不了四个小时。
”我盯着他的眼睛,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丝熟悉的温柔,可看到的只有冰冷的疏离,“林屿,
你没必要替她撒谎,我只是想跟她打个招呼,没别的意思。”他皱起眉,
语气瞬间冷了下来:“苏晚,你别这么不讲理行不行?夏栀身体不好,经不起折腾,
你就不能让她清静会儿?”我看着他护着客房门的样子,心里像被泼了一盆冰碴子,
冷得发疼。我没再跟他争,转身慢慢下楼。唐晓还坐在餐桌旁,
手里戳着我早上炖的莲子百合羹,见我回来,气鼓鼓地说:“晚晚,你就是太软了!
换做是我,早就把夏栀的行李箱扔到小区垃圾桶里去了,让她知道这是谁的家!
”我把那碗莲子百合羹推到她面前,声音轻得像飘在空气里:“尝尝吧,我今天放了点蜜枣,
比上次炖的甜一点,你以前总说我炖的甜汤不够甜。”唐晓舀了一勺放进嘴里,嚼着嚼着,
声音突然软了下来:“……是挺甜的,晚晚,你手艺还是这么好。”可我尝不到一丝甜味,
嘴里满是苦涩,连呼吸都带着疼。那是胰腺癌晚期的隐痛,像针一样,
细细密密地扎着我的五脏六腑。2他护着初恋骂我疯了,
我烧了他送的速写我让唐晓把衣柜最上面的那个纸箱搬下来。里面装的全是林屿送我的东西,
从恋爱时到结婚后,一件都没丢过。唐晓踩着凳子把箱子抱下来,灰尘落在她的卫衣上,
她拍了拍,笑着说:“晚晚,这里面还有你当年开花店时,林屿给你画的花店设计图吧?
我记得你当时还跟我炫耀了好久。”我蹲在地上,慢慢打开纸箱的封条。
最上面放着一块木质挂牌,上面刻着“晚星花店”四个字,
字体是林屿特意练的簪花小楷,还刷了清漆,摸起来光滑又温暖。这是我关店那年,
他送我的礼物,说:“晚晚,就算花店关了,我也会做你的星星,陪着你。
”下面是一沓速写纸,全是林屿画的我。有我在花店浇花的样子,
有我坐在沙发上看书的样子,还有我睡着时的样子,每张画的右下角,
都写着日期和“我的晚晚”四个字。再往下,是结婚周年时他送的小苍兰标本,
压得平平整整,还放在精致的玻璃框里。我指尖抚过那些画纸,眼泪差点掉下来。就在这时,
林屿从楼上下来了,他看到我蹲在地上,面前摆着那个纸箱,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唐晓识趣地溜进厨房,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空气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什么?”林屿走过来,语气里满是不耐烦,甚至带着一丝嫌弃,
好像这些他曾经花心思准备的礼物,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些都是你送我的,
我一直好好收着,没丢过一件。”我抬头看他,手里捏着一张他画我浇花的速写,
纸上的我笑得眉眼弯弯,跟现在的我判若两人,“林屿,你还记得你画这张画的时候吗?
那天我在花店浇小苍兰,你蹲在旁边画了半个多小时,说我认真的样子最好看。”他没接话,
只是皱着眉:“我问的是你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不是让你回忆过去。
”我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是上次去便利店买的,一直放在身上。我在他错愕的眼神里,
把手里那张速写纸扔进了打开的纸箱里,然后点燃了打火机,火苗“腾”地一下窜起来,
很快就舔舐到了旁边的画纸。我赶紧合上箱盖,怕火星溅到旁边的窗帘。我虽然难过,
却也不想把这个家烧了,这是我跟林屿住了五年的地方,还有太多回忆。林屿反应过来后,
冲过来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打火机,扔到一边,然后抓起桌上的凉白开,对着纸箱就浇了下去。
直到箱子里的火完全灭了才停下来。他捡起一块烧黑的速写纸,纸角还冒着烟。
他捏着那张纸,转头瞪着我,眼里全是冷意,甚至带着一丝厌恶:“苏晚,你是不是疯了?
这些速写都是我花心思画的,你就这么不珍惜?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是他结婚五年来,
第一次用这么重的语气跟我说话,第一次骂我“疯了”。
我盯着地上那个湿漉漉、黑乎乎的纸箱,心里的疼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淹没了我。
我慢慢站起来,声音轻得像随时会碎掉:“林屿,如果你想让夏栀住在家里,我没意见,
但别太张扬。她前夫卷款跑路的事,宁州建筑圈里不少人都知道,
你现在正在争设计院副总监的位置,要是被人知道你跟这样的女人走得这么近,
对你的前途不好……”“我的事不用你管,夏栀的事也不用你管!”他打断我,
语气硬得像冰,“苏晚,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别整天盯着别人不放,显得你很刻薄。
”说完,他转身就往楼上走,脚步踩在楼梯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像锤子一样,
一下下砸在我的心上。我站在原地,看着地上那个烧得面目全非的纸箱,
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那些画,那些礼物,是我这五年婚姻里唯一剩下的,可现在,
被我亲手烧了,也被他亲手否定了。唐晓从厨房探出头来,小声说:“晚晚,你别难过,
林屿他就是被夏栀迷昏了头,等他反应过来,肯定会后悔的。”我摇了摇头,慢慢蹲下来,
捡起一块没烧透的速写纸。纸上的我还能看清眉眼,林屿画得很认真,
连我头发上别着的小苍兰发夹都画出来了。我把那张纸紧紧攥在手里,指腹蹭过烧黑的边缘,
疼得蜷缩起来。不是肚子痛,是心痛,比胰腺癌的疼,还要痛一万倍。
3我织了两个月的披肩,穿在了白月光身上以前林屿在设计院做助理设计师的时候,
总忘了吃早餐,有时候赶项目,甚至连午饭都顾不上吃。我嫁给他之后,
就养成了七点起床做早餐的习惯,每天换着花样来,今天是全麦三明治配杂粮粥,
明天是水煮蛋配豆浆,后天是蔬菜饼配小米粥,然后开车送他到设计院楼下,
看着他进了大楼才离开。昨天跟他闹成那样,我还是醒得很早。五点半就起来了,
去菜市场买了新鲜的芦笋和虾仁,回来煎了芦笋虾仁,还烤了小面包,摆放在精致的瓷盘里,
等着林屿下来吃。可我等了一个多小时,煎好的芦笋都凉透了,也没见他下来。
我坐在餐桌旁,看着桌上的早餐,心里空落落的。以前他就算起得晚,也会跟我说一声,
可现在,他连一句解释都没有。直到二楼传来下楼梯的声音,我以为是林屿下来了,
赶紧站起来,却看见林屿正帮夏栀拉羽绒服的拉链,夏栀肩上搭着的,
是我去年冬天织了两个多月的羊毛披肩。那是我专门选的浅灰色羊毛线,
跟林屿的很多衣服都能搭,每天下班回家,我就坐在沙发上织两小时,
手指被毛线针扎破了七八次,贴了创可贴继续织,织完后还特意拿去干洗店熨烫了。
林屿收到的时候,还笑着说:“晚晚,你手真巧,这披肩真好看,我以后天天都穿。
”林母也跟在他们身后,手里拎着一个粉色的保温桶,笑盈盈地对夏栀说:“栀栀,
这是我早上五点起来炖的乌鸡汤,你路上喝,补补身子。你要是觉得家里住得挤,就跟妈说,
妈再给你收拾一间朝南的房间,保证你住得舒服。”夏栀轻轻咳嗽了两声,
眼神往我这边扫了扫,然后露出一个软乎乎的笑,声音甜得发腻:“晚晚,好久不见啊,
你好像瘦了不少,是不是最近没好好吃饭?要多注意身体才行。”我没接她的话,
目光死死地盯着她肩上的那条羊毛披肩。那是我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上面还绣了一朵小小的小苍兰,就在披肩的左下角,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那是我跟林屿的定情花,他以前总说小苍兰像我,温柔又坚韧。可现在,
这条披肩穿在了夏栀身上,像一根刺,扎得我眼睛生疼。林屿看了眼手腕上的手表,
语气急促地说:“我们先走了,夏栀还要去医院复查,下午我送她回来。”“等等!
”老太太突然从客厅里走出来,她手里拿着一个苹果,刚咬了一口,看见夏栀,
突然停下了动作,指着她说:“你不是跟那个做地产的老板去广州了吗?怎么回来了?
我记得你当时走的时候,还跟小屿说再也不回来了呢。”夏栀的脸瞬间僵了,
嘴角的笑容也挂不住了,下意识地往林屿身后躲了躲。林屿赶紧打圆场:“奶奶,您记错了,
夏栀早就从广州回来了,只是一直没来得及来看您。她这次回来,就是专门来看您的,
等她身体好点,就陪您说话。”老太太还想再问,林母赶紧走过去,拉着她往屋里走:“妈,
您别瞎问了,栀栀还要去医院呢,别耽误了她的时间。”一边走,一边给我使眼色,
让我别说话。两人走后,林母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闪躲和愧疚。她犹豫了半天,
才开口说:“晚晚,夏栀她……也不容易,离婚了还身体不好,你就多担待点,
别跟她计较太多,啊?”我没说话,转身慢慢回了卧室。床头柜上放着顾砚给我开的药,
有止痛药,还有一些补充营养的药,满满一抽屉。我拿起水杯,
把止痛药和那些药一起吞了下去。早上起来的时候,肚子就开始疼了,一直忍着,
现在疼得更厉害了,连腰都直不起来。“晚晚,你这药都吃一个月了,啥时候是头啊?
”唐晓端着一杯温水走进来,看着我把药吞下去,皱着眉说,“顾医生也真是的,
就不能开点见效快的药吗?你看你最近瘦的,都快没肉了。”“我哥说这是调理肠胃的药,
慢慢吃就会好的,说不定以后还能怀上孩子呢。”我笑着跟她撒谎,
这是我跟顾砚约好的借口,怕林家人多想,也怕唐晓担心。
我没告诉唐晓我得的是胰腺癌晚期,只说我肠胃不好,需要慢慢调理。唐晓眼睛一亮,
凑到我身边,笑着说:“真的吗?那以后小宝贝肯定像你,笑起来有两个小小的梨涡,
肯定特别可爱。晚晚,到时候我要做小宝贝的干妈,天天带他去买糖吃。”我被她逗笑了,
靠在床头,闭上眼睛说:“好啊,到时候让你做干妈。我睡会儿,
下午顾砚来接我去选生日礼物,你记得叫我。”唐晓点点头,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鸟叫声,眼泪慢慢流了下来。我也想有个孩子,想跟林屿有个家,
可我没机会了,胰腺癌晚期,连活着都成了奢望,更别说生孩子了。4咳血那天,
我看见他陪白月光买营养品下午顾砚开车来接我,他把车停在小区门口,我坐上车,
看见副驾驶座上放着一个丝绒盒子,里面装着一条珍珠项链。是妈妈上周在珠宝工作室订的,
说要给我做生日礼物。顾砚把盒子递给我,笑着说:“妈说让你自己看看喜欢不,
要是不喜欢,再去换别的款式,她特意跟工作室的老板说了,随时可以改。”我打开盒子,
那颗淡水珠躺在丝绒上,透着柔和的光,大小刚好,颜色也均匀,一看就是精心挑选的。
我摸了摸珍珠,心里暖暖的,笑着说:“喜欢,妈选的肯定好看。对了,妈最近跳广场舞没?
上次跟我说她膝盖疼,你让她别跳太久。”“说了,她不听,还说要跟张阿姨比谁跳得好。
”顾砚无奈地笑了笑,发动车子,“对了,你最近复查了吗?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我摇摇头,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不用复查了,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挺好的,就是偶尔会咳嗽两声,没什么大事。”顾砚还想说什么,我突然指着窗外,
声音有些发颤:“哥,你看,那是不是林屿?”街对面的母婴用品店里,
林屿正帮夏栀拎着一个大大的购物袋,里面装满了进口的营养品,有蛋白粉,有维生素,
还有一些孕妇吃的叶酸。夏栀根本没怀孕,她就是想借着“补身体”的名义,
让林屿给她买东西。夏栀挽着林屿的胳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不知道说了什么,
林屿笑了起来,还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那温柔的样子,是我结婚五年都没见过的。
顾砚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猛地踩了刹车,就要开门下去:“我去找他!林屿这小子,
太过分了!你都这样了,他还陪着别的女人买东西,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老婆!
”我赶紧拉住他的胳膊,声音带着哭腔:“哥,别去,别去找他。”顾砚回头看我,
眼里满是心疼:“晚晚,你都这样了,还护着他?你看看他对那个女人的样子,
再看看他对你的样子,你值得吗?”“我问过夏栀的前同事了。”我喘着气,
肚子又开始疼了,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当年林家出事后,不是林屿提的分手,
是夏栀嫌林家没钱了,主动跟那个地产商走的,林屿一直瞒着我,还跟我说,
是他对不起夏栀。哥,你说,他为什么要骗我啊?”顾砚还没说话,我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手捂在嘴上,咳得撕心裂肺。顾砚赶紧从包里拿出纸巾递给我,我接过来,捂在嘴上继续咳。
等咳嗽停下来,我拿开纸巾,上面全是刺目的红。是血,我又咳血了。“晚晚!
”顾砚赶紧从包里拿出药,手都在抖,他把药递给我,又给我倒了杯温水,“快把药吃了,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不能再硬撑了!”“不去医院。”我摇了摇头,
眼泪掉在满是血的纸巾上,晕开一朵朵小红花,“哥,我快不行了,我知道自己的身体,
去医院也没用,只会让爸妈担心。你答应我,别告诉爸妈,别告诉任何人,好不好?
我不想让林屿和夏栀得意,不想让他们看我的笑话。”顾砚没说话,他别过头去,
我看见他的肩膀在抖,眼泪落在方向盘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他是医生,
比谁都清楚胰腺癌晚期的严重性,也比谁都明白,我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
车子里安静得可怕,只有我的呼吸声和顾砚压抑的哭声。我看着窗外的街景,
想起了十一岁那年。那天小区里的孩子又欺负我,把我养的小苍兰连根拔了,
还把我推到花坛边的月季丛里,我的胳膊被月季刺扎破了,流了很多血。
就在我以为要被他们打死的时候,十五岁的林屿跑了过来,他把那些孩子赶跑,
然后蹲在我身边,小心翼翼地帮我摘衣服上的刺,还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创可贴,
贴在我的伤口上,说:“晚晚,以后他们再欺负你,就告诉我,我保护你。”从那以后,
林屿总来找我玩,他会给我带多肉小苗,说“这个好养活,就像你一样,
要好好长大”;他会帮我画花店的设计图,说“晚晚,
以后你的花店肯定会很受欢迎”;他会在我难过的时候,把肩膀借给**,说“晚晚,
有我在,别害怕”。我以为他会一直保护我,会一直陪着我,可我没想到,
他会在夏栀回来后,把我丢在原地,不管不顾。“哥,我们去珠宝工作室吧,
我想把那条珍珠项链定下来,早点做好,说不定我还能戴几天。”我轻声说,
声音里满是疲惫。顾砚点点头,发动车子,往珠宝工作室的方向开去。
阳光透过车窗照在我脸上,暖暖的,可我却觉得冷,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冷。
5白月光姑姑闹上门,他护着她骂亲戚夏栀在我家住了半个月,没主动找过我一次,
却天天跟林母待在一起,要么去商场买衣服,要么去美容院做SPA,
要么就在家里看电视,把林家当成了自己家。林屿每天下班回来,
第一句话永远是“栀栀呢”。要是夏栀在客厅看电视,他就会走过去,坐在她旁边,
跟她一起看;要是夏栀在房间休息,他就会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敲门问她要不要吃水果。
那天下午,我正在厨房炖银耳羹,刚把银耳泡发好,就听见客厅里传来吵架的声音,
还有女人的哭声。我关掉燃气灶,擦了擦手,走到客厅门口,
看见一个穿着深色外套的中年女人正拉着夏栀的胳膊,红着眼眶,声音激动地说:“夏栀,
你跟我回去!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都怎么说你?说你离婚了还赖在别人家里不走,
说你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丢不丢人啊!我们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那个女人是夏栀的姑姑。夏栀的父母早逝,她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姑姑对她一直很好,
没想到现在会闹到这个地步。夏栀躲在林母身后,双手抓着林母的胳膊,
